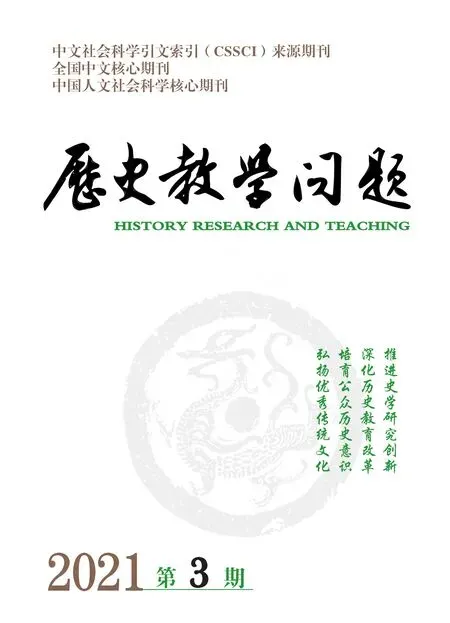耶路撒冷的“俄國財產”與蘇聯對以色列外交(1948—1953)
江 藝 鵬
耶路撒冷的“ 俄國財產”(русское имущество)曾被譽為“俄國在圣地的事業”,展現出沙俄政府渴望建立“第三羅馬”的夢想。[1]作為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城”,耶路撒冷歷來是各方勢力的必爭之地。十八世紀以來,俄國東正教傳教團前往巴勒斯坦建立海外教會并在當地購置了大批財產。“俄國財產”主要位于耶路撒冷的“新城”,[2]包括大小教堂、學校、朝圣者房舍以及養老院等設施。[3]沙俄政府借助東正教教會的力量,以這些財產為基礎擴大在海外的影響。東西方冷戰爆發后,蘇聯政府出于地緣安全的考慮向新生的以色列政府要求接管“俄國財產”。[4]受到當時冷戰局勢的影響,蘇以雙方之間有關財產問題的交涉被擱置了。赫魯曉夫執政時期,蘇聯政府將大部分“俄國財產”出售給以色列政府,僅要求接管其中的數座建筑物。此后,蘇以兩國政府有關“俄國財產”問題的交涉有了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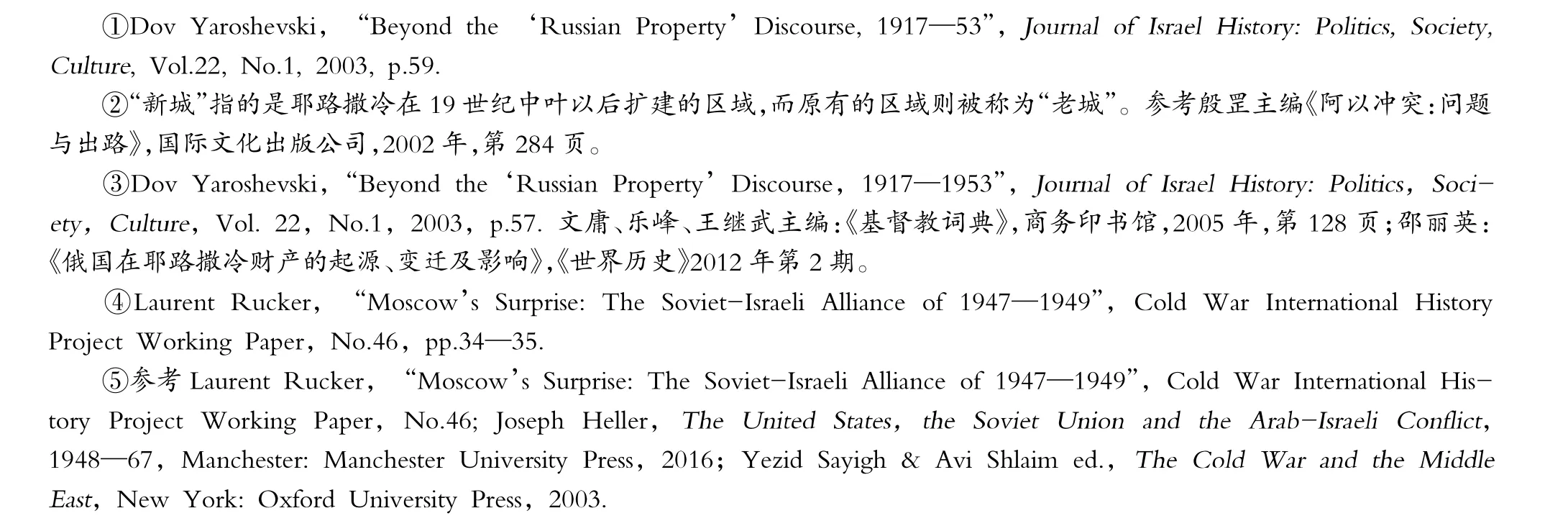
最近二十年,隨著蘇聯檔案的解密與冷戰史研究的興起,學界愈發關注冷戰時期的國際局勢對蘇以外交關系的影響,[5]尤為重視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對以色列政策的轉變過程。[1]已有研究的重點在于蘇以兩國政府之間的互動,較少關注冷戰中的多方博弈及其對近東外交格局的重塑。[2]而耶路撒冷的“俄國財產”問題恰好為此提供了一個觀察窗口。蘇以雙方圍繞“俄國財產”問題的交涉持續多年,且恰逢冷戰在全球蔓延之際,本應為蘇以雙邊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的俄國財產問題高度冷戰化,牽扯到蘇以、美蘇、美以等多重雙邊關系及其之間的互動。基于有關該問題的現有研究成果,[3]本文運用《蘇聯-以色列外交關系檔案集》[4]和《近東沖突: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文件選編》等解密檔案,[5]梳理蘇以雙方對“俄國財產”問題的交涉過程,關注斯大林執政后期蘇聯政府對以政策的轉變及其影響因素。在彌補學界關于蘇以關系研究所存在的缺憾的同時,[6]筆者嘗試探討戰后中東外交格局的冷戰化重塑問題,并回應“冷戰在近東地區的形態及其特征”這一問題。
一、耶路撒冷的“俄國財產”問題之緣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向其他參戰國承諾戰后共同分割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阿拉伯人的土地。1916 年5 月,英法俄三國代表秘密締結“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規定英法將分別統治伊拉克南部和敘利亞大部分土地,而英國還間接占據了從地中海到波斯灣的地區。當時,俄國的國家實力衰退,無暇顧及遠在東方的擴張,僅要求劃出一塊國際飛地用以管理宗教事務。[7]1917 年10月,俄國國內政局劇變,布爾什維克黨上臺執政并宣布退出一戰。巴勒斯坦的東正教教會失去了沙俄政府的資助,無奈之下將耶路撒冷的主要建筑出租以維持生計。[8]于是,耶路撒冷的“俄國財產”成為英國駐軍在巴勒斯坦的辦公場所。一戰結束后,英法雙方通過圣雷莫會議(Conference of San Remo)達成協議,由英國政府對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進行委任統治,而“俄國財產”也隨之由英國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委任統治管理當局保管。[1]這意味著蘇維埃政權的合法性不被承認,所以它無權接管沙俄政府在巴勒斯坦的財產。

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政府頒布一系列法令剝奪宗教組織的各種特權,將其置于國家權力的統一監督之下,使改造后的宗教與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相適應。[2]1918 年2 月18 日,蘇維埃政府頒布《關于信仰自由、教會和宗教團體》法令,該法令對東正教的政治和經濟權利作出了新的規定。根據法令,東正教在沙俄時期獲得的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特權全部被取消。蘇聯國內的教會和宗教團體和財產一律沒收。[3]按照上述規定,沙俄時期東正教教會的海外財產應該國有化,那么蘇維埃政府就有權接收在巴勒斯坦的“俄國財產”。1923 年5 月,蘇聯政府借本國貿易代表團訪問倫敦之機,再次提出“收回”在巴勒斯坦的俄國東正教教會財產。[4]蘇聯駐英國使館代表К. 拉科夫斯基(К. Раковский)向英國方面聲明:“位于巴勒斯坦的俄國東正教教會財產屬于蘇聯政府所有,任何人在未經蘇聯政府同意的情況下都無權處理這些財產”。[5]英國方面答復說,除非有法律文件能證明蘇聯政府擁有繼承權,否則他們不會交出這些財產。[6]蘇聯政府拿不出相關的法律文件,自然無法繼承前沙俄政府的海外財產。而巴勒斯坦的東正教教會堅持效忠前沙俄政權,也反對蘇聯政府接管“俄國財產”。如此一來,蘇聯政府在該問題上無計可施,只能望洋興嘆。
1941 年6 月蘇德戰爭爆發后,蘇聯政府放寬了對國內宗教活動的限制,以愛國主義凝聚人心,集中全國力量抵御外敵,同時還授意國內的東正教教會與海外宗教團體建立聯系,為國家爭取更多的戰爭資助。1943 年,蘇聯人民委員部俄國東正教事務委員會主任Г.Г.卡爾波夫(Г.Г. Карпов)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文件,建議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正式要求“收回”位于巴勒斯坦的東正教教會財產,增強俄國東正教教會在當地的影響力。蘇聯人民委員部副外交人民委員И.邁斯基(И. Майский)也指出,蘇聯政府應通過外交、政治和文化等措施擴大在巴勒斯坦的影響。[7]當戰爭慢慢走向尾聲,蘇聯社會經濟各領域百廢待興,急需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提供的援助進行重建。為了維護雅爾塔體系構建的戰后國際秩序,蘇聯政府在近東政策上比較克制,恐怕引起英國政府的不滿。И. 邁斯基認為,戰后應該創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使“長時期內,至少在歐洲和亞洲,蘇聯的安全得到保障,和平得以維持。”[8]此外,他還建議蘇聯政府不要援助泛阿拉伯運動,以免同英國政府產生矛盾。蘇聯外交部中東局也提議,蘇聯政府不應插手中東地區的阿猶沖突,防止英國在“俄國財產”問題上制造障礙。[9]由于不想觸及英國的勢力范圍,蘇聯政府在財產問題上并無進展。
在蘇聯政府看來,“俄國財產”只是前沙俄政府的海外財產,并不具備戰略上的重要意義。1945 年3月31 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C.И. 卡夫塔拉澤(С.И. Кавтарадзе)向莫洛托夫報告,說英美的石油輸送管道將會經過巴勒斯坦,蘇聯政府迫切地需要在巴勒斯坦建立據點,以便監視英美的石油政策。他的建議是設立蘇聯駐巴勒斯坦領事館,并不是接管與利用當地的“俄國財產”。[10]“俄國財產”問題仍然是一個宗教問題,尚未進入蘇聯近東政策的計劃。當時蘇聯政府也是通過宗教途徑去溝通該問題。1946 年,莫斯科教會的阿列克謝大牧首一行抵達耶路撒冷,與當地的東正教教會人員建立初步聯系。[11]然而,隨著非殖民化運動與東西方“冷戰”對峙的發展,蘇聯政府的態度卻發生了改變。
戰后英國政府的海外勢力日益衰退,逐漸從埃及、印度和巴勒斯坦退卻。中近東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風起云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也不斷壯大。而美國和蘇聯也以巴勒斯坦問題為契機,極力把英國趕出中近東地區。受到冷戰思維的影響,“俄國財產”不再是一個宗教問題。它被蘇聯政府納入對近東地區進行滲透、擴大對中近東的影響的政策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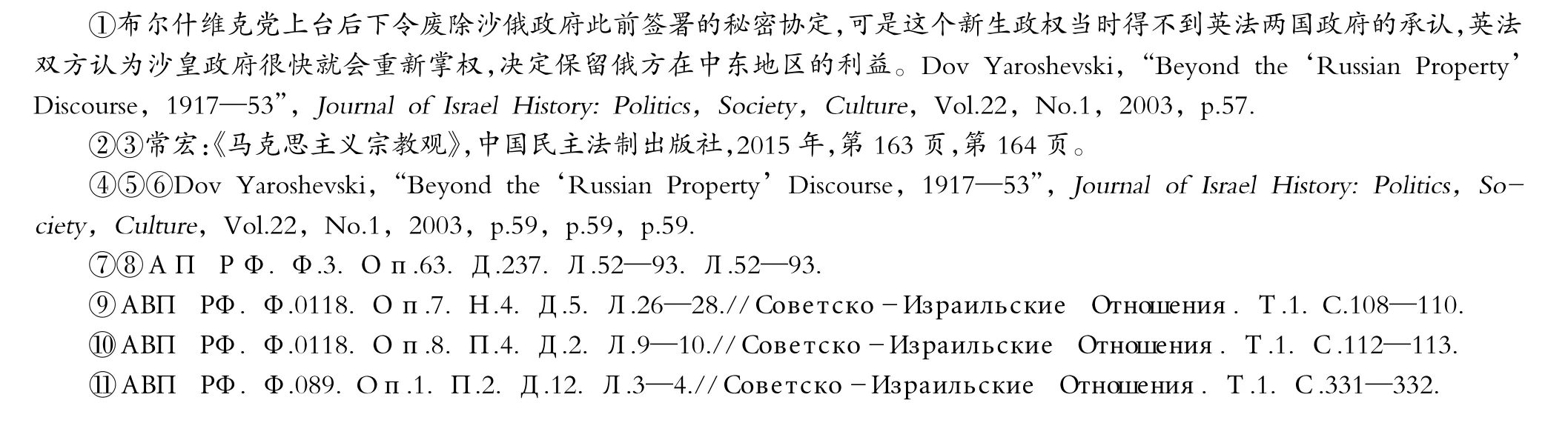
二、蘇聯重提耶路撒冷的“俄國財產”問題
二戰結束后,蘇聯利用其戰勝國的地位向南擴張,對土耳其提出領土要求,拒絕從伊朗撤軍,還謀求獲得在伊朗的石油租借權。[1]受到英美的合力抵制之后,蘇聯政府又把目光投向近東地區。[2]1947年2 月,阿猶雙方的矛盾由于歐洲猶太難民的大量涌入而被激化,英國政府被迫將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這恰恰為蘇聯政府插手近東事務、重提“俄國財產”提供了一個契機。
1947 年11 月29 日,在美蘇兩國代表的支持下,聯大通過了《巴勒斯坦將來治理(分治計劃)問題的決議(第181 號決議)》,規定猶太人有權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而耶路撒冷作為“獨立個體”接受國際共管,任命一位總督作為行政長官,由各國派駐代表組成管理委員會。[3]不久之后,“巴勒斯坦問題特別調解委員會”成立,制定了耶路撒冷的管理方案,并賦予總督任命管理委員會的各國代表的權力。[4]很可能,正是第181 號決議的通過提高了耶路撒冷及其當地的“俄國財產”在蘇聯近東政策中的地位。根據蘇聯方面的調查,“俄國財產”除了位于耶路撒冷的主體部分之外,其余分布在橄欖山(Mount of Olives)、雅法(Jaffa)和伯利恒(Bethlehem)等地。[5]如果蘇聯政府能順利接管這些財產,就能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建立起據點,有利于擴大蘇聯在近東地區的影響。在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前景不明的情況下,蘇聯政府接管耶路撒冷的“俄國財產”,無異于往英美的勢力范圍打下一個楔子。因此,耶路撒冷的命運是蘇聯近東政策的一個關鍵問題。1948 年3 月1 日,蘇聯外交部提出,各國派駐耶路撒冷的代表不能由總督任命,否則總督有可能不讓蘇聯代表參加。[6]更何況,耶路撒冷作為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城”,在近東各國人民的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蘇聯政府極力爭取對耶路撒冷事務的管理,除了想接管耶路撒冷的“俄國財產”,也試圖與英美爭奪在近東問題上的話語權。如此,支持實行聯大第181號決議的規定、對耶路撒冷實行國際共管,便成為蘇聯政府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一貫立場。
1948 年5 月14 日,英國政府提前結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當天下午,以色列宣布建國,美蘇迅速予以承認。次日,阿拉伯各國軍隊進攻巴勒斯坦的猶太定居點。[7]第一次中東戰爭正式爆發。[8]而此時蘇聯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系卻惡化了。由于不滿蘇聯政府對以色列建國的支持,很多阿拉伯國家的民眾甚至舉行了反蘇游行。二戰后期以來,蘇聯政府公開支持埃及政府廢除英埃條約的行為,譴責法國政府出兵占領敘利亞和黎巴嫩。[9]所以,埃及、敘利亞和黎巴嫩三國政府對蘇聯政府的評價較高,它們都和莫斯科方面保持著密切聯系。[10]當聯大通過第181 號決議之后,埃、敘、黎三國政府派人請求蘇聯政府改變立場,希望莫斯科能站在阿拉伯人這邊。但蘇聯政府不愿意放棄管理耶路撒冷的機會,莫斯科方面堅持認為,應該實行聯大第181 號決議的相關規定。[11]與此同時,蘇聯政府通過東歐國家分別向阿以雙方軍隊出售武器。[12]阿拉伯軍隊擁有英國政府提供的武器,以色列方面卻受制于武器禁運,因此,來自蘇東國家的武器對以色列軍隊的意義更加重大。蘇以雙方的關系被迅速拉近了,而阿拉伯國家和蘇聯之間卻有了隔閡。

蘇阿關系的惡化迫使蘇聯政府把更多精力放在以色列身上。隨著第一次中東戰爭被平息,蘇聯-以色列雙方關系步入佳境,蘇聯政府提出接管耶路撒冷的“俄國財產”問題的時機也到來了。1949 年2月至7 月,埃及、黎巴嫩、約旦、敘利亞四國政府分別與以色列政府簽訂停戰協定,第一次中東戰爭宣告結束。戰后外約旦軍隊占據了耶路撒冷老城,而以色列軍隊則占領了西區新城。由于“俄國財產”主要位于新城,因此大部分財產都被以色列軍隊接管。以色列方面將“俄國財產”交給猶太代辦處的伊扎克·拉賓諾維奇(Yitzhak Rabinovich)管理。[1]隨后,蘇聯政府立即向以色列政府提出接管這些財產,以色列政府不想得罪蘇聯政府,故同意與蘇聯方面交涉“俄國財產”問題。伊扎克·拉賓諾維奇認為,如果轉移“俄國財產”的所有權,首先要聯系原來的財產負責人。[2]蘇聯政府知道這些教會人員不會接受莫斯科的領導,建議蘇以雙方繞開他們直接討論接管問題,該提議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認同。[3]然而,以色列政府并不愿意交出這些財產,尤其不想失去在耶路撒冷的“俄國區”(Russian Compound)。“俄國區”是一個歷史悠久、風格獨特的建筑群,包括圣三一大教堂、醫院、領事館、給朝圣者過夜的住所和謝爾蓋莊園等等。[4]這個建筑群的所有權原本屬于皇家正教巴勒斯坦協會(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Палести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ИППО)[5]及其主席С. 亞歷山德羅維奇(С.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大公。[6]在英國委任統治時期,“俄國區”的建筑物被用作政府機構的辦事處,例如移民局和公共工程局。當以色列軍隊占領耶路撒冷之后,也沿用了這些辦公場所。此時再讓以色列政府把各個機構遷出來,將這些財產交給蘇聯政府,自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且,東西方“冷戰”對峙的局勢日益加劇,以色列政府也感受到巨大的安全威脅。建國初期,以色列政府內部由“馬帕伊”黨(Mapai,全稱為“以色列勞動黨”)執政。“馬帕伊”黨主張在外交上走中立路線,但是黨內成員的親西方傾向很嚴重。此外,還有第二大黨——“馬帕姆”黨(Mapam,全稱為“聯合工人黨”),該黨與蘇聯政府的關系非常密切。[7]從1949 年以來,蘇聯駐以色列大使館經常與以色列政府內部的“親蘇”人士來往,其中就包括“馬帕姆”黨的領袖斯納·摩西(Sneh Moshe)。[8]由此推測,以色列領導人擔心蘇聯借助“俄國財產”實施滲透,增強以色列國內“親蘇派”的力量,甚至有可能干涉以色列內政。所以,以色列政府為了維護國家利益,遲遲不肯交出“俄國財產”。除了耶路撒冷的“俄國區”,其他財產的移交也是遙遙無期。這些財產屬于前沙俄政府及其派出的前俄國宗教使團(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所有。為了名正言順地接管財產,蘇聯政府還成立了新的“俄國宗教使團”,并任命莫斯科正教會的人員為該機構的代表,派遣他們前往耶路撒冷進行交涉。[9]但是,新的“俄國宗教使團”得不到以色列政府的承認,因而也無法正式接管財產。[10]1949年年底,“俄國財產”仍處于以色列政府的控制之下,蘇聯方面的財產接管工作毫無進展。[11]此時,耶路撒冷的歸屬問題在聯合國掀起波瀾,蘇以雙方有關“俄國財產”問題的交涉有了轉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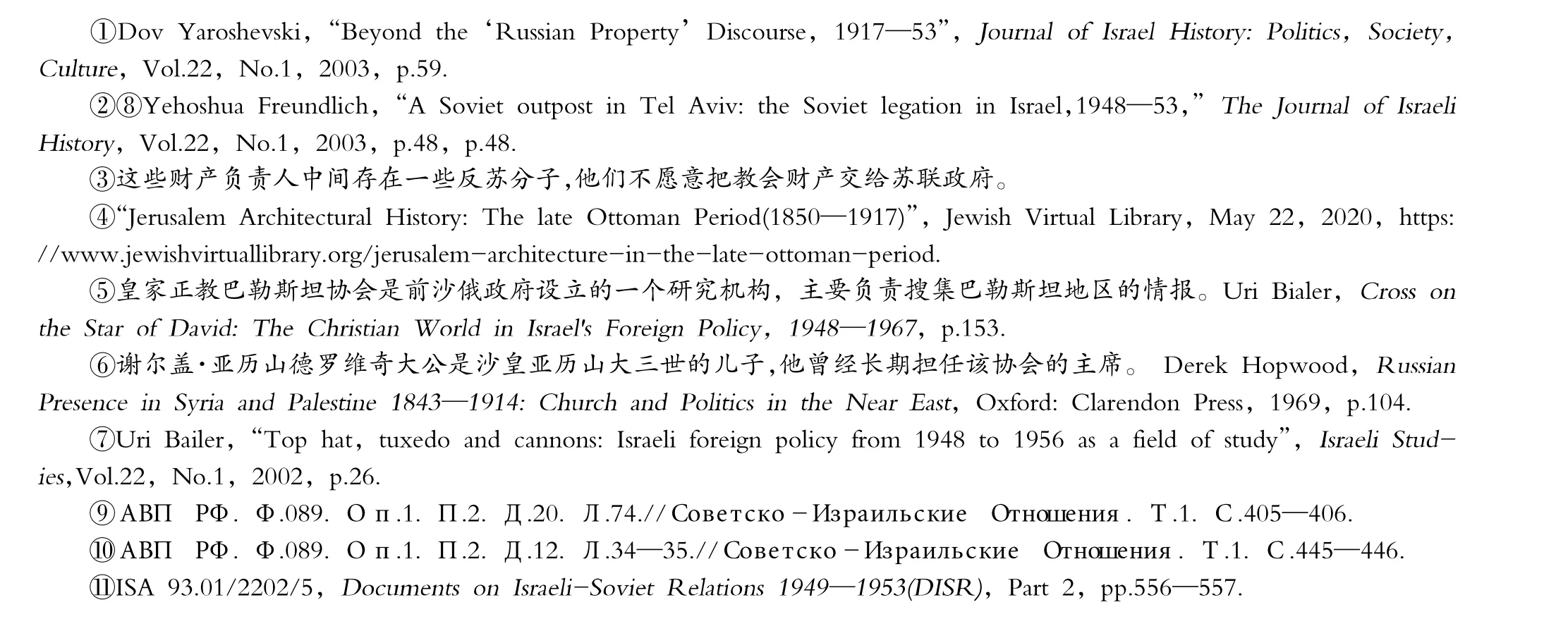
三、蘇聯欲打破在“俄國財產”問題上的僵局
第一次中東戰爭改變了近東的政治格局,也留下了耶路撒冷的歸屬問題。戰爭結束后,耶路撒冷被以約兩國軍隊分區占領。雙方都拒絕將“圣城”交給聯合國管理,反對實行第181(Ⅱ)號決議的規定。[1]這種行為不但引起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抗議,也遭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反對。因此,聯合國被迫重新開會討論耶路撒冷的歸屬問題。[2]在東西方“冷戰”環境的影響下,耶路撒冷的歸屬權不再是作為阿以矛盾焦點的地區問題,而是關系到美蘇近東戰略的國際問題。
從處理希臘和土耳其危機開始,美國就接過英國在中東地區的擔子,逐步將中東建成“反蘇防共”的堡壘。1949 年1 月20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了援助經濟落后的不發達國家的“第四點計劃”,其援助對象包括近東地區的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約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3]雖然美國政府更想拉攏阿拉伯國家,所以對以色列的援助相對較少,但是美國猶太人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再加上美國與以色列兩國在文化上的親緣性,因此以色列仍然在美國近東戰略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1949 年5 月16 日,美國國防部向國家安全委員會遞交了一份名為《美國在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的備忘錄,指出美國在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為:A、確保以色列政府傾向西方民主國家,疏遠蘇聯勢力;B、堵塞共產黨對以色列的滲透,防止蘇聯對以色列的控制;C、解決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分歧和爭端;D、從軍方觀點來看,應改善英國與以色列的關系,使在對以色列的政策上美英能實現共同目標。[4]1949 年10 月17 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出臺了NSC47/2 號文件,文件規定:A、努力維持以色列政治和經濟的穩定;B、應當努力促成阿以之間解決爭端,至少使他們在反對蘇聯控制和影響方面;C、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向以阿雙方在解決經濟、政治及社會問題上提供幫助和指導。[5]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國作為一個整體,被納入美國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戰略范圍。
為了盡快穩定近東地區的局勢,美國政府支持聯合國調停“耶路撒冷之爭”。[6]但是,聯大第181 號決議并不符合英美的利益,因為耶路撒冷接受國際共管之后,蘇聯政府將會趁機干預近東事務,所以英美嘗試制定一個全新的解決方案。[7]以英美為首的巴勒斯坦調解委員會(Palestine Conciliation Commission,PCC)提出了不少建議,可是各方的意見難以統一,始終無法拿出理想方案。[8]1949 年8 月份,以色列政府提出了一個新方案,讓英美都喜出望外。該方案承認以約分區占領耶路撒冷,僅規定耶路撒冷城內的基督教圣地為“國際共管區”,由聯合國進行托管,保證外國人可以自由出入。[9]然而,這個方案被外約旦政府拒絕了。[10]因為基督教圣地位于耶路撒冷的老城,屬于外約旦政府的占領區域。如果這些地方交由聯合國管理,外約旦軍隊就要被迫撤出。[11]這個方案維護了以色列的利益,卻要求外約旦單方面作出讓步,外約旦政府自然不肯接受。外約旦的阿卜杜拉國王是英美在阿拉伯地區的忠實盟友,因此以色列的新方案失去了英美的支持。[12]英美都要求以色列政府先征得外約旦方面的同意,務求制訂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案。[13]以色列政府通過新方案占領耶路撒冷的計劃破滅了。聯大召開之日臨近,為了廢除第181 號決議的相關規定,以色列政府轉而向蘇聯政府尋求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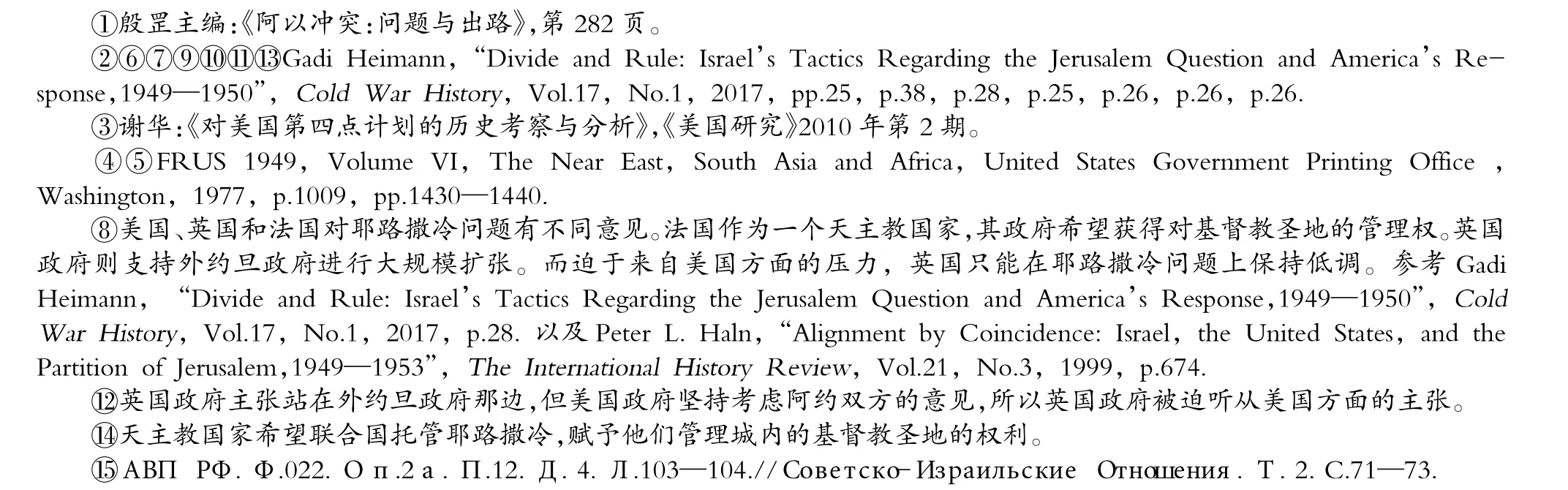
蘇聯政府此時仍堅持原來的立場:支持實行第181 號決議的規定,由各國代表委員會對耶路撒冷進行共管。而站在同一陣營的除了東歐國家,就是阿拉伯國家(外約旦除外)和大多數天主教國家。[14]后兩者是出于宗教原因,所以不會對以色列政府作出妥協。為此,取得蘇聯政府的支持變得格外重要。只要蘇聯不再支持第181 號決議的規定,東歐各國將會緊跟其后,這就大大降低了聯合國托管耶路撒冷的可能。[15]以色列駐蘇聯大使館的顧問阿里耶·列瓦維(Arieh Levavi)提議,以色列政府可以利用“俄國財產”,因為這些財產對蘇聯政府而言有著特殊意義。[1]這個建議很快就被采納了。以色列外交部長摩西·夏里特對蘇聯駐聯合國代表С.К. 查拉普金(С.К. Царапукин)說,如果聯大第181 號決議的規定被執行了,耶路撒冷表面上由國際共管,實際上被英美把控住。到時候,蘇聯政府連日常事務都很難插手,更別說接管當地的“俄國財產”了。蘇聯代表說,這兩個問題不應該混為一談。[2]對此,莫斯科方面沒有作出具體答復,或許是因為有著其他方面的考慮。例如,試圖借此打破蘇以雙方在“俄國財產”問題上的僵持。聯合國正式托管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政府就無法繼續占用“俄國財產”,這些財產的所有權要重新討論,那么蘇聯政府就能參與其中。而且,耶路撒冷一旦接受國際共管,英美很難將蘇聯的影響排除在外。如果蘇聯政府真的打算繞開以色列政府來解決“俄國財產”問題,那就意味著以方的態度為莫斯科方面所不喜,蘇聯政府正在重新思考對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自以色列建國以來,蘇以雙方的關系并非毫無芥蒂。此前,雙方針對蘇聯國內猶太人移居以色列的問題就產生了一些矛盾。以色列政府多次請求莫斯科方面批準蘇聯國內的猶太公民移居到以色列。當時蘇聯國內的“反世界主義”(Anti-Cosmopolitanism)運動甚囂塵上,蘇聯猶太人群體的生存狀況令人堪憂。“反世界主義”運動可以追溯到二戰結束后蘇聯政府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的政治清洗運動。1946 年8 月9 日,蘇聯政府對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等多個領域進行了大批判。[3]在蘇聯最高領導層的推動下,這場政治運動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并在1948 年達到了高潮。而蘇聯猶太人在政府文化部門擔任了大部分要職,難免淪為這場運動的主要受害群體。[4]蘇聯政府對以色列政府說,蘇聯國內不存在所謂的“猶太問題”,也沒有猶太公民提出移居國外的要求。[5]另一方面,蘇聯政府力圖杜絕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在蘇聯國內傳播的可能性。以色列駐蘇聯大使館經常散發有關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的宣傳資料。[6]蘇聯政府便下令監視使館人員的日常生活,嚴禁他們與蘇聯國內猶太人私下接觸。[7]這些消息陸續傳到了以色列國內,蘇聯政府的猶太政策遭到猛烈抨擊。[8]一時間,蘇聯國內的猶太人政策帶來的沖擊,雙方在“俄國財產”問題上的矛盾,還有“耶路撒冷之爭”引起的沖突,這些問題都使蘇以關系變得更加脆弱。
當蘇以雙方矛盾重重之時,美國政府忙于協調各方的利益,放松了對耶路撒冷問題的掌控。一份支持第181 號決議的提案進入了聯大投票環節。1949年12 月9 日,第四屆聯大通過了《關于耶路撒冷“國際化”的決議》,即第303(四)號決議。該決議重申了1947 年第181 號決議的原則,確立了耶路撒冷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在國際法層面否定了以約雙方的行為。[9]美國代表反對第303 號決議,斥之為“不切實際”的決議。[10]但是,蘇聯和東歐國家、阿拉伯各國(除了外約旦)以及大部分拉美國家都表示支持。[11]而有關“俄國財產”的交涉受此牽連,也立即被以色列政府叫停。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阿巴·埃班(Abba Eban)對美國駐以色列大使詹姆斯·麥克唐納(James MacDonald)談及此事,聲稱“大部分財產還沒移交,也不會再移交。”[12]這意味著以色列政府公開與蘇聯政府決裂了,雙方的合作關系無法維系下去。

四、蘇聯政府對以色列外交政策的轉變
1950 年3 月16 日,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向斯大林提議,蘇聯政府宣稱不再參與耶路撒冷問題的后續討論。約一個月后,4 月17 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Я.А.馬立克(Я.А. Малик)向聯合國提交了一份聲明,稱“蘇聯政府認為無法繼續支持聯合國大會的決議,相信聯合國能找出讓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法”。[1]АВП РФ. Ф.059. Оп.24. П.27. Д.154. Л.68—69.//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T.2. C.158—159.這個消息讓各國代表愕然。因為聯大第303 號決議公布之后,以色列政府將首都遷往西耶路撒冷,而約旦政府也宣布正式兼并東耶路撒冷。[2]1949 年12 月11 日,以色列政府決定將首都遷往西耶路撒冷。次日,約旦宣布正式兼并東耶路撒冷。以約分治耶路撒冷已成事實,為何蘇聯政府還作此聲明呢?
首先,冷戰以歐洲為中心迅速向近東地區擴展,加深了美蘇雙方關系的緊張態勢。從插手巴勒斯坦問題開始,蘇聯政府關注的就不是阿以雙方的勝負,而是美國政府在近東地區的政策動向。美國力圖在中近東建立區域性軍事-政治集團,使蘇聯政府對國家安全感到十分擔憂。1950 年3 月,蘇聯駐黎巴嫩和敘利亞大使Д.С.索羅德(Д.С. Солод)向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葛羅米柯提交了一份詳細報告。該報告稱,1950 年1 月份以來,英美在近東的斗爭越來越激烈,雖然美國嘗試掩飾這個問題,但英國在阿拉伯地區的行為經常受制于美國。[3]АВП РФ. Ф.0106. Оп.9. П.12. Д.1. Л.1,12.//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В. Наумкин. Т.1. C.114,C.114.據此,Д.С. 索羅德認為“美國人正在公開地將英國人趕出去,這首先發生在沙特阿拉伯、希臘、土耳其和伊朗,緊接著在埃及、敘利亞和黎巴嫩,以后將輪到伊拉克和約旦,直至美國政府完全控制整個近東。近東地區將變成美國的軍事基地,他們很快就會把矛頭指向蘇聯。”[4]АВП РФ. Ф.0106. Оп.9. П.12. Д.1. Л.1,12.//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В. Наумкин. Т.1. C.114,C.114.不難想象,這份報告引起了蘇聯政府對近東問題的重視,它預示著近東將變成美蘇對抗的新戰場,給蘇聯南部的領土安全帶來巨大威脅。1950 年4 月7 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 號文件出臺。該文件指出,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在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勝利,都是對美國及自由世界的挑戰。美國政府要幫助不發達地區和國家發展經濟,以免這些地方爆發社會運動,讓共產主義勢力有可乘之機。[5]謝華:《對美國第四點計劃的歷史考察與分析》,《美國研究》2010 年第2 期。通過這份文件,美國確定了在全球范圍內對抗蘇聯和共產主義擴張的政策。蘇聯政府面對美國方面的猛烈攻勢,只能利用近東的動蕩局勢反擊。作為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蘇聯在聯合國長期處于被動地位。而耶路撒冷問題提供了一個報復英美的機會,于是蘇聯政府便借題發揮,宣布不再支持實行聯大第303 號決議,讓聯合國尋求符合近東人民意愿的方案。
其次,以色列政府試圖利用美蘇矛盾,爭取來自雙方的援助,卻漸漸走上了“親美反蘇”的道路。建國之初,以色列政府試圖走一條“中立”的外交路線。但是這種設想很快就破滅了,以色列政府的“親美”傾向日益明顯。從1949 年開始,蘇聯駐以色列大使葉爾紹夫就向莫斯科報告,說以色列政府內部的“親美派”勢力十分強大。[6]АВП РФ. Ф.089. Оп.2. П.3. Д.10. Л.6,8—13. 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140; АВП РФ. Ф.089. Оп.3. П.6. Д.8. Л.211—226,262—26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47—51,140.其中,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里安就是“親美”路線的支持者之一。他曾經親自飛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商討以美兩國建立經濟與軍事合作關系的問題。[7]Avi Shlaim,“Israel between East and West,1948—1956”,,Vol.36,No.4,2004,pp.657—673.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政府急需來自美國方面的經濟援助。以色列政府鼓勵全世界的猶太人移居過來,使得外國移民的人數在短時間內激增。大批移民的涌入造成各種社會問題,以色列國內的經濟危機爆發了。應本-古里安的請求,美國猶太人發行了以色列債券,還提供一筆6500 萬美元的貸款,為以色列政府解決了燃眉之急。[8]阿倫·布雷格曼:《以色列史》,楊軍譯,東方出版中心,2015 年,第75 至76 頁。這些加深了蘇聯政府對以美關系的懷疑,導致蘇以關系進一步惡化。1950 年3 月10 日,蘇聯駐以色列大使葉爾紹夫向蘇聯外交部報告說,以色列政府在外交上的反蘇情緒很強烈。[9]АВП РФ. Ф.089. Оп.3. П.6. Д.8. Л.211—226,262—26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C.140,C.140.以色列政府禁止國內對蘇聯友好關系協會的活動,[10]АВП РФ. Ф.089. Оп.3. П.6. Д.8. Л.211—226,262—26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C.140,C.140.嚴格限制蘇聯文學作品的傳播。[11]АВП РФ. Ф.089. Оп.3. П.8. Д.1. Л.1,5—7.//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C.164.隨后,蘇聯國內報紙《文學報》發表了題為《特拉維夫的追隨者》的政論,嘲諷以色列政府打著“中立外交”的幌子,實則追隨美國政府的“反蘇反共”政策。[1]Прудков.“Гель-авивски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 Ачесона.”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5 март 1950.當以色列外交部長摩西·夏里特提出訪蘇,莫斯科方面也是毫不理會。[2]АВП РФ. Ф.059. Оп.24. П.52. Д.332. Л.199—200.//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C.188.所以,在宣布蘇聯政府不再干預耶路撒冷問題之后,蘇聯駐聯合國代表拒絕了以色列方面的邀約,以此表明蘇聯此舉并非為了幫助以色列政府。也許,蘇聯此舉是為了防范美國通過以色列控制耶路撒冷。因為以色列政府無視聯大決議,強行占領耶路撒冷,挑戰著聯合國大會的權威。而蘇聯的聲明再次強調了聯合國的調解角色,相當于宣告耶路撒冷問題仍然是“懸而未決”的,以約兩國政府的占領行為違背了國際法。
再次,阿拉伯各國強調美國勢力對近東的威脅,以此爭取來自蘇東國家的援助。二戰以來,蘇聯政府支持近東人民反對英法殖民統治,高度贊揚埃及、敘利亞與黎巴嫩的民族獨立運動,并將他們視為“進步的阿拉伯國家”。[3]劉競、張士智、朱莉:《蘇聯中東關系史》,第98 至99 頁。然而,受到當地條件的限制,近東民族獨立運動難以深入發展。由埃及政府倡導建立的阿拉伯國家聯盟結構松散,各成員國相互爭斗,無法達成統一意見。[4]1945 年3 月22 日,在埃及的倡議下,埃及、沙特阿拉伯、外約旦、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門7 個阿拉伯國家在開羅開會,成立了“阿拉伯國家聯盟”。而國內政治動蕩、社會秩序混亂的問題,始終困擾著埃及、敘利亞和黎巴嫩三國政府。[5]哈全安:《“肥沃的新月地帶”諸國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109 至110 頁。所以,對阿拉伯各國政府來說,最可怕的不是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威脅,而是國家政權岌岌可危的現狀。故此,利用美蘇對峙局勢、爭取更多的援助才是最符合實際的外交路線。1950 年4 月14 日,敘利亞財政部長對蘇聯駐敘利亞和黎巴嫩大使索羅德說,美國政府正在對阿拉伯各國政府施壓,迫使他們與以色列政府締結和約,從而構建近東的反蘇軍事集團,因此敘利亞政府急需來自蘇聯的援助。[6]АВП РФ. Ф.0128. Оп.13. П.12. Д.6. Л.69—74.//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В. Наумкин. Т.1. C.120—123.而埃及政府和黎巴嫩政府隨后也請求蘇聯提供援助。考慮到以色列政府的“親美”舉動,再結合阿拉伯各國對蘇聯代表的接近,蘇聯政府宣稱不再插手耶路撒冷問題并將其交給聯合國,可能是為了加深阿拉伯國家對英美近東政策的不滿,促使它們迅速地向蘇聯和東歐國家靠攏。蘇聯政府雖不參與討論耶路撒冷問題,但是卻密切關注著該問題的后續發展。而阿拉伯各國則更加積極地尋求蘇聯在外交、經濟和軍事上的支持。[7]殷罡主編:《阿以沖突——問題與出路》,第144、第152、第383 頁。也許在他們看來,蘇聯政府對近東事務的態度更開放了。
由此可見,蘇聯政府宣布退出“耶路撒冷之爭”,將其完全交給聯合國來解決,表明莫斯科不再幫助“親美”的以色列政府,并傾向于加強與阿拉伯各國政府之間的聯系。而蘇聯政府介入近東事務的程度不斷加深,也加快了英美控制中近東的步伐,致使近東地區的局勢惡化,并逐步變成“冷戰”的試驗場。
1950 年5 月,英、美、法三國外長在倫敦舉行會議,發表了關于中東局勢的《三國宣言》,宣稱準備以武力干涉中東事務。1951 年10 月,英、法、美、土耳其四國政府發表關于組建“中東司令部”的聯合宣言,要求中東各國共同對抗“來自外部力量的威脅”。“外部力量”指的就是蘇聯共產主義。英美試圖以此拉攏阿拉伯各國政府,將阿拉伯地區與土耳其相連,建立起中近東地區的反蘇軍事聯盟。[8]劉競、張士智、朱莉:《蘇聯中東關系史》,第136 頁。以色列政府也簽訂了美以合作協議,作為對“中東司令部”計劃的補充。[9]АВП РФ. Ф.059. Оп.26. П.58. Д.362. Л.81—8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C.309—311.但“中東司令部”的建立舉步維艱,因為阿拉伯各國拒絕與土耳其、以色列合作。可是,英美并沒有放棄這個設想,還推出了類似的計劃。為了抵擋英美的攻勢,蘇聯政府也考慮向阿拉伯國家提供武器。1953 年2 月份,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對蘇聯駐埃及大使說,告知埃及政府,莫斯科方面將考慮他們關于購買武器的請求。[10]АВП РФ. Ф.059a. Оп.7. П.13. Д.4. Л.40—41.//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В. Наумкин. Т.1. C.182.另一方面,蘇以雙方關系正在迅速地惡化下去。從1952 年到1953 年,蘇聯政府對國內猶太人的迫害再次升級。“斯蘭斯基案件”和“醫生間諜案”令國際社會嘩然,從而激化了蘇以雙方之間的矛盾。[1]以色列國內舉行聲勢浩大的反蘇游行,蘇聯駐以色列大使館也遭到炸彈襲擊。[2]1953 年2 月11 日,蘇聯政府宣布撤走駐以使館的全體人員,斷絕與以色列政府的外交關系。[3]此后,蘇聯政府拋棄了“中立”的立場,開始實行“親阿反以”的政策。
經過一系列風波,蘇聯政府接管“俄國財產”的計劃被迫延后。赫魯曉夫上臺后,蘇聯政府實行“和平外交”,著手改善與第三世界的關系。1964 年,蘇以雙方簽訂了有關買賣“俄國財產”的協議。該協議規定,以色列政府向蘇聯政府買下大部分財產,并以國內出產的柑橘來支付。[4]后來這份協議被稱為“柑橘協定”(Апельсиновая Сделка)。[5]該協議由雙方秘密簽署,實質是蘇聯政府對以色列政府占有“俄國財產”的正式承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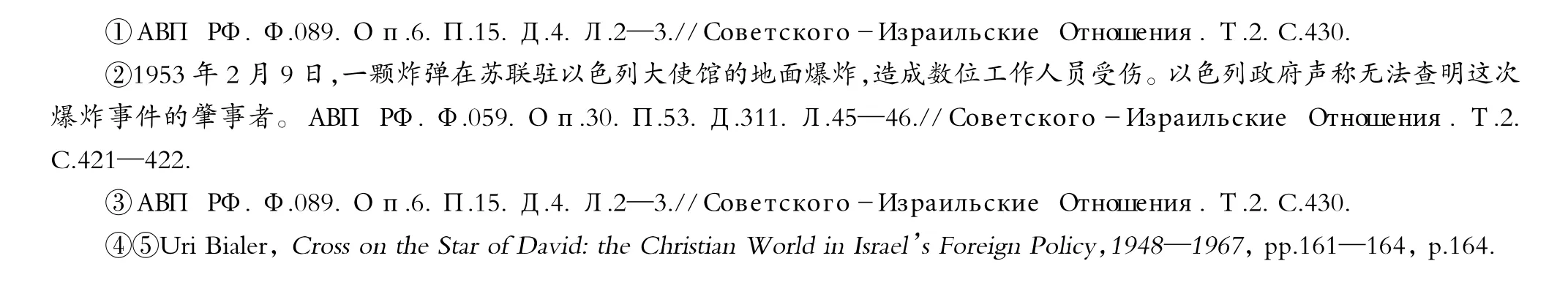
結 語
本文是對“冷戰在近東地區的形態及其特征”這一問題的回應。通過考察蘇聯、以色列雙方圍繞耶路撒冷的“俄國財產”接收問題的交涉,還有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國政府對耶路撒冷歸屬權的爭奪過程,以及美蘇兩大國對耶路撒冷相關問題的應對策略,筆者提出了兩點思考:
其一,近東地區“被卷入”冷戰并非一個完全被動的過程,而是蘇聯、美國、以色列與阿拉伯各國多方互動的結果。美蘇雙方在冷戰思維的影響下,將對方的近東政策視作對自身安全的威脅。他們力圖填補英國留下的權力真空,擴大在當地的影響范圍,為此對近東各國進行拉攏或施壓。而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國政府也正想借助大國的力量,一來有助于達成某些外交目標,二來也可以獲得援助并提升國力。于是,這些國家刻意渲染近東地區的冷戰氛圍,進一步加深了美蘇雙方之間的不信任與敵意,謀求從大國相爭之中漁人得利。在耶路撒冷問題上,以色列方面以“俄國財產”落入英美之手來要挾蘇聯方面讓步。當蘇方決定不再參與調解“耶路撒冷之爭”時,影響因素除了蘇方對蘇以關系、美以關系、蘇聯與阿拉伯各國關系的考量之外,或許還有埃及和敘利亞等國的慫恿。然而,近東各國政府謀取自身利益的行為,最終間接地加劇了美蘇在近東地區的敵對態勢。
其二,近東地區的冷戰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這與歐洲主戰場的情況對比可謂大相徑庭。其原因在于當地根深蒂固的傳統宗教思想。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擁有非常虔誠的宗教信仰,這直接造成雙方之間的沖突頻發,也導致耶路撒冷成為各國爭搶的“香餑餑”。而這種濃厚的宗教氛圍形成了一道“文化的屏障”,阻礙了美蘇對近東當地事務的過度干預。正如在調解“耶路撒冷之爭”的過程中,美蘇兩國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尷尬無力的狀況。又如蘇聯政府通過東正教教會代表到以色列接收“俄國財產”的多次嘗試都失敗了。如此一來,美蘇意識到很難利用意識形態輸出的手段擴大地區影響。近東地區在地理位置上遠離美國和蘇聯的本土,兩國政府也不會輕易往當地派兵。于是,美蘇只能選擇支持以色列或阿拉伯世界其中一方來加強自身影響力。這自然就給近東各國領導人留下了與兩大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空間,而美蘇從此也再難從近東問題中抽身。
盡管如此,冷戰仍然對近東的政治生態造成了深遠影響,某些當年懸而未決的問題一直延續至今,例如耶路撒冷的歸屬問題。在歷次的近東戰爭當中,耶路撒冷的歸屬問題都處于沖突的核心位置。以色列和約旦一直在擴建這座城市,使耶路撒冷的范圍持續擴大。聯合國則多次譴責以約分割耶路撒冷,否定這種占領行為的合法性。迄今為止,在耶路撒冷設立使館的國家只有美國和危地馬拉,其他國家的駐以使館都在另一座城市特拉維夫。近東地區的紛爭并未停息,和平共處之路仍崎嶇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