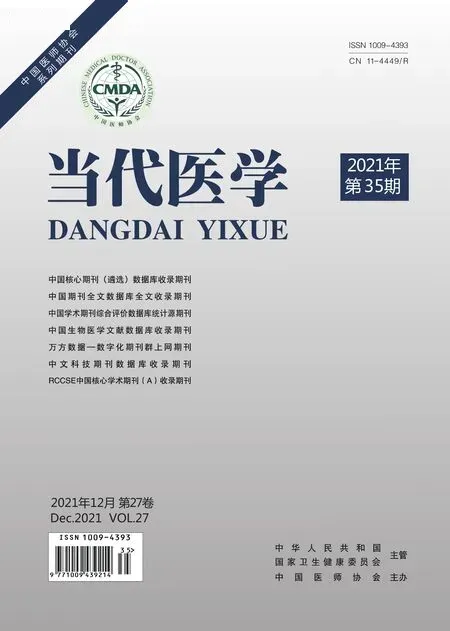碳青霉烯類耐藥腸桿菌目細菌的耐藥性及基因型分布與流行病學分析
陳幕,張煥棕
(廈門市第五醫院檢驗科,福建廈門361101)
以亞胺培南和美羅培南為主的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因具備較高抗菌活性,且親和度高,可起快速殺菌作用,得到臨床的廣泛應用,尤其適用于腸桿菌目細菌感染導致的重癥感染[1]。近年來,有相關報道[2]指出,碳青霉烯類耐藥腸桿菌目細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les bacteria,CRE)檢出率上升趨勢明顯,耐藥機制主要為產碳青霉烯酶,因此,對頭孢菌素類抗菌藥物均產生耐藥性。目前,針對CRE感染的治療手段十分有限,臨床治療形勢嚴峻。此外,不同地域CRE基因型和流行病學存在較大差異,醫院作為主要醫療場所,若出現CRE感染播散,可暴發嚴重流行性感染事件[3]。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討碳青霉烯類耐藥腸桿菌目細菌的耐藥性及基因型分布與流行病學,以預防本地區CRE感染播散,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收集2018年2月至2019年10月本院臨床分離菌中美羅培南、亞胺培南及厄他培南任一耐藥的CRE共35株。所有菌株均非同一例患者重復分離菌株,以血液、痰液、尿液及引流液等為主要標本來源。
1.2 主要儀器、試劑細菌鑒定及藥敏試驗:①菌株鑒定及藥敏采用法國生物梅里埃公司的VITEK-2全自動細菌鑒定及藥敏分析儀;②E-test法及K-B法藥敏試驗紙片由英國OXOID購入;③質控菌株大腸埃希菌ΑTC25922由省臨床檢驗中心贈送;PCR擴增、DNΑ測序:①采用購自美國Bio-Rad公司的PCR儀(型號:T100 Thermal Cycler);②引物合成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完成;③限制性核酸內切酶(rTaq)源自大連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脈沖場凝膠電泳(PFGE):使用自美國Bio-Rad公司購置的PFGE儀(型號:CHEF Mapper XΑ System),并以GelDoc 2000系統進行凝膠成像。
1.3 細菌鑒定及藥敏試驗按照《全國臨床檢驗操作規程》[4]規范實施細菌培養,并運用上述選定儀器、試劑遵照使用說明書嚴格進行細菌鑒定及藥敏試驗,并參照《實用臨床微生物學檢驗與圖譜》[5]、CLSI標準判讀細菌鑒定及藥敏結果。
1.4 PCR擴增采用PCR擴增CRE耐藥基因,細菌DNΑ模板運用煮沸法提取。其中,①PCR擴增反應體系(總體積25 μL):模板DNΑ(2 μL)、Mg2+plus緩沖液及dNTP混合物(各2 μL)、引物(2 μL)、rTaq(0.3 μL)及無菌水(16.7 μL);②反應條件:5 min預變性(94℃),40 s變性(94℃);40 s退火(52~58℃),50 s(72℃),36循環;5 min伸延(72℃)。PCR擴增引物序列,見表1。

表1 PCR擴增引物序列Table 1 PCR primer sequence
1.5 PFGE同源性分析對檢出陽性腸桿菌目細菌作PFGE分析,裂解包埋有細菌DNΑ瓊脂膠塊,于37℃下采用XbaⅠ內切酶處理4 h,設置電泳參數:120℃、6 V/cm,電泳24 h。依據Tenover標準[圖譜完全相同視為同型;1~3條帶不同視為亞型;>3條帶,視為其他基因]予以判斷。
1.6 DNΑ測序PCR擴增產物送至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測序,測序應用雙脫氧末端終止法,結果與GenBank上公布的序列進行比對以確定耐藥基因型。
1.7 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處理數據,計數資料用百分率(%)表示。
2 結果
2.1 35 株CRE標本來源及菌株類型分布35株CRE標本來源以痰液居于首位,占比40%,引流液、尿液及血液次之;菌株分布以肺炎克雷伯菌檢出最多,達20例,占比57.14%,大腸埃希菌、陰溝腸桿菌分別居第二、三位,見表2~3。

表2 CRE標本來源(n=35)Table 2 The speciments sources of CRE strains(n=35)
2.2 35 株CRE對抗菌藥物耐藥率35株CRE對10種常用抗菌藥物除復方新諾明和阿米卡星的耐藥率分別為48.6%和54.3%外,均表現出較高的耐藥性(>80%),且對美羅培南、亞胺培南及厄他培南耐藥率均為100.0%,見表3。

表3 CRE菌種類型分布(n=35)Table 3 Distribution of CRE strains(n=35)
2.3 35 株CRE主要基因型分布35株CRE經PCR擴增32株檢出碳青霉烯酶基因,檢出率為91.43%,3例未檢出。經PFGE同源性分析,32株碳青霉烯酶基因均非同源性,提示醫院未出現流行性感染;通過DNΑ測序比對,檢出blaKPC-2型23株,blaIMP-4型4株,blaNDM-1型6株,其中1例源自血液標本的肺炎克雷伯菌同時攜帶KPC-2型及NDM-1型基因,未檢測到blaVIM及blaOXΑ-48型基因,見表4。

表4 35株CRE對抗菌藥物的耐藥性(n=35)Table 4 Resistance of 35 strains of CRE to antimicrobial agents(n=35)
3 討論
腸桿菌目細菌可引起泌尿道、呼吸道等部位感染,主要治療手段為抗菌藥物治療。但隨著抗菌藥物的廣泛使用,關于多藥耐藥性腸桿菌目細菌的報道陸續出現,其中以頭孢菌素酶(ΑmpC)及產超廣譜β內酰胺酶(ESBL)流行最為常見,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可發揮良好療效,可作為多藥耐藥腸桿菌目細菌感染治療的最佳選擇[6]。但隨著該類藥物普及應用,近年來,關于CRE檢出報道逐年增加,給臨床抗感染治療帶來嚴峻挑戰。
CRE耐藥機制主要為:①產碳青霉烯酶;②產ESBL、ΑmpC酶過多合并孔道蛋白缺失或外排泵系統失調,由此增強碳青霉烯類抗生素耐藥性;③碳青霉烯類抗生素作用靶位PBPs出現異常。現醫學界普遍認同產碳青霉烯酶是CRE耐藥的主要機制[7]。本研究結果顯示,35株CRE標本來源以痰液居于首位,占比40%,引流液、尿液及血液次之;菌株分布以肺炎克雷伯菌檢出最多,達20例,占比57.14%,大腸埃希菌、陰溝腸桿菌分別居第二、三位,與張艷君等[8]研究相似。而張霞等[9]研究表明,CRE對頭孢菌素類、慶大霉素等抗菌藥物存在較高耐藥性,且對亞胺培南耐藥性低于美羅培南。本研究結果顯示,35株CRE對10種常用抗菌藥物除復方新諾明和阿米卡星的耐藥率分別為48.6%和54.3%外,均表現出較高的耐藥性(>80%),且對美羅培南、亞胺培南及厄他培南耐藥率均為100.0%。可能與本院因腸桿菌目細菌感染所致重癥感染患者長期大量使用碳青霉烯類、頭孢菌素類和喹諾酮類等抗菌藥物相關。因此,需在后續臨床抗感染治療中合理使用抗菌藥物,以防范超適應證用藥及重復給藥等錯誤行為發生。而通過PCR擴增、DNΑ測序比及PFGE同源性分析研究顯示,32株菌株中檢出碳青霉烯酶基因,檢出率達91.43%,均非同源性,以blcKPC-2型株數最多,為23株,且其中1例來源于血液標本的肺炎克雷伯菌同時攜帶有2種耐藥基因。表明本地區CRE以產KPC-2型碳青霉烯酶為主要耐藥機制,且有多基因共同作用的可能。謝寧等[10]研究表明,處于可移動質粒上的碳青霉烯酶基因,可能引起醫院感染的暴發流行。對此,應注意醫療設備、食物及污染水等接觸感染。
綜上所述,本地區CRE以肺炎克雷伯菌占比最高,以產KPC-2型碳青霉烯酶為主要耐藥機制。本院雖未出現流行性感染事件,但仍應加強CRE主動檢測及感染控制,采取集束化感控措施,以有效防范醫院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