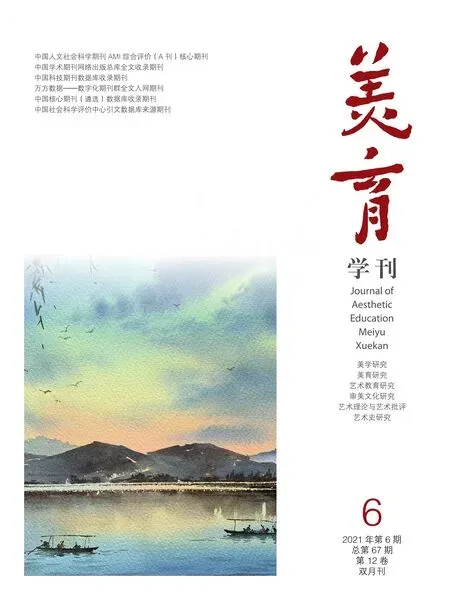藝術生產的智能化變革
——微軟“小冰”作品《我知我新》批評
單小曦,黃凌伶
(杭州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1121)
在人工智能(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術的加持下,人類的文藝生產方式進入了新的發展時代,人們對藝術的理解也不斷突破原有模式和框架。由微軟(亞洲)互聯網工程院設計開發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微軟小冰已經更新到了第八代,目前已發展成為以情感計算為核心的完整人工智能框架。“她”不僅是“詩人”,是“畫家”“設計師”“主持人”,還是“歌手”和“音樂家”。2016年7月,微軟小冰登陸bilibili創作平臺,至今已發布視頻50多個,累計播放量達到70萬余次。小冰的百度搜索指數日平均值在1千以上,最高達到2萬以上。從這些數據中可以看出,人們對小冰藝術“創作”的態度逐漸從質疑和好奇轉為接受和欣賞。
美國計算機學者斯圖爾特·羅素和皮特諾·維格曾在《人工智能:一種現代的方法》一書中將智能實現分為四個維度,一是“類人思考”,二是“類人行動”,三是“理性地思考”,四是“理性地行動”。[1]目前,在滿足大眾精神文化需求的新道路上,人工智能文藝的確在沿著這四個維度發展著。然而,AI是否需要像人一樣思考和行動?小冰的藝術創作能否被稱為“藝術”?本文立足于小冰歌曲《我知我新》,研究其技術框架,呈現人工智能音樂創作的技術邏輯,從人工智能文藝應具有的獨立性出發,反駁人文主義者對人工智能文藝的偏見和批評,論述智能體從人類藝術的創作工具轉變為藝術實踐“類人主體”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問題。
一、AI歌曲生成的“技藝”框架
根據微軟第六代微軟小冰發布會,小冰已完成Deep Neural Networks(深度神經網絡)模型第四次迭代升級,克服了此前無法對時間序列上的變化進行建模的缺點。接受海量云端音樂大數據的訓練后,小冰能夠自行學習并計算情感表達的合適強度,輕松駕馭各種風格歌曲的演唱,幾乎達到行業內虛擬歌手的最高素養。2017年,“知乎”構想“知識×計劃”,與微軟公司進行跨界合作。微軟亞洲互聯網工程院發布了與知乎知識青年聯動的新單曲《我知我新》,由微軟小冰作詞作曲并演唱。作為此次升級的示范性作品,《我知我新》彰顯出與以往發布歌曲截然不同和領先行業的技術元素。
首先表現在作詞框架上。《我知我新》歌詞包含四個樂段:
他們都順應潮流/他們問為什么改變/青春灼灼花樣翩翩/卻不向前/當世界還在變遷/若時間無垠/若探索無邊/認知就不再有極限
我在我主場/世界就任我去狂想/我知我新/未知的世界那么驚艷/哪怕有傷/滿手泥濘還眼神發光/當我身處困境/也要像跑在叢林
急風驟雨的前路/人潮洶涌的江湖/我問我答我聽我想/不懼怕來日方長
不跟隨的一個我/是倔強的鯨和自在的鳥/不妥協的一個我/是沙漠的舟和獨特的島/很有趣的一個我/是山川的海和海底的草/很好奇的一個我/晝夜四季輪轉/現在我知我新
就這四個樂段歌詞的編寫,小冰首先利用LSTM的seq2seq模型(1)LSTM(Long Short-Term Memory)是一種長短期記憶人工神經網絡,屬于循環神經網絡,可處理時間序列的數據。Seq2seq(sequence to sequence)是一種自然語言處理的序列模型,解決了傳統的固定大小輸入問題。,學習千萬行以上的歌詞語料。由于seq2seq模型對自然語言處理水平較高,小冰作詞的輸入輸出間距比過去大大縮短,能夠在不超過半小時的時間內通覽知乎站內所有的內容,比如“2018全新品牌視頻”,知乎官方發布的信息,以及用戶公開的實時問答和想法,等等。接著處理不同輸入點和輸出點之間的信息,分析出知乎用戶“新知青年”的構成和特征,搭建歌詞主體“我”的形象。如第一樂段“他們問為什么改變”,展現了知乎青年與一般人眼中庸常年輕人的不同。開頭寫“他們都順應潮流……認知就不再有極限”,以“他們”為觀察點,講述庸常年輕人的從眾和守舊,同時由“他們”引出“我”。“我在我主場/世界就任我去狂想……”寫出青年人應有的立場和奮斗歷程,每一句都使用了情感色彩鮮明的詞匯,如“狂想”“驚艷”“哪怕”“發光”“跑”等,處處洋溢著熱血青年不服輸、敢冒險的意氣。
完成了詞境主人公形象塑造之后,小冰模擬人腦的神經結構,學習樂曲或歌詞數據中的符號及與之對應的抽象意義,根據某種意義反推其具象符號,篩選能調動人們視覺、聽覺、觸覺等感覺器官享受的詞句,以喚起人們無論是身體還是心靈的全方位共鳴。第三樂段中的“疾風驟雨”“人潮洶涌”,營造使人身臨其境的鮮活立體畫面。聽眾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文本空間中的風雨、驚雷,焦躁煩悶的心情不自覺升起。此時,宣誓一般的四個“我”的連用,打破了惡劣環境的桎梏,以獨立沖鋒的意志和自我堅守的精神不斷前進。審美主體也從焦慮轉為奮勇。第四樂段是主旨樂段,其文學品味在四個樂段中為最高,主要表現為修辭的運用。小冰借助象征和排比,從“不跟隨”“不妥協”“很有趣”“很好奇”四個角度分別闡釋這種精神品質在現實世界里對應的具體意象。鯨魚飛鳥、荒舟島嶼、山川海草等意象優美,表現了年輕人崇尚并追求新事物的特征。此外,每個樂段都設置了各不相同的韻腳,每樂段內部的換韻頻率也不相同。第一樂段每句都押“ian”韻,第二和第三樂段都是每兩句換一次韻腳,形成錯落搖曳之美。第四樂段則除了高潮末句,跨“……的一個我”句式押“ao”韻。韻腳雖多,卻不至于俗濫黏膩,使審美主體通過聲韻感受青春韶華的跳躍和瀟灑。
其次表現在作曲框架上。《我知我新》的樂曲同樣是通過算法生成的。小冰運用的算法是對現有音樂的切片和重新排序的方法,其實這也是傳統聲樂創作的重要方法。這種分割和重新排序的過程與其說是一種生成過程,不如說是一種隨機生成過程。它修改現有的音樂,而不是從頭開始創作新的音樂。因此,算法本身是一個嚴格的基于規則的創作機制。
可以對這樣的算法過程作一個簡要的描述。第一步,小冰在程序中編寫一個音符列表(相當于音樂段落)。每個音符包含三個屬性:音量、音高和八度。然后,在正在組成的列表的開始處為每個音符的音量、音高和八度指定一組發生概率,并為列表的結尾指定另一組發生概率。同時,程序根據作曲者的輸入判定編寫多少個音符,以及音符每個屬性從其起始狀態到結束狀態的加速度。對于編寫的每一個音符,程序都會自動詢問它在列表始末中所處的位置,并根據它的每個屬性中已被指定的加速度,計算一組瞬時概率(在此時刻選擇給定音符的概率)。一旦計算出瞬時概率,程序將根據這些概率隨機選擇一個音符,前進到列表中的下一個點,并不斷重復該過程,直至列表的結尾。程序輸出的是一個音量、音高和八度的有序列表,該列表展示了從開頭到結尾的屬性的指定進程。最后,該列表被轉換為合成或記譜的格式,如MIDI格式。(2)參見Xenakis, I. Formalized Music: Thought and Mathematics in Compos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2.pp.110-130。
算法的結果是,《我知我新》前兩個樂段節奏和力度強勁,以電鋼琴和鼓的擊打聲為背景。這是因為小冰基于對知乎論壇氛圍的感知,對廣大知識青年得出“搖滾”“朋克”的印象,故而以極具質感和青春色彩鮮明的金屬樂聲為主旋律。但架子鼓的強度有所弱化,與人類世界較為浮夸的搖滾樂相比,其節奏和力度更加平和。第三樂段以近乎RAP的形式過渡,旋律淡化,節奏轉快,大有縹緲入云之感。不穩定的尾音滑向下一樂段的首音,承接自然,巧妙圓融。第三和第四樂段的銜接之處,曲調向高音方向大幅度上行,音頻振幅階梯式提高,節奏瞬間增強,各種金屬音交織翻滾。在四次循環往復后,曲調戛然而止。數秒后,又響起了最開始的旋律,與歌詞“不懼怕來日方長”形成呼應,象征青年的初心和志向永恒不變。
再次體現在歌唱聲音框架上。在訓練聲音顆粒度并統一聲區之余,小冰對聲音進行了許多人性化的處理,例如自動預測合成換氣聲,為最終效果添加感染力。這種換氣技巧屬于適配第八代小冰框架的歌手軟件X Studio的成果。該軟件由Wave Land Team發布,是全球同類軟件中第一個支持云端更新的軟件,具備深度網絡學習引入的自注意力機制和判別模型。音樂人將樂譜和歌詞導入X Studio后,其中的虛擬歌手會根據樂譜和歌詞信息,計算出一系列的聲學特征,決定用什么樣的力度和長度換氣,從而調整前后的譜參數,保證自然的音高起伏。《我知我新》的每句歌詞開頭或結尾都有微弱的換氣聲,在第四樂段每兩句的相接部分尤為明顯。此外,小冰沒有機械地劃分層次設定換氣位置。如第三樂段“我問我答我聽我想”和“不懼怕來日方長”之間沒有換氣聲,而其他地方大都一句一換氣。這是因為這兩句的節拍數增加,旋律更緊迫,缺少停頓空間。此處換氣會中斷兩句節拍的銜接。這種換氣技巧對于人類高水平歌手而言,也是難以達到的。X Studio軟件還支持小冰進行轉音、顫音等多風格裝飾性演唱。作曲者可通過開放的音素參數調教、音高參數精調等功能,以錨點繪制的方法,對發音增加控制,生成轉顫音,并調整轉顫音的起伏,使音符與音符間的過渡更加連貫,大幅度提高平順度。如果想要達到更深切的真實感,還可以運用畫筆工具在音頭和音尾改變音高線,以實現收緊嗓音的效果。轉音可見于第二樂段每兩句開頭的第四個字“主”“新”“傷”“處”,以及第四樂段的“一”和每個形容詞的首字(倔、自、沙、獨、山、海)。小冰對這些音符作了節拍重音和轉音處理,加強了起承轉合的節奏感。顫音主要出現在每句句末,如第三樂段中“不懼怕來日方長”的末音“長”,第四樂段“現在我知我新”的末音“新”。它們由快速交替的升降音符構成,以主音符結尾。由于顫動幅度和頻次較低,小冰的顫音容易被誤解為振動時間的簡單持續。這種唱法刻意切分了節奏,使韻律變幻莫測,情感張弛有度。
和聲為《我知我新》增添了豐富的層次感。在和聲技術方面,小冰能搜索相同或相似的曲目,分析這些曲目的所有和聲變化,并在具體的MIDI中找出每一個和聲序列發生的頻率,然后通過概率決策組成和聲的級數,以相同的比例生成該曲的和聲序列,自動判斷哪些位置需要構成多聲部。換言之,小冰框架充分學習人類世界的樂曲庫,提取和存儲和聲這一關鍵特征,按照要求輸出有類似特征的新歌曲。《我知我新》僅出現了一處和聲,即最后一句歌詞“現在我知我新”。該句中,除了明顯的高音層之外,還可以聽到充當和聲的兩層低音聲部。多層聲部打破了橫向運動的單一聲部形式,擴張了歌曲的縱向空間,形成一種類似空谷回聲的縹緲感。此外,“我知我新”的三層音并不重疊,而是呈時間上的梯度交錯,仿佛海水漲到最高處,逐漸降落,退潮平息。
二、傳統人文主義藝術觀念對AI創作的質疑
毫無疑問,小冰的《我知我新》充分展示了AI技術在藝術創作方面的成就,但文藝理論與批評界常常將小冰這樣的AI創作視為數字計算的結果,站在人文主義立場質疑AI藝術是否算是真正的藝術。換言之,在很多人看來,基于數字技術的AI藝術創作徹底打破了那些習以為常的藝術規則和慣例,打破了那些理所當然的美學意義和價值。在傳統的美學和藝術理論視野中,AI創作有違藝術創作的“本質”。情感和具身感受、創造力和想象力以及主體性這些核心概念,在AI“藝術”制品中已不再有效。不僅在大多數保守學者那里存有這種觀念,甚至很多前沿研究者也有著類似看法。比如超文本理論先驅喬治·蘭道(George P.Landow)曾不無擔憂地指出,可計算文藝缺少主體經驗。[2]機械倫理學學者帕特里克·林(Patrick Lin)采用倫理視角去探究人工智能文藝,認為AI藝術將冷冰冰的技術理性無限放大,是對人類藝術的威脅。[3]
確實,按照傳統人文主義的藝術理論范式,藝術生成的兩大基本要素是情感和具身感受(具身性),而這些要素在目前的AI藝術創作中幾乎是完全缺失的。AI藝術的否定派通常就是從這兩個密切關聯的方面提出質疑,得出AI藝術并非藝術的結論。音樂和其他絕大多數能被稱為藝術的事物首先是情感的產物,最著名的表述莫過于華茲華斯的浪漫主義美學宣言“一切好詩都是詩人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在當下這個基本上只能實現弱人工智能(ANI)的階段,人工智能體的“智能”更多地還展現在特定邏輯、符號識別、實用工程、精準技巧等“智能”方面,而展現情感、情緒方面的“智能”則非常薄弱。
小冰團隊原本對小冰的定位是“以情感計算為核心的完整人工智能框架”,但小冰在歌曲《我知我新》中對人類情感的表達既有局限又缺乏靈活度。歌詞中“他們都順應潮流/他們問為什么改變”二句突出了小冰反思庸常青年人的立場,她的確在此為人們標畫出不隨波逐流、追求改變、面向未來等宏觀的愿景和目標,但“她”沒有計算出人性在自由和妥協的天平上難以抉擇的復雜心緒。就人類而言,自由追求和任意改變常常會滑向任性的泥潭,現實中的復雜性較大程度上超出了小冰的情感計算框架。而在旋律方面,基于數字運算和處理所造成的過于規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作品情感的單薄性和幼稚化。通過聲道波形圖可以看出,激昂進取、不畏艱險的情感層層遞進,在高潮處徹底爆發,并在最強音處以波狀結束(如圖1所示)。全曲仿佛愈升愈高的階梯,缺乏“一波三折”的復雜感和曲折度,可謂激情有余而戲劇性不足,難免流于簡單和表面。根據《我知我新》的情況看,AI創作的歌曲可能在藝術表現上更類似于大多數游戲背景音樂而非電影配樂。因為AI音樂表現出缺少戲劇化的樂音曲線進路,沒有展現出類似電影的戲劇化情緒曲線,更接近許多游戲背景音樂那種從低到高線性推進的一般設定。

圖1 《我知我新》背景音左右雙聲道波形圖
所以,若以人類情感為衡量指標,人類復雜的情感并沒有被AI藝術很好地表現出來,多數情況下只是AI通過算法模仿出人類情感并外化成藝術文本而已。從人文主義的藝術理論范式來分析,這主要是因為AI由機械的、程式化的算法邏輯所決定。AI藝術所匱乏的不僅僅是情感,更有產生情感所必需的對于世界的具身感受以及與此息息相關的生命意識。AI不具有能夠像人一般“感受”的具身性,它與世界的接觸和聯系,它對于世界的反映和對于自身的表達,都無法像人類一樣,自然也就難以真正去“情動”。而根據分析哲學家約翰·塞爾(John Searle)的觀點,“程序不是心靈,它們自身不足以構成心靈”[4],硅基機器無法產生碳基生命那樣的意向性,AI也就不可能進一步具備生命意識。
在人文主義藝術理論看來,除去情感和具身感受,那種內在包含著想象、靈感等各種審美主體性要素的創造力,也尤為重要。即使小冰作詞作曲的策略和技巧再精妙,其缺乏人類作者那樣的創造力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可以看到,在小冰創作的不同歌曲中,象征手法的使用頻率相當高。例如《桃花夢》中頻繁出現的“霧”“雨”“風”“煙”,皆暗示夢境與往事;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云端峰會主題曲《智聯家園》中“星河”意為未來的征程,“天梯”指代人工智能。而在《我知我新》第四樂段,更是將運用了象征手法的每句歌詞組成一個排比片段,使青春意氣具象化,解除了此前的“人潮洶涌……”這一片段產生的壓抑感。然而,由于對意象所作的繁多甚至冗余的陳述,歌詞拼湊雕琢的痕跡突出,整首歌曲的創新性反倒被削弱了。另外,第二樂段最后一句“當我身處困境/也要像跑在叢林”,實際上是有語病的。“身處困境”和“像跑在叢林”無法銜接,使聽眾不知所云。由前文對小冰作詞框架的描述便可知,“困境”和“叢林”正是小冰依照詞義相關度刻意拼湊的結果。換言之,以人類審美標準看,小冰的創作還很粗糙,也很幼稚。
究其根本,是因為小冰對音符和語詞的創作依托于一種創建音樂作品的數字拷貝方法——采樣。無論是單一的鼓聲、復雜的旋律還是各式語詞,小冰都可以利用采樣捕捉音樂史上經典歌曲的每個組成部分,以便后續單獨播放和操作,而具體操作包括改變樣本的速度、音高或音長,進行循環、分層、添加、消除或增加背景噪音等。從聲音到歌詞的一系列樣本的采集,可以使跨流派、跨時空的作品都被融入一部全新的作品中,近似于一幅拼貼畫,但AI拼貼的質量無法與人類充滿靈性的創作相比。這是因為從決定性環節來說,AI創作的質量取決于“輸入”。所謂輸入,即電腦算法傳導過來的數據,包括對過去事實、事件的知識和曾作用于創作對象的諸多技藝,是有限且已知的。人類的藝術創作思維其實也是如此,藝術想象力總是來源于知識、記憶和經驗,藝術創造在某種意義上總是對過去的再創造。但是,小冰的創造力、想象力雖然與人類有相似或者說模仿之處,卻總是被批評不具有創新色彩。并且批評者斷言,運算程序不能創造任何新事物,只能以不同的方式在總數據庫中篩選組合,其結果有時會引起人類的驚嘆,但更多時候則純屬低質量的重復創作。不得不承認,如有的學者所言,AI藝術創作尚不完善,獨立性不強,缺乏真正的想象力,“比起人類感性的想象力而言更多是理性博弈的結果”,并且“沒有個人好惡之分,它并不能劃定想象范圍、選擇想象方向”,而“人類的想象力并不會具化成軌跡與策略,因為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博大精深,意識與潛意識處在隨時轉換的活躍狀態中,有時候創作者的靈感往往只存在于一瞬間”。[5]
其實,關于小冰《我知我新》這樣的AI藝術創作所引發的巨大非議,無論是情感和具身感受等方面,還是創造力與想象力等方面,都可以歸結為藝術創作的人類主體性問題。而在考察AI藝術創作所帶來的問題時,美學與藝術理論歷史脈絡中曾經關于“藝術終結”的討論似乎會伴隨著這種藝術創作的主體性匱乏再次凸顯出來。就像有學者所強調的,藝術終結的四種模式:在黑格爾那里終結于本體,即終結于對理念的顯現;在丹托那里終結于自我,即藝術敘事模式的更迭;在波德里亞那里終結于媒介,即藝術蛻變為無意義的能指符號;在卡斯比特等人那里終結于生活,即生活與藝術的同一。現在,在人工智能的作用下藝術終結不再是藝術內部的嬗變,而是針對整個人類藝術存在,人工智能藝術的出現提供了新的藝術終結模式——藝術終結于主體。[6]也就是說,在世界上的“存在者”中,藝術曾被視為專屬于人類的領域,只有作為主體的人類才能從事這種高級精神活動,如今AI改變了一切。由此可以引出一系列值得探討的問題:《我知我新》是否必須符合人類偏好才能成為藝術?AI技術所能實現的排列組合是否能稱得上是藝術?AI藝術創作是否需要接受人類主導的審美模式的審判?這些問題并非一時能獲得定論,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拓寬了人工智能藝術的問題域。
三、作為獨立性存在的AI藝術
實際上,作為藝術創作智能體的小冰并非必須模仿人類創作主體,AI藝術也并不需要以人類藝術為衡量標尺,或許可以有不同于人類藝術的獨立性,只不過這種獨立性的獲得可能無法完全杜絕爭議,并伴隨著AI藝術的演化而逐漸確立。
眾所周知,文藝復興時期以來,人文主義思想是藝術發展的圭臬。人文主義藝術觀念中,藝術或者被作為主體的人對世界的模仿、再現,或者是人的心靈、情感的主觀表現。18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西方主體性哲學突出人的理性精神,康德等德國古典哲學家將人之為人的根本確立為“自由意志”。美學上強調人的想象力和審美自由性。文藝理論上,先有浪漫主義者主張文藝是心靈、情感表現,再有克羅齊等表現主義者主張藝術即直覺,直覺即表現。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學說則向主體深層意識挖掘,強調藝術是個體“力比多”的升華。這一歷史時期和稍后的20世紀下半葉,還出現了文本論和讀者接受論流派,盡管具體觀點各異,但終極衡量尺度仍然沒有離開人的主體審美能力。(3)文本論極端觀點主張清除“作者”“讀者”的所謂“意圖謬見”和“感受謬見”,但多數論者的觀點中最終還是沒有離開作者和讀者的主體審美創造力。
后結構主義、后現代文論對人文主義思潮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和宏大敘事模式進行了解構和批判。后人類理論則提出立足后人類文化,建構“克蘇魯紀”學說[7]、“普遍生命力”哲學[8]等主張。后人類理論的出現,改寫了人的定義,改變了傳統的人性觀,進一步瓦解了人文學科的人類中心主義。而人工智能作為后人類最顯著的表征之一,激發的是關于人的境遇和命運的完全不同的思考。如果說信息模式被視作生存的常規狀態,那么在此意義上身體存在與機器人存在沒有本質區別,這也就從根本上增強了AI創作形成未來藝術之焦點和常態的可能性。目前,AI藝術研究也隨著AI自身的發展和理論探索而悄然興起。當一些人用“意識”“情感”等問題來剝奪AI藝術的合法性時,其實仍舊囿于人類中心主義。但正像當代藝術的一條重要路徑最終走向了觀念藝術,AI藝術也是完全可以擁有一種挑戰傳統的前衛身份的。就有學者提出,AI藝術是一種極具探索性的觀念性藝術,挑戰了人們目前對既有藝術形態與觀念的理解:不需要類似于人類的“生活經驗”表達;思想或概念成為可形式化進而可編程的代碼;挑戰了人類藝術家的“創造性”主體地位。[9]不管怎樣,AI藝術已經提醒我們,在原本僅僅強調對情感進行表達、對世界進行體認的專屬于人類的藝術領域,還有“另一條道路”的存在,讓我們可以暫時性地跳出“主體”的限制。
當我們帶著將AI藝術看作處于人類主體性之外的獨立性存在的觀點,回到《我知我新》這樣的作品會看到,小冰的創作按照人類藝術的創作標準雖然是有很多局限和粗糙之處,但又初步展示出了AI藝術自身非常具有價值的特點,以及建構以AI為主的新型藝術體系的可能性。首先,AI藝術的新型主體是“智媒介”。這是因為它具備將世界上所有事物數據化和信息化的技術力量,顛覆傳統人文主義的思想與審美,從而脫離限制性的人類視角,作為非人類成員的形態或身份,在人類主導的世界中獲得位置,同時成為藝術表達的另一個中心。然而,這個建構過程并不像后人文主義者想象的那樣簡單。微軟小冰是大眾較為熟悉的AI,但它只處于弱人工智能的高度。根據前文對《我知我新》的技術分析,小冰的創作是分裂的,即小冰強行融合了“人類”與“后人類”這兩種特征。《我知我新》創作程序有著廣義“后人類”的智能特性,但創作內容完全合乎“人類”的審美標準。這說明小冰雖然可以自我學習和訓練,但還不能進行真正的自我探索,只是按照人類的設計和指示進行藝術生產,因此《我知我新》這首歌曲顯得十分人性化,甚至可以被看作人類通過小冰參與了創作。總的來說,小冰本質上是根據人類的目標、價值觀和信仰被塑造出來的部分“擬人”的機器程序,而真正獨立于人類的智能體仍有待實現。
其次,AI藝術創作的各項機能遠超當代所有的人類創作。原因在于AI的“智媒介”特性,似乎一切事物屬性都可轉化為計算機信息被上傳、下載和共享。以情感和智力為例,IBM托馬斯沃森研究中心的AI音樂研究員艾比奧盧(Kemel Ebcioglu)認為,人類的復雜情感與智力不過是對客觀事物的反應的綜合,是現實世界中知識與經驗的附屬。[10]這種邏輯關系遵循了一種趨勢,即認為人的情智是寫在大腦中的信息模式。圖靈提出了“模仿游戲”來測試數字計算機的人類相似度(4)參見Turing, A. “As we may think”. In P. A. Mayer(Ed.), Compute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edition 1950,Chap.1,pp.23-36。,得出智力和情感是可存在于神經系統和計算機中的信息。香農(Claude Shannon)認為,信息能夠被分離出其存在基礎,移動到另一種介質上并維持原狀。用維納(Noebert Wiener)的話說:“信息是信息,而不是物質或能量。”[11]庫茲韋爾(Ray Kurzweil)和莫拉維克(Hans Moravec)進一步提出將大腦中的信息下載或者掃描到計算機中來搭建全新的智能體。(5)參見Kurzweil, R. The age of Spiritual Machines: When Computers Exceeded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Penguin,1999.和Moravec, H. Mind children: The future of robot and human intellig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海爾斯也指出,人類的本質存在可以作為可傳輸的信息被載入計算機中。[12]這些理論表明,智能體能通過信息中介吸收人類機能,甚至還有可能以技術力量將機能超能化。實際上,創作了《我知我新》的小冰已經展現了其未來成為更高階智能體的潛能。以歌詞編寫為例,小冰將人類用語習慣整合為有一定規則的數據串,當“知乎青年”的字形浮現,便在“智腦”處理器中開啟轉換、編碼、解碼三步驟。準確獲取對應信息,即字形的意義之后,以其自身解釋數據的模式,在短時間內連接語義相似的基塊,以漫射形式構成同義網絡,做出豐富的音樂聯想,寫出“我在我主場/世界就任我去狂想/我知我新/未知的世界那么驚艷”這樣兩句個性鮮明、令人驚艷的青年口號,并為其譜上朝氣蓬勃的動感旋律。可見小冰融合了人類的高級情智機能,并且在它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到超能層次。微軟小冰首席架構師周力等人曾提出了一個原則:“人工智能創造的主體(如小冰),須是兼具IQ與EQ的綜合體。”[13]與小冰保持合作的獨立音樂人陳鴻宇設想:“將來的某一天,小冰能以其本身的模式去分析一首給定的歌曲擁有怎樣的含義。”[14]如果有比小冰更高階的AI出現,真正突破情和智這種人類機能的束縛,未來的藝術形式都將會有更巨大的變化。
最后,AI藝術創作的前期設計、中期的形式和內容以及后期傳播都有可能跨越人類所處的感官世界,呈現難以估量的、有待探索的生長態勢。從純技術的角度來看,如牛津大學信息哲學與信息倫理學的教授盧西亞諾(Luciano Floridi)所述,現代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第二級技術社會。技術與技術聯通連鎖,人類則對技術進行發明和干預,于是構成一個人類—技術—技術的相互制約且相互強化的循環。未來,人類被排除在第三級技術,即技術—技術—技術的閉路循環之外,僅作為技術的享受者和消費者。(圖2)[15]這表明,AI革命將不是一些未知新技術的縱向發展,而是把所有事物都聯系起來的橫向發展。

圖2 第三級技術(third-order technology)
所以未來的藝術創作空間很可能是一個完全自動集成的信息域,AI會提升到超越人類感官和人類特性的另一個層面,很難預測其藝術創作的內容、主題、風格、語言等。曼諾維奇(Lev Manovich)指出:“只有在AGI取得足夠進展之后,創造出在人類及宏大世界的美學上令人滿意和語義明確的媒介藝術品才會成為可能。”[16]唯有AGI即強人工智能實現之際,AI藝術的全貌才能從模糊轉為清晰。在那種最理想狀態下,人類才能切實地感受到AI藝術所具有的驚人創造力,并獲得難以想象的全新審美體驗
從現階段看,AI藝術仍然受限于弱人工智能(ANI),AI提供了“與人藝術”的可能,即作為一種工具協助人類、由人類參與的藝術創作。至于上文所述的強人工智能(AGI)階段,AI有可能具有了類似于人的意識和情感,在很大程度可以進行“類人藝術”的創作。而到了超人工智能(ASI)階段,AI或許可以完全突破人的感官、情感和意識,其“超人藝術”完全凌駕于人的創作之上。或許在未來,這些不同類型和階段的AI可能會出現重合或共存的情況,若想真正去理解和闡釋,歸根到底是需要運用媒介論來進行統合的。關鍵就在于,“按照媒介論,人工智能體既非一般性工具(機器),亦非主體,而是處于工具(機器)和主體之間動態發展的‘智媒介’”[17]。
四、結語
必須正視的情況是,在人文主義的審美標準下,即使AI可以生成巴赫、莫扎特等大師之作的完美摹仿品,許多人仍然會持排斥的態度,認為它們不過是被切碎的音樂片段的重新排列。就小冰的《我知我新》而言,即使它表達的思想內容符合知乎青年的理想志向,人類中心主義者仍然批評這首歌曲缺乏人文精神,因為AI藝術對人類藝術的實質性僭越已經威脅到人類藝術的權威。[17]但事實上AI藝術和人類藝術不應存在這樣的糾葛,人類不應對AI創作抱有如此大的偏見和憂慮。“人工智能給我們藝術創造帶來的可能不僅僅是目前表現出來的對人的能力的‘攻城掠地’,相反,它很可能以另外一種方式提醒我們,人的創造更可能往哪個方向行進。”[18]真正值得探索的應是人類如何與智能體結合,如何通過發展AI藝術,甚至后人類藝術來打破現有藝術和人類自身的邊界,并在這種探索中保持對世界的寬容和對自我的確信。由數據之美和算法可能性驅動的小冰為代表的AI創作,昭示出智能體正在創造一種新的藝術形態,同時也正在改變人類的存在狀態。人類可能開始認識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和角色已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開始理解自己在媒介維度上的信息屬性,“一種超人文主義、超人類主義的價值觀可能得以建構”[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