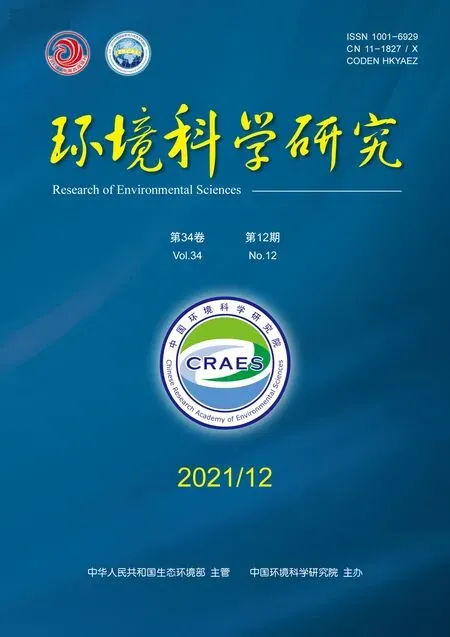中蒙毗鄰草原區荒漠化時空動態研究
王 旭, 刁兆巖, 鄭志榮, 靳三玲, 馬 普, 呂世海*
1.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生態研究所, 北京 100012 2.蘭州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甘肅 蘭州 730000 3.北京林業大學草業與草原學院, 北京 100083
荒漠化是最具威脅的區域性環境問題之一,有“地球癌癥”之稱,主要發生在干旱半干旱和半濕潤地區,常伴隨著生產力下降、土地資源喪失、地表呈現類似沙質荒漠化景觀等生態環境退化問題[1-4],其成因與氣候變化、人類過度干擾活動等直接相關[5]. 目前,全球有2.5億人受到荒漠化的直接影響,約有10億人處于荒漠化風險之中,荒漠化每年導致的經濟損失達4.2×1010美元[6]. 中國是受荒漠化危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7],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政府和地方相繼啟動實施了一系列荒漠化綜合防治工程,如京津風沙源治理、退牧還草、退耕還林還草、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等,對改善區域植被覆蓋成效顯著,但土地沙化和草原荒漠化問題依然十分嚴峻. 全國第五次荒漠化與沙化土地監測結果顯示,截至2014年,我國荒漠化土地總面積約2.71×106km2,占荒漠化監測區面積的78%,占國土面積的27%. 其中,內蒙古草原荒漠化面積60.92×104km2,占全國土地荒漠化總面積的22.5%,占內蒙古自治區土地總面積的51.50%.
沙塵暴是土地荒漠化引起的最直接的環境災害,因其具有傳輸距離遠、涉及范圍廣、危害程度大等特點,多年來倍受沙塵源地及下游區民眾的廣泛關注[8]. 沙塵暴會影響大氣溫度、太陽輻射、大氣組分和地球生物化學循環過程[9-10],增大區域環境健康風險,危害人體健康[11-12]. 中蒙毗鄰草原區地處蒙古高原腹地,受強烈蒙古氣旋及其后部冷空氣影響,地勢較高、地表干燥、荒漠化嚴重、地表裸露度較大,已成為東北亞沙塵暴發生的主要源頭區[13-15]. 其中,蒙古蘇赫巴托爾省、東戈壁省以西荒漠化嚴重草原區為東亞沙塵暴的主要源地,中國內蒙古錫林郭勒盟中西部典型草原、陰山北麓荒漠草原及科爾沁沙地、渾善達克沙地、庫布齊沙地、毛烏素沙地為東北亞沙塵暴加強區[16-19]. 每年由此而引發的災害性特大沙塵天氣過程,不僅嚴重制約著當地工農牧業生產和民眾日常生活,而且對下游區大氣環境質量和民眾健康構成了嚴重威脅. 但是,由于中蒙毗鄰草原區屬中國和蒙古毗鄰交界區域,受多種因素影響,諸如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許多基礎性研究相對缺乏,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對礦產礦藏開采[20]、草原生產力時空變化[21-22]、草原放牧利用與管理[23]等具體問題的探討,將中蒙毗鄰草原區作為一個整體,開展區域荒漠化時空動態比較的研究相對較少. 鑒于此,該研究以2001年、2010年和2020年影像數據解譯為基礎,結合地面調查數據,重點分析區域荒漠化時空動態變化特征,以期為進一步推進區域荒漠化聯防聯治和沙塵源地植被恢復提供科學依據.
1 數據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域為中蒙毗鄰草原區(41°11′27.86″N~49°24′08.83″N、107°59′02.20″E~116°32′54.39″E),包括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蘇尼特左旗、二連浩特市、阿巴嘎旗,以及蒙古蘇赫巴托爾省、東戈壁省. 研究區總面積約3×105km2(見圖1),屬北溫帶干旱草原植被. 全年平均氣溫0~6 ℃,降水量150~250 mm,土壤以栗鈣土、棕鈣土為主,土層較薄、沙質含量大. 近20年來,年均特大沙塵暴發生頻次15~20次;植被分布特征,中東部以針茅(Stipacapillataspp.)、羊草(Leymuschinensis)草原為主,旱生化現象顯著,中部及南部以小葉錦雞兒(Caraganamicrophylla)荒漠草原為主(見表1).
依據植被類型、覆蓋度、人口數量、行政區劃等指標,將研究區分為3個區(見圖1),各區域概況見表1.

表1 研究區概況描述
1.2 數據來源
1.2.1遙感影像
以Modis NDVI、Modis Albedo、Landsat TM和Landsat OLI數據為基礎,分別選擇2001年、2010年和2020年每年8月的遙感影像數據,結合地面調查對研究區荒漠化程度進行評估. 其中,Modis數據為8月下旬MOD09A1 16天合成數據、MCD43A3逐日數據,行列號為h25v04和h26v04;Landsat數據為2001年和2010年Landsat TM5 16天合成數據,2020年Landsat 8 OLI 16天合成數據;對同期云量不達標(高于5%)數據,選取臨近達標數據填補;Modis數據獲取自NASA數據網站(https://ladsweb.modaps.eosdis.nasa.gov),Landsat數據獲取自美國地質勘探局(https://earthexplorer.usgs.gov).

注: C區表示中國內蒙古中西部荒漠草原區,D區表示蒙古東戈壁省荒漠草原區,S區表示蒙古蘇赫巴托爾省典型草原區. 底圖下載于自 然資源部地圖技術審查中心標準地圖服務平臺(http://bzdt.ch.mnr.gov.cn/browse.html?picId=%274o28b0625501ad13015501ad2bfc0045%27) 的《中國地圖1∶4 800萬64開 分省設色 有鄰國 線劃二》. 下載日期: 2021年06月26日. 審圖號:國審字(2021)第5979號. 下同.圖1 研究區區位及取樣點分布Fig.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urvey spots
1.2.2地面跟蹤監測
于2020年8月下旬的植物生長季,在3個區域進行調查取樣. 荒漠化分級和監測方法執行GB/T 20483—2006《土地荒漠化監測方法》標準. 由于研究區生境類型均一,且交通不便,3個區域共選取典型監測樣地43個,其中C區29個、D區4個S區 10個(見圖1).
1.2.3統計數據及氣象數據
統計數據分別來源于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統計局(http://tj.nmg.gov.cn)、蒙古國家統計局(https://www.1212.mn),氣象數據來源于中國氣象數據網(http://data.cma.cn)和歐洲中期氣象數據中心(https://cds.climate.copernicus.eu).
1.3 研究方法
1.3.1數據處理
利用ENVI 5.3和ArcGIS 10.5軟件,對Landsat數據進行輻射定標、大氣校正、鑲嵌拼接、裁剪等處理,并結合eCognition 9.0軟件對研究區水體、農田、建筑物進行提取和剔除;利用MRT(Modis reprojection tool)對NDVI和Albedo數據進行拼接和重投影處理;利用Origin 2018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和圖表制作.
1.3.2Albedo-NDVI特征空間及荒漠化監測差值指數
參照已有文獻[25-27],選取Albedo-NDVI特征空間及荒漠化監測差值指數(DDI)對研究區荒漠化現狀進行研究. 其中,NDVI表征地表植被蓋度,Albedo表征地表粗糙程度. 利用研究區特征空間中的“干邊散點”(各NDVI值所對應的Albedo最大值點)進行線性回歸擬合,得到Albedo-NDVI特征方程及DDI計算公式.
Albedo=k1×NDVI+c
(1)
DDI=k2×NDVI-Albedo
(2)
k1×k2=-1
(3)
式中,Albedo為地表反照率,NDVI為歸一化植被指數,k1為Albedo與NDVI擬合特征方程的斜率,c為擬合產生的常數.
2 結果與分析
2.1 荒漠化監測差值指數
荒漠化監測差值指數(DDI)是由Albedo-NDVI特征方程衍生出的監測荒漠化狀況的指數,主要用于荒漠化程度分級[25]. 利用ArcGIS 10.5生成1 500個點,分別提取2001年、2010年、2020年研究區對應點的NDVI及Albedo值,進行歸一化處理、最大值提取、線性擬合等,生成不同時段Albedo-NDVI特征方程,結果如圖2所示. 研究區不同時段NDVI與Albedo呈明顯負相關,且各特征方程的R2均大于0.8,Albedo-NDVI特征方程表現出較好的擬合性.

圖2 Albedo-NDVI特征方程Fig.2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of Albedo-NDVI
依據式(1)(2),對不同時期DDI值進行計算和歸一化處理,按照自然斷裂法將DDI值劃分為5個等級,并使各類別內方差最小,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DDI值及荒漠化程度劃分
隨機選取若干點,對各時段Landsat影像進行目視解譯,結合實地典型樣地監測結果,共建立300個精度驗證點. 驗證結果表明,該分類方法的總體精度達0.89,Kappa系數達0.89. 其中,對ESD和SD的識別精度在0.90以上,對MD和ND的識別精度在0.85以上,對LD的識別精度達0.81.

圖4 研究區各分區不同時期荒漠化程度組成Fig.4 The composition of desertification degree of different regions at the different times
2.2 荒漠化時空分布格局
由圖3、4可見,研究區荒漠化程度總體呈現“西高東低、南高北低”的空間特征,以2020年為例:① ESD、SD面積約占研究區總面積的37.2%,主要分布在C區和D區. 其中,中國境內ESD、SD面積為39 710 km2,占研究區總面積的13.24%,主要位于二連浩特市、四子王旗和蘇尼特右旗的中部和北部、蘇尼特左旗大部等荒漠草原區;蒙古境內ESD、SD面積為71 830 km2,占研究區總面積的23.94%,主要分布于東戈壁省的中部和南部荒漠草原區. ② ND主要集中在C區北部和S區大部,占研究區總面積的18.3%. ③荒漠化分區特征明顯,C區以MD和SD為主(分別占C區總面積的36.1%和28.6%),D區以ESD和SD為主(占D區總面積的65.5%),S區以ND、LD為主(分別占S區總面積的67.2%、26.2%).

圖3 不同時期荒漠化空間分布格局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esertification degree at the different times
不同時期研究區荒漠化格局存在明顯差異. 其中,2001年以ESD、SD、MD為主,三者面積分別占研究區總面積的24.60%、29.27%和21.49%;2010年,ESD面積有所減少,較2001年減少了33.78%,而SD、MD、LD面積略有增加,分別較2001年增加了4.17%、4.37%和16.37%;2020年,ESD、SD、MD面積縮減,分別占研究區的13.53%、23.81%和22.82%,LD和ND面積增加,分別占研究區的18.70%和21.14%.
2.3 荒漠化演變趨勢
如圖5所示,2001—2010年,研究區荒漠化程度加劇區域主要分布在D區北部和S區的東西兩翼地區,面積為 21 300 km2,占研究區總面積的7.1%;荒漠化逆轉區域主要分布在C區大部和S區北部,荒漠化逆轉面積為 74 100 km2,占研究區總面積的24.7%.

圖5 研究區不同時段荒漠化演化程度的空間分布Fig.5 The distribution of desertification changes in different period
各分區荒漠化演變趨勢見圖6,結果顯示:2010—2020年,研究區荒漠化逆轉面積較大,逆轉比例約占研究區總面積的40.3%,較2001—2010年增加了63.18%;但D區西部、C區四子王旗、蘇尼特右旗、蘇尼特左旗、阿巴嘎旗的南部地區,草原荒漠化加劇趨勢顯著,荒漠化加劇面積占研究區總面積的8.7%.
由表3可見,2001—2020年,C區ESD、SD面積呈持續縮減態勢,凈減少面積分別為 30 360、10 350 km2,MD、LD、ND面積呈不斷增加趨勢,面積分別凈增 19 200、16 700 和 5 060 km2;D區ESD、SD、MD面積分別縮減 2 890、3 360、360 km2,LD面積增加 6 300 km2,ND面積基本未變;S區由于自然條件相對較好,且人口較少,利用程度較輕,ESD面積變化量相對較小,而SD、MD、LD面積分別減少 2 640、14 830、11 310 km2,ND土地增加 28 820 km2,呈逐年好轉趨勢.

表3 研究區各分區荒漠化程度轉移矩陣
綜上,與2001年相比,2020年研究區荒漠化程度整體上有所好轉,其中,ND面積增加了近1倍,ESD面積減少了約90%,荒漠化凈逆轉面積(荒漠化逆轉面積與擴展面積之差)約 147 220 km2. 研究區各分區荒漠化逆轉情況存在明顯差異,其中,C區荒漠化凈逆轉面積占研究區荒漠化凈逆轉總面積的58.84%,S區占31.30%,D區僅占14.52%;C區ESD面積縮減超過75%;S區ND面積增加了1倍;D區LD面積略有增加,其余荒漠化程度面積變化不大.
2.4 荒漠化驅動因素分析
氣候變化和自然變率及人類活動對荒漠化的影響存在時空差異[28],因此分別計算研究區各分區DDI與氣象因素的相關性. 結果(見表4)顯示,C區PRE(降水量,precipitation)、RH(相對濕度,relative humidity)與DDI均呈極顯著正相關(P<0.01);D區DDI與PRE、RH均呈顯著正相關(P<0.01),與TEM(年均溫度,temperature)呈極顯著負相關(P<0.01);S區PRE、RH、TEM、WS(年均風速,wind speed)均與DDI呈極顯著正相關(P<0.01). 3個分區內PRE與RH均呈極顯著正相關(P<0.01);其余氣象因子間的相關性存在空間差異.

表4 研究區DDI與氣象因素相關系數矩陣
2000—2020年《中國內蒙古統計年鑒》和《蒙古統計年鑒》(Mongolia Statistical Yearbook)數據顯示: ①近20年來,研究區各分區人口密度變化不大,人口增長緩慢,C區人口密度遠高于D區和S區. ②放牧強度方面,一直呈現S區>D區>C區的規律;C區放牧強度變化不大,總載畜量一直維持在4×106~5×106羊單位的較低水平;D區與S區分別以2008年和2006年為節點,先呈現較大幅度的波動,后持續增長;2019年,D區和S區總載畜量分別突破了6×107和3×107羊單位(見圖7). 顯然,研究區各分區總載畜量變化趨勢與人口變化趨勢并不相符,可能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 首先,受游牧文化影響,D區和S區居民對肉食的需求量大,而C區居民可以在腹地獲取蔬菜供給,對肉食的需求相對較低. 其次,年鑒顯示,蒙古總人口數量一直呈大幅增長趨勢,盡管D區和S區人口數量變化不大,但周圍區域人口的增加,導致對肉奶等的市場需求增加,間接增大了該區域的放牧強度.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在C區實施的草原生態補助獎勵政策,使牧民通過合理放牧,把草原保護好,不必追逐高放牧強度,就可以增加收入.

圖7 近20年各分區人口密度及放牧強度的變化趨勢Fig.7 The trends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grazing intensity over the past 20 years
3 討論
利用Albedo-NDVI特征空間,對中蒙毗鄰草原區2001年、2010年、2020年的遙感影像進行擬合分析,生成3期DDI指數,并利用自然斷裂法對其進行等級劃分以實現荒漠化監測分級,監測精度達0.89. 由于荒漠化常伴隨著地表理化性質的改變,因此用于荒漠化監測的指標有很多. 劉愛霞等[29]將植被覆蓋度(FVC)、改進型土壤調整植被指數(MSAVI)、反照率(Albedo)、陸地表面溫度(LST)和土壤濕度(TVDI)5個指標隨機組合進行荒漠化監測,發現監測精度會隨指標數量的增加而提高;只有2個指標參與監測時,精度范圍為0.77~0.87;指標增至5個時,監測精度達0.95. 利用Albedo-NDVI特征空間及DDI荒漠化監測差值指數進行荒漠化監測分級,可在使用較少指標的情況下,獲得較高監測精度,且精度大多在0.85以上[26-27,30-34]. 目前,關于Albedo-NDVI特征空間的構建和使用存在差異. 任艷群等[35]利用該方法對準格爾盆地進行了土地荒漠化監測,用一個模型進行多期荒漠化監測,精度為0.87;鄒明亮等[27]采用4個模型監測了瑪曲縣2001—2015年的荒漠化時空動態變化,監測精度高達0.96. 后者監測精度的提升可能與Albedo、NDVI的時間差異性有關,不同時期Albedo與NDVI存在不同的線性關系,多時期共用同一DDI模型可能會降低模型的監測精度. 在擬合Albedo-NDVI 特征方程時,部分研究提取Albedo和NDVI值后,未對各NDVI值所對應的Albedo做提取最大值處理,即在Albedo-NDVI特征空間內隨機提取數值點進行擬合,但曾永年等[25]對Albedo-NDVI特征空間和DDI的闡述表明,特征空間的干邊散點更能反映土地荒漠化情況,依據干邊散點得出的DDI指數的監測精度更高. 筆者利用干邊散點擬合了3期DDI指數,時間間隔為10年,總體監測精度為0.89,Kappa系數為0.89,精度高于大多數隨機采點的方法.
荒漠化是蒙古高原干旱半干旱地區最嚴重的生態問題之一,氣象因素和人類活動是影響荒漠化地域性和差異性的關鍵因素[36-38]. 塔米日[24]對蒙古高原東部氣象因素動態變化的研究表明,中蒙毗鄰草原區年降水量呈“東北多、西南少”的空間分布特征;Shi等[39]等發現,近60年來,中蒙毗鄰草原區所屬區域的年降水量呈增加趨勢;Su等[40]研究表明,內蒙古高原降水量的增加會促進其地表植被的生長恢復. 筆者發現,中蒙毗鄰草原區荒漠化程度與年降水量、相對濕度均呈極顯著負相關(P<0.01);近20年來降水量波動增加,促進地表植被的生長恢復,決定了區域荒漠化整體呈逆轉趨勢. 不同區域的風速、年均溫與荒漠化程度的相關性存在差異,可能與氣象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及下墊面的空間差異性有關,仍待進一步研究.
此外,研究區地廣人稀,人口主要集中在城鎮及其周邊,對草原造成破壞的人類活動主要是過度放牧和礦產資源開采. 資料分析發現,近20年來,研究區中國境內的放牧強度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而蒙古一側放牧強度一直持續增加,且近10年來增速明顯;同時,考慮到蒙古境內數量龐大的黃羊、野驢等野生動物未被納入統計,蒙古一側放牧強度可能高于目前的統計數據. 另外,蒙古采礦業極其發達,2019年礦業產值占蒙古工業總產值的57%,其中,東戈壁省北部、中部和南部的3條大型成礦帶是重要作業區[41],對草原造成較大破壞,且因地方較注重追求經濟利益,忽視了開礦區草原的保護與恢復,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人為活動造成的荒漠化. 近年來,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草原的國家生態安全戰略定位,先后在內蒙古草原實施了退牧還草、退耕還草、京津風沙源治理、草原生態保護補助和獎勵政策等多項重大工程和措施,草原植被不斷恢復,土地荒漠化得到有效控制,突出表現為在自然本底和土地荒漠化程度相近的情況下,近20年來中蒙毗鄰草原區中國境內的土地荒漠化逆轉程度和速率均顯著高于蒙古東戈壁省.
4 結論
a) 中蒙毗鄰草原區荒漠化程度呈“西高東低、南高北低”的特征. 其中,蒙古東戈壁省以ESD(極重度荒漠化)和SD(重度荒漠化)為主,占研究區總面積的65%以上;中國內蒙古荒漠草原區以SD和MD(中度荒漠化)為主,分別占28.5%和36.1%;蒙古蘇赫巴托爾省93%的土地為LD(輕度荒漠化)和ND(未荒漠化),其中ND面積占比為67%.
b) 近20年來,中蒙毗鄰草原區荒漠化程度呈逐步逆轉態勢,且后10年逆轉程度高于前10年. 與2001年相比,2020年ND面積增加了1倍,ESD面積減少了90%;2001—2010年29.97%的荒漠化土地出現不同程度逆轉,凈逆轉面積約 51 360 km2,2010—2020年荒漠化逆轉比例為40.26%,凈逆轉面積約 95 860 km2.
c) 2001—2020年,中蒙毗鄰草原區荒漠化逆轉程度呈“東高西低”的空間特征. 在分區上,C區的荒漠化凈逆轉面積占荒漠化凈逆轉總面積的58.84%,S區占31.30%,D區僅占14.52%;在地理單元上,蒙古蘇赫巴托爾省草甸草原和中國內蒙古荒漠草原的土地荒漠化程度出現大幅好轉,位于中國境內的極重度荒漠化面積減少了75%以上,但蒙古東戈壁省,除LD面積略有增加外,其他荒漠化類型面積變化不大,其境內的極重度荒漠化面積基本未變.
d) 研究區荒漠化時空分布格局及逆轉特征主要受降水以及放牧、礦產開采等人類活動的影響,年降水量決定了荒漠化的演變趨勢和基本分布格局,放牧和礦產開采進一步加重了區域荒漠化程度,而生態保護與修復工程推進了荒漠化逆轉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