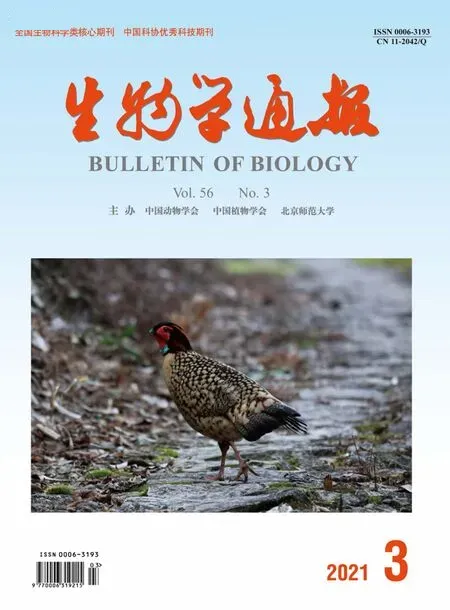傳統Cronquist系統的澤瀉亞綱在APGⅣ系統中的地位*
王庚申 劉忠成2, 王 蕾 廖文波,3
(1 有害生物控制與資源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廣東省熱帶亞熱帶植物資源重點實驗室,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廣東廣州 510275 2 首都師范大學資源環境與旅游學院 北京 100048 3 中山大學生態學院 廣東廣州 510275)
澤瀉類(Alimatids)是單子葉植物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類群,在形態上經歷了廣泛的多樣化過程,主要習性以淡水濕地為主,包括沉水、浮水、挺水或水澤地,還有部分生于海岸灘地呈海草(seagrasses)狀,并出現一些高度退化的花結構、水媒傳粉或形成特化的花粉粒等。更奇特的是,那些海洋支系的形成據認為是陸地植物至少經過4~5 次[1]反復進化的結果。另一方面,傳統澤瀉目(Alimatales)具有特殊的水媒傳粉,而這僅在雙子葉植物的金魚藻科(Ceratophyllaceae)和水馬齒科(Callitrichaceae)發現[2]。無疑,澤瀉目的傳粉從風媒、蟲媒到水媒,進而進入海洋環境是有花植物進化的一個很特殊的過程。
總體而言,從集“形態學、胚胎學、孢粉學、細胞學”大成的Cronquist(1981)[3]系統到以“分子數據(結合胚胎、生理生化特征等)”為依據的、歷經4 版、綜合許多分支分析形成的APGⅣ(2016)[4],其間經歷了“形態→系統,個別→歸納”的過程,而今天的APGⅣ系統給人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在目前分子系統學背景下,如何反其道而之,體現“系統→形態”“歸納→個別”這一過程? 特別是,分子系統形成的集合,很可能在極大程度上通過“分子序列→體現生理功能、生態適應性”。本文試圖從教學的角度,以傳統Cronquist系統的澤瀉亞綱(Alimatidae)為代表,討論其在新的分子系統APGⅣ中的地位和吻合情況,從而為理解澤瀉類甚至整體單子葉植物的系統變化提供幫助。
1 克朗奎斯特系統的澤瀉亞綱與APGⅣ系統的澤瀉類
1.1 克朗奎斯特系統的澤瀉亞綱 克朗奎斯特系統是美國學者Arthur Cronquist 于1981年發表的,包括64 目383 科[3],該系統主要以形態學、解剖學、胚胎學、孢粉學、細胞學特征等為主要分類依據,也是過去10~30年前廣泛認可的流行系統。
Cronquist(1981)[3]贊同真花學說及被子植物單元起源的觀點,認為被子植物起源于一類已滅絕的前被子植物,現存被子植物各亞綱都不可能來源于其他亞綱,而是來源于前被子植物,木蘭目是被子植物的原始類型,柔荑花序類各自起源于金縷梅目,單子葉植物來源于類似現代睡蓮目的祖先,并認為澤瀉亞綱是百合亞綱進化線上最近基部的一個側枝(圖1)。針對單子葉植物,APGⅣ系統認為菖蒲目是最基部的分支,澤瀉目則是第2 分支。而在Cronquist 系統中,并沒有菖蒲目,它屬于棕櫚亞綱天南星目天南星科的一個屬,即菖蒲屬,它在APGⅣ系統中是被調整并升級為目[3-4]。

圖1 克朗奎斯特單子葉植物綱系統圖[3]
在Cronquist 系統中,澤瀉亞綱有4 個目,即澤瀉目(Alismateles)、水鱉目(Hydrocharitales)、茨藻目(Najadales)和霉草目(Triuredales)。澤瀉目含3 個科:沼草科(Limnocharitaceae)、花藺科(Butomaceae)、澤瀉科(Alismataceae);水鱉目含1 個科,即水鱉科(Hydrocharitaceae);茨藻目含9 個科:麗麗草科(Lilaeaceae)、角果藻科(Zannichelliaceae)、水麥冬科(Juncaginaceae)、芝菜科(Scheuchzeriaceae)、海神草科(Posidoniaceae)、水蕹科(Aponogetonaceae)、大葉藻科(Zosteraceae)、眼子菜科(Potamogetonaceae)、川蔓藻科(Ruppiaceae);霉草目含1 個科,即霉草科(Triuridaceae)。
1.2 APG Ⅳ系統的澤瀉類 APG(Angiosperm Phylogeny Group)系統發表于1998年[5],之后又陸續推出3 個版本[4,6-7]。2016年的第4 版發表在《林奈植物學報》(Botan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上,共64 目416 科。APG 系統是一個以分子序列為優先依據而建立的被子植物分類系統,也是一個無等級的演化支,可與植物界各高等植物類群相連接[8-9](圖2)。

圖2 APGⅣ系統單子葉植物部分[4]
在APGⅣ系統中,單子葉植物的澤瀉目是一個重要的原始類群,包括14 科166 屬約4 500 種。澤瀉目通常被分為3 個分支或類群,即天南星科(Araceae)、巖菖蒲科(Tofieldiaceae)和核心澤瀉類(core alismatids)。核心澤瀉類又可進一步分為2 個類群,即瓣花類(Petaloid)和萼花類(Tepaloid)。瓣花類有3 個科,即澤瀉科(Alimat-aceae)[合并了沼草科(Limnocharitaceae)]、花藺科(Butomaceae)、水鱉科(Hydrocharitaceae);萼花類包括其他9 科,即冰沼草科(Scheuchzeriaceae)、水蕹科(Aponogetonaceae)、水麥冬科(Juncaginaceae)、花香蒲科(Maundiaceae)、大葉藻科(Zosteraceae)、眼子菜科(Potamogetonaceae)、海神草科(Posidoniaceae)、川蔓藻科(Ruppiaceae)、絲粉藻科(Cymodoceaceae)[10]。
2 APGⅣ系統的單子葉植物基部群
澤瀉類(目)無論在克朗奎斯特系統(1981)[3],還是APGⅣ系統(2016)[4],二者都是被看作是單子葉植物的原始類群(圖3)。這也是大多數植物學者所廣泛認同的。但天南星科、菖蒲科如何成為基部群是令人意外的。

圖3 克朗奎斯特系統的澤瀉亞綱與APGIV 系統的澤瀉類
在形態學特征上,澤瀉亞綱的各屬均不具肉穗狀花序,不具佛焰苞,且為離生心皮;天南星科和菖蒲屬,具肉穗花序,雌蕊群心皮合生成筒狀。因此,最傳統的觀點例如Engler(1920)[11]、Hutchinson(1973)[12]、Cronquist(1981)[3]大多認為廣義的天南星科屬于棕櫚亞綱(類)或百合亞綱(類)。
2.1 天南星目被證實宜并入澤瀉目 克朗奎斯特系統(1981)[3]的天南星目Arales,含2 個科,即天南星科(Araceae)、浮萍科(Lemnaceae),隸屬于棕櫚亞綱(Arecidae,棕櫚類)。2000年,Stevenson[13]從分子序列角度證明天南星科和澤瀉類聚在一個支上,但顯然形態數據與分子序列存在明顯沖突。Dahlgren等(2012)[14]也贊同與澤瀉類有明顯的親緣關系。
2001年,Buzgo[15]研究了天南星科和澤瀉科的屬、菖蒲屬的胚胎學特征,認為它們是相似的,贊同均作為單子植物的基部群,最終得到了分子序列數據[16]的支持。Buzgo(2001)[15]也研究了線粒體、質體和核DNA 的相對比例,他認為不同數據集應用會引起爭議,菖蒲屬只是作為姊妹群嵌套到澤瀉類。在APGⅣ系統中,浮萍科已并入天南星科。
2.2 菖蒲目Acorales——APG Ⅳ系統所有單子葉植物的基部群 2016年,APGⅣ進一步證實天南星科的菖蒲屬,不同于其他屬。因而將其獨立為科Acoraceae,并提升為目,作為所有單子葉植物的基部姐妹群,含1 屬,即菖蒲屬Acorus,共2種。為多年生常綠草本;根莖匍匐,肉質,葉二列,無柄,扁箭形;肉穗花序指狀圓錐形或鼠尾狀,佛焰苞長,葉狀,生于當年生葉腋,柄長,全部貼生于佛焰苞鞘上;花兩性,密集,花被片6;雄蕊6,心皮合生;漿果,熟時紅色;種子有胚乳,肉質。廣布亞洲和北美溫帶、亞熱帶、熱帶亞洲;中國黃河以南廣布。
菖蒲科盡管具肉穗花序,佛焰苞,合生心皮,但在胚胎發育、花器官發生上與天南星科有差異,例如,天南星科(例如,Orontium屬)花通過內輪花被片退化,其三基數發育為二基數;而菖蒲屬的花被片減少的模式、雌蕊群發育方式與之不同[17]。
2.3 APGⅣ澤瀉目增加了巖菖蒲科、花香蒲科、絲粉藻科
1)巖菖蒲科(Tofieldiaceae)。為多年生草本,根狀莖匍匐;葉基生,線形,螺旋狀排列,基部互相套疊,兩側壓扁。總狀花序,頂生;花小,兩性,具花梗或無,基部具1 枚小苞片;花被片6,2 輪,離生;雄蕊6;心皮3,花柱離生或合生;蒴果蓇葖果狀。5 屬31 種,廣布北溫帶,少數見南美洲;中國1 屬3 種,產于東北、華東、西南。
在Cronquist 系統中,百合亞綱的百合目、百合科,有一個小屬,稱為巖菖蒲屬(Tofieldia),APGⅣ(2016)依據分子序列將其并入澤瀉目,并提升為巖菖蒲科(Tofieldiaceae)。從形態學特征看,巖菖蒲科的花粉粒具有雙萌發孔,而核心澤瀉類的花粉粒不具有萌發孔,這一特征可將巖菖蒲科和澤瀉科進行區分[10]。此外,Delpino(1903)[18]沒有將巖菖蒲屬并入菖蒲科,盡管二者都具有單一的等面葉,以及分泌絨氈層(secretory tapetum),但與澤瀉目其他種都是具有蛻膜(plasmodial)不同,而這2 個特征被看作可能是單子葉植物早期分化的共同祖征。甚至Remizowa(2010)[19]認為,分泌絨氈層在巖菖蒲科中存在,可能意味著澤瀉目的基部群分支應是巖菖蒲科而不是天南星科。
2)花香蒲科(Maundiaceae)。為多年生草本;根狀莖粗約5 mm;葉海綿狀,在交叉的位置腫脹或三角狀,長達80 cm 或更長,寬5~10 mm;穗狀花序具花葶,長10 cm,直徑約2.5 cm;心皮(3~)4室,6~8 mm 長,無柄;分果,果實長約1 cm,直徑約8 mm。僅1 種,花香蒲(Maundia triglochinoidesF.Muell.),產澳大利亞東部;中國不產。
花香蒲科為單型科,僅1 屬1 種,即花香蒲屬(Maundia),在Cronquist 系統中,屬于澤瀉類的水麥冬科(Juncaginaceae),在APGⅣ系統中被提升為科。另一個近緣科,Cronquist 系統的麗麗草科(Lilaeaceae),僅1 屬1 種,被并入APGⅣ系統的水麥冬科。
3)絲粉藻科(Cymodoceaceae)。為一年生沉水草本,生于淡水或海水;植株纖長,柔軟,二叉狀分枝或單軸分枝;下部匍匐或具根狀莖;葉線形,無柄,無氣孔器,具多種排列方式;葉脈1 或多條;葉基擴展成鞘或具鞘狀托葉;花單性,單生、簇生或為花序,腋生或頂生,雌雄同株或異株;雄花花被有或無,或具苞片;花絲細長或無,花藥1、2、4 室;雌花花被片無或具苞片,常具1、2、4 枚心皮,離生,柱頭2 裂或為斜盾形;瘦果。4 屬,16~20種,產全球熱帶和亞熱帶地區;中國3 屬4 種。
在Cronquist 系統中,絲粉藻屬亦屬于澤瀉類的角果藻科 (Zannichelliaceae),在APGⅣ系統中絲粉藻屬(Cymodocea)被獨立,并與二藥藻屬(Halodule)、針葉藻屬(Syringodium)等組成絲粉藻科。而角果藻科被取消,所含的角果藻屬被并入眼子菜科,亦屬澤瀉目。
2.4 水鱉科 在Cronquist 系統中,水鱉科亦屬澤瀉類,屬于水鱉目。在APGⅣ系統中,被合并在澤瀉目內。水鱉科、花藺科、澤瀉科共同組成瓣花澤瀉類(Petaloid Alismatids)。
在形態學特征上,水鱉科具胚珠多數,散布在子房壁內側,形成全面胎座(側膜胎座的一個典型類型),早期哈欽松(1934)[20]將其放在花藺科;1981年Cronquist(1981)[3]根據心皮合生、子房下位等進化特征將其單列為水鱉目。APGⅣ(2016)[4]將水鱉科并入澤瀉目,也考慮了形態學證據,即澤瀉科、花藺科、水鱉科其種子均不具胚乳,花粉粒具有厚的花粉壁、發達帶刺的頂蓋和欠發達的柱狀層,而且都具有平列型氣孔器。
離生心皮是被子植物的原始特征,澤瀉目中的離生心皮應為祖征,水鱉科的合生心皮起源于離生心皮;而花藺科具6 枚心皮且僅在基部合生,可能是演化過程的一個中間階段。由此,很顯然在瓣花澤瀉類分支中,3 個科的演化順序是澤瀉科、花藺科到水鱉科。
2.5 霉草目(Triuridales)的地位 在Cronquist 系統中,霉草目屬澤瀉類,僅含霉草科(Triuridaceae)。霉草科非常特殊,其為腐生草本,葉退化為鱗片狀,非綠色;花小,雌雄同株或異株,形成總狀近傘房花序,具明顯花被片,3~8(~10)片,1 輪,雄花雄蕊2~6,有退化雄蕊,心皮多數,但為離生,胚珠1 顆。中國1 屬5 種。
在APGⅣ系統中,霉草科并入露兜樹目,與舊系統相比相去甚遠,該目含4 科,特征截異,即翡若翠科(Velloziaceae)為旱生草本或灌木;百部科(Stemonaceae) 為多年生草本或灌木,常具肉質塊根;環花草科(Cyclanthaceae)陸生或附生草本,葉螺旋狀;露兜樹科(Pandanaceae)為喬、灌木,莖多呈假二叉狀分枝。
3 分子分類系統給人們的啟發
澤瀉類(Alismatids)常為水生植物,繁育系統幾乎包含了被子植物的各種傳粉類型[21],許多物種都可在水中完成部分甚至全部的生活周期,它們從陸生向水中的演化至少經歷過4~5 次獨立的分化過程。眾所周知,水生環境較穩定,理化性質大多比較相似,導致其生活方式比較接近,因而在形態演化上形成趨同現象,也引發了澤瀉類植物在形態分類學上的諸多難題[1]。從1998年APGⅠ系統發表,至2016年APGⅣ發表,前、后近20年,分子系統4次更新,每一次調整的幅度越來越小,意味著很多之前在形態學中爭議較多的目或科,在經過分子數據的多次核校后已逐漸穩定,并且也更加明確地揭示了分類群之間的演化關系。
澤瀉類各目、科在克朗奎斯特系統與APGⅣ系統之間的交叉關系,以及大致相似性,給人們一定的啟發。無疑,分子分類系統打亂了傳統的形態學分類系統,人們不習慣,甚至抵觸。但事實上分子數據分類的結果也可以有良好的形態學解釋。例如,澤瀉科、花藺科、水鱉科在APGⅣ系統中,能根據胎座類型和心皮合生程度作出進化上的解釋。當然,需要說明是,分子系統并非就是完全客觀正確的。分子系統樹的構建也會受到數據集性質的影響,基因序列的類型、數量,不同研究者的權重方式都會影響系統構樹。現在的問題是,人們不能依賴在實驗室內提取DNA 和通過PCR 認識野外形形色色的植物世界。因此,希望生物學家構建更加完善的系統進化樹,甚至采用全基因組測序,并且能揭示基因控制表型性狀和生態功能的方式,如此,分子系統的形態學解釋將不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