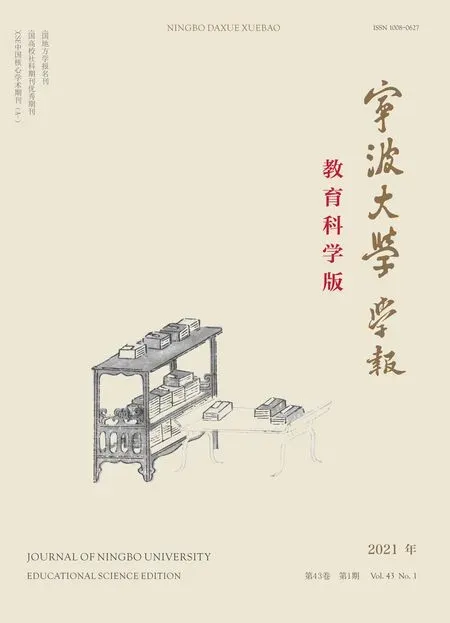城鄉教育一體化與鄉村文化傳承的悖論與化解
王 樂,馬小芳
城鄉教育一體化與鄉村文化傳承的悖論與化解
王 樂,馬小芳
(陜西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2)
城鄉教育一體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鄉村文化傳承是民族精神延續的原初根脈。鄉村文化的現實掙扎揭示出兩者之間的邏輯悖論,包括整體思維與一元思維的系統差異,開放性與保守性的特性殊途,文化改造與自然承續的方法分歧,以及制度建設與觀念建設的建設思路不同。因為矛盾始于整體性差異,所以只能采用教育現代化文化自覺的共生理念,擱置差異與沖突,引導兩者在不同的邏輯路向上尋求價值共識。共生策略是化解邏輯悖論的操作性設計,包括利用現代化的教育理念重塑鄉民的文化觀,構建城市教育與鄉村教育的“區隔—合作”機制,以及探索鄉村教育文化自覺階段化與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城鄉教育一體化;鄉村文化;教育現代化;文化自覺
城鄉一體化是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一項重大、深刻和必然的社會改革。其中,人口、技術、資本、資源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均依托于教育的支持。城鄉教育一體化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組成和核心動力。它是我國統籌城鄉教育改革、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等政策實施以來,中央為破解城鄉教育二元結構、推動城鄉教育公平與和諧發展而做出的新的戰略部署。[1]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動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2]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再次提出,要高度重視發展農村義務教育,推動建立以城帶鄉、整體推進、城鄉一體、均衡發展的義務教育發展機制。[3]
費孝通指出,“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4],鄉土根脈孕于文化。霍爾和尼茲(Hall & Neitz)認為,文化提供了塑造社會角色行動的價值與規范。[5]也就是說,鄉村文化形塑了鄉民人格,建立了鄉村秩序,培育了民族精神。所以,鄉村文化建設是鄉村發展的靈魂。《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也明確了“繁榮發展農村文化”[6]的戰略任務。在此背景下,城鄉教育一體化建設能否完成鄉村文化傳承的使命,兩者是否存在邏輯上的協同性,這應當成為鄉村教育振興的前提性問題。
一、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文化功能與鄉村文化傳承的教育責任
教育與文化是一種彼此敞開的關系,城鄉教育一體化與鄉村文化傳承的關系也是基于屬性與價值的相互支持,一者承擔文化功能,一者履行教育責任。
(一)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文化功能
2007年,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城鄉一體化”命題,次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對其進行了系統闡述。城鄉一體化是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促進城鄉資源及生產要素自由流動,使城鄉在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生態等領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過程。城鄉教育一體化是城鄉一體化的應有之義,它是在教育公平的核心價值取向下,打破城鄉二元僵局,建設城鄉教育共同體,在保持與發揮城鄉教育區域性特色與優勢的基礎上,促進城鄉互動聯結、相互幫扶、相互作用、消解差距,逐步實現城鄉教育公平、共生共榮、協調發展的動態過程。[7]
此外,“一體化”具有內在的文化關聯性。一方面,“一體化”是“屬文化的”。1988年,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命題,其中“一體化”既是一種文化視角,也是一種文化概念。另一方面,“一體化”又是“含文化的”。它是一種全納結構的發展動向,而文化必定是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按照這一邏輯,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關鍵在于文化建設,它也將成為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有學者提出,城鄉教育一體化是一種基于文化、通過文化、為了文化的教育體系。[8]由此可見,文化功能是城鄉教育一體化的內在價值演繹。它又可以從系統功能的角度分為系統外的“一體化文化功能”和系統內的“文化一體化功能”,前者是“城鄉一體化”范疇內教育系統與文化系統的一體化互構,后者則是“城鄉教育一體化”范疇內文化因素在教育系統內的一體化表征。
從外部的系統功能看,城鄉一體化中的教育與文化是兩種相互區隔且彼此支持的獨立系統,兩者與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系統共同構成城鄉發展的“一體”。城鄉一體化建設的實質是城鄉的統籌發展,教育與文化在整體性原則指導下,圍繞“城鄉共同體”的目標各司其職、兼收并蓄、協同發展。此外,由于屬性、特點、功能、表現形式等方面的差異,教育與文化又具有不同的系統結構和發展路向。從內部的系統功能看,教育系統中文化因素的“一體化”是城鄉教育一體化的重要組成,城鄉教育一體化要求其在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育內容、教育目標等方面符合“城鄉融合”的一體化標準。因為鄉村文化具有繼承性和保守性,所以城鄉教育一體化需要進行教育系統內的“文化改造”,使文化因素具有更強的“適應性”和“表達性”,能夠同時向農村和城市“開放”,建立城鄉統一協調發展的教育模式。
總而言之,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文化功能服務于城鄉統籌發展,宏觀上形塑城鄉一體化發展理念,微觀上培養城鄉間自由流動的“文化人”。
(二)鄉村文化傳承的教育責任
文化是一種體現于符號中的意義的歷史性傳承模式,是一種以符號形式表達的概念的傳承體系,能夠交流、保存和發展他們的生活知識與生活態度。[5]傳承性既定義了文化的內涵,也規約了文化的屬性。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自我傳承的需要厘定了延續文化薪火的必要條件——穩定性、保守性和一元性。文化是一種相對穩定的“意義之網”,意義由某一群落的公眾編織和所有。[9]文化一旦形成就會被文化自身及其承載的主體所承續并維持穩定,以文化的純粹性為矢夯實積極意義的保守狀態。所以,文化和教育自誕生之日起就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關系,文化定義著教育的內涵,教育建構著文化的“生命機制”。[10]
鄉村文化是華夏文明的肇始,是孕育民族精神和性格的搖籃。梁漱溟說:“中國的國命寄托在農業,寄托在農村。”[11]然而,在高速的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文化隨著一座座消逝的村落而日漸凋蔽。從2000年到2010年,我國自然村由363萬個銳減至271萬個,10年間減少了90多萬個,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個。[12]如此一來,鄉風、家風和民風失去了文化上的物質依托和精神依歸,進而導致珍貴的習慣風俗無以為繼,智慧的鄉規民約無以為守,實用的耕植經驗無以為用,樸實的鄉民性格無以為傲。村莊的破敗與文化的落寞互為因果,它們與孤獨的農人共同描繪了一幅蕭瑟的鄉村圖景。在不可逆的時代趨勢下,教育成為傳承鄉村文化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堡壘。
鄉村教育的文化責任在于激活教育自身的“生命機制”,擔承文化傳承的歷史使命。鄉村教育應當扎根鄉村文化深處汲取養分,建立教育與文化的深度對話,將土地里生長出的文化編譯成教育的語言和符號。一方面,鄉村教育成為“文化化”過程中的重要路徑,教育獲具文化屬性;另一方面,鄉村教育承擔著篩選、保存和改造文化的責任,使珍貴的鄉村文化通過鄉民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教育的本質是培養人,鄉村文化的教育責任是培養對鄉村文化知識上認識、價值上認可和心理上認同的“鄉民”。所以,鄉村教育要使鄉民成為理解鄉村文化的“文化獲得者”,喜歡鄉村文化的“文化欣賞者”以及宣傳鄉村文化的“文化自豪者”。鄉村教育不是鼓勵鄉民“走出鄉土”,而是讓其懷有愿意“走回鄉土”的情懷和自信,同時能夠吸引新質鄉民的歸入。
文化是傳承性的,鄉村的區位(偏遠)、樣態(聚落)和生產勞動(四季輪回)特征進一步強化了鄉村文化的穩定性、保守性和一元性。如果教育志在推動鄉村文化興盛,它必然不能違背文化傳承規律,應當尊重鄉村文化的核心價值,避免基于他者邏輯建構教育理解。這也意味著,鄉村教育的文化立場是本土的,文化思維是動態的,文化價值是服務于其內在發展的。
二、城鄉教育一體化與鄉村文化傳承的邏輯悖論
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構建理念預設著其與鄉村文化傳承的邏輯一致和價值適切,后者能夠在政策的推動下自然融入一體化建設體系。然而,鄉村文化的現實掙扎卻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兩者之間的關系。這很可能不是操作層面的失誤,而是根植于一體化與文化傳承意涵深處的邏輯悖論。
(一)整體思維與一元思維的系統差異
城鄉教育一體化是整合城鄉教育資源,將處于分隔狀態的城市教育與農村教育融合統整為一個教育共同體,將城鄉教育視為整體進行統籌發展的目標模式。[7]城鄉教育一體化既非農村教育城鎮化/城市化,也非鄉村化,其本質上是一種結構功能主義,以整體思維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發展的目標、速度、規模和質量,構建統合的穩定系統。這種整體思維選擇宏大視角,將城市教育和鄉村教育放入同一范疇,采用“以城帶鄉,以鄉促城”的模式,推動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
鄉村文化是基于歷史、地理、資源、生產方式等特色而生長出的區域文化。正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每個地區的文化具有極大的差異。刺繡、蠟染、編織、山歌、舞蹈等民間藝術都是某一地區或村落所獨有的文化遺產。“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文化范式反映了鄉村文化的一元思維,它只會依據本土文化的邏輯和視角保持生命力,文化資源僅在自成體系的文化圈內流動。所以,鄉土文化的傳承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特征,以特定場域為邊界,面向已獲文化資質的特定人群的有限文化繼替模式。
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整體思維屬于技術邏輯,鄉村文化傳承的一元思維則屬于觀念邏輯。人口、技術、資本、資源等都可以進行“整體化”的技術處理,唯獨文化難以如是。鄉村文化是在長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產勞動中形成的經驗文化,具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不可說性”。所以,鄉村文化的意蘊是無法進行技術化處理的,反之,強行的技術設計勢必消弭最本真的鄉土韻味。而且,鄉村文化傳承的區域生成邏輯也不適應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整體思維,兩者的價值理念和運行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當鄉村文化傳承同意被一體化系統所接納,鄉村文化也就失去了歷代堅守的身份。
(二)開放性與保守性的特性殊途
城鄉教育一體化是城鄉教育雙向溝通、良性互動、協同發展的區域開放系統。它打破了城鄉相互區隔的教育結構,在開放的動態系統中探索城鄉教育融合的機制。所以,城鄉教育一體化是資源整合型的結構式開放,包括城鄉教育之間的內部開放和城鄉教育共同體的外部開放。前者指城鄉教育面向彼此的全景式敞開,教育資源在區域間合理流動,教育質量獲得全面均衡的發展。后者指城鄉教育作為統一的教育系統,以主動、多元、創新的姿態參與外部世界互動,保持與政治、經濟、文化等系統對話,建立不同教育共同體之間跨區域和跨國別合作。
從文化的傳承與延續功能分析,文化為了保持自身的原生樣態和核心價值,需要在積極意義上維持自我的保守性。保守性在本體論上是文化的核心屬性,在價值論上是文化得以傳承的必要條件。鄉村文化是在人與人的交往關系和人與自然的勞動關系中形成的獨特價值觀及其表征方式。“熟人社會”中的交往關系和“靠天吃飯,賴地穿衣”的勞動關系孕育了追求“安穩”的生存哲學,“差序格局”和敬畏土地都說明了鄉村文化深層次的保守性。鄉村區域圈定的文化傳承邊界使鄉村文化具有超越時間與空間的穩定性,因為文化往往只在特定的區域形成、流轉和認可。可見,鄉村文化并非不愿走出鄉土,而是不能離開根脈,“離根”預示著文化失去了原初的精魂。
在此意義上,城鄉教育一體化的開放性與鄉村文化傳承的保守性在“變與不變”中就產生了沖突。變是開放的邏輯,不變是保守的態度,時代的變化已經使鄉村文化無從選擇自己的立場。當鄉村文化向外部世界敞開,它的核心價值和傳承方式會受觀念、制度、生產方式等因素的影響而被迫改變。城鄉教育一體化解構了鄉村文化自我保護的機制以及文化傳承的既定規則,而且它使鄉村文化沿著教育制度和日常生活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徑承續下去,這種生長又會同時作用于相同的群體,繼而不可避免地產生文化身份的困惑(我要去哪)或自卑(我要離開)。
(三)文化改造與自然承續的方法分歧
城鄉教育一體化文化建設是依循從分散到整合、從“落后”到“先進”的價值路向的文化改造。理論上,文化改造是城市文化和鄉村文化的雙向調適,兩者共同向一體化聚合,達成文化在教育上的融合。然而,城鄉教育一體化的立場卻非交互的,而是基于城市文化改造鄉村文化的單向立場,其蘊含著城市文化優于鄉村文化的價值預設。當然,在城鄉教育一體化的進程中,鄉村文化的改造是必然的。文化的價值良莠不齊,呈現形式異彩紛呈,運行方式也與教育截然不同,所以鄉村文化無法直接進入教育場域。它需要在教育理論的指導下,尊重教育規律,通過篩選和修整的方式,進行科學化、系統化和可操作性的改造。
文化是人類在生產生活中積累的經驗,文化傳承是在生命成長的整全環境中經驗的自然承續。融于生活的自然承續是文化傳承的原初方式,也是鄉村文化傳承的核心途徑。它具有兩類特征:生活生成和“因信稱義”。生活生成是自然承續的方法論解釋,鄉村文化是在春耕秋收、迎來送往的鄉土生活中自然生成的。“牛角掛書,柳枝為筆,沙地練字”的教育方式說明了鄉村文化傳承的耗散性和碎片化。“因信稱義”是自然承續的價值論規范,“信”是鄉村文化的認同,“義”是文化傳承的行為正義。只有鄉民對文化身份自信,才能導出文化傳承行為的自然發生。
文化改造和自然承續的路徑是完全不同的,一者是基于城市立場的外部改造,一者是基于鄉村立場的內部承續。如果用文化改造的邏輯代替自然承續,勢必會破壞鄉村文化傳承的原有生態。他者改造是程序化的技術處理,往往會忽略文化內在的歷史、規律和細節,丟失鄉村最珍貴的“精氣神”。梁漱溟認為,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浸入,一種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的殖民。這樣的教育塑造可謂對鄉村內在活力的侵蝕。[11]反之,如果鄉村文化繼續堅持自然承續,固步自封的觀念會剝奪鄉民“看世界”的機會,也會消弱文化的生命力。在“改”與“不改”的張力中產生的糾節最終只會作用于鄉村,城市一直都是處于既得利益位置的“旁觀者”。
(四)制度建設與觀念建設的建設思路不同
城鄉教育一體化的實質是制度建設,[12]是整合城鄉教育資源,統籌城鄉教育發展的體制機制。[1]城鄉教育二元分化的結構主要是由制度差異和制度壁壘造成的,只有創新教育體制機制才能解決這一問題。由此可見,制度建設是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的必然選擇。制度建設是一種政府行為,具有計劃性、強制性、穩定性和指標化的特點,政策是其主要表現形式。這也意味著,城鄉教育一體化是政策的醞釀、頒布和實施的過程。此外,制度建設是城鄉教育一體化框架的頂層設計,制度建設之后的具體行為則遵循政策指導下的自我運行邏輯,受政策下行方式、執行主體、操作規程等因素的影響。
鄉村文化的傳承即文化建設,文化的本質是人類的思想及其外化,所以鄉村文化建設的核心是觀念建設。它是一種態度的培養和認知的塑造,通常基于兩種特性(長期性和偶然性)和兩類中介(教育和環境)展開。文化觀的形成是日積月累的,觀念建設也是在長期的鄉村生活中漸漸完成的。而且,形塑文化觀的不是系統的知識,而是散布于鄉村生活中的種種偶然因素,例如歷史、故事、述說、體驗等等。這一意義上,觀念建設又具有間接性和生成性,它是通過教育和環境的中介,以及鄉土世界的真實棲居,影響鄉民對待文化的態度以及文化知識的獲得。
制度建設與觀念建設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建設材料和建設視角兩個方面。從前者分析,城鄉教育一體化依據政府制定的政策,鄉村文化傳承則賴于鄉民的態度。但是,鄉民的態度無法撼動政策的推行,政策的制訂往往又無視鄉民的態度。雙方的對峙又非“勢均力敵”,鄉村文化一定會在“經濟利益”的裹挾和多方“合謀”下成為犧牲品,這也是“鄉村荒漠化”產生的原因。從后者分析,制度建設從宏觀層面專注城鄉教育的結構調整,觀念建設則從微觀層面關心鄉民在鄉土生活中的文化態度。制度建設難以深入具體的文化生活,觀念建設也無法影響頂層的政策調整。這也導致了宏觀視角下鄉土文化被視為阻礙發展的頑疾,微觀視角下制度規劃忽視民聲和民生。
三、城鄉教育一體化與鄉村文化傳承的共生理念
城鄉教育一體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鄉村文化傳承是民族精神延續的原初根脈,兩者的邏輯沖突勢必會影響鄉村振興的時代使命。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的重點是弘揚鄉村文明,遏制鄉村教育衰敗;[13]鄉村文化傳承的意義是保持文化活力,培養能夠面向未來的鄉民。兩者在目標指向上存在某種價值契合,基于這一共識的闡釋、生發和建構將成為化解兩者邏輯悖論的可能。此外,城鄉教育一體化與鄉村文化傳承的邏輯悖論始于系統結構、本質屬性、運行方式和建設思路的整體性差異,所以兩者的沖突無法從本質上徹底解除,浮于形式的功能調和既無持續的遠見,也無深層的功效。在此情況下,我們可以嘗試擱置差異與沖突,引導兩者在不同的邏輯路向上尋求價值共識,立足長期可持續的教育發展,使階段性沖突走向整體性融合。這一共生理念即教育現代化的文化自覺。
教育現代化是與教育形態的變遷相伴的教育現代性不斷增長和實現的過程。[14]文化自覺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特色和發展趨向,從而增強自身文化轉型的能力,取得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15]文化環境影響著教育現代化的發展方向與進程,教育現代化則致力培養具有“文化自知之明”的“現代人”,所以教育現代化在一定意義上即文化現代化。甚至有學者指出:“如果沒有文化的現代化,教育的現代化也是沒有意義的。”[15]教育現代化的文化自覺是從教育與文化內部自然生長出的時代精神,鼓勵教育扎根本土和服務本土,利用區域文化特色和發展規律,培養具有文化自覺意識的現代公民。它主要表現在鄉村文化自覺和鄉村群體現代化兩個方面。
(一)鄉村文化自覺
費孝通認為,文化自覺的關鍵是“能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以及在社會大變動和大發展中,基于文化轉型尋求生路。[16]我們也可以改變下陳寅恪的表述“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一方面不忘本來鄉土之地位”。因為文化是流動和擴大的、變化和創新的,而且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同時強調維持和創新。所以,“文化自覺”既非“復舊”,也非“全盤他化”,而是要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與各種文化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條件。[17]而這一切的前提和基礎都是文化自覺的“自知之明”。
文化自覺本質上是正確處理文化交流、文化融通、文化創新、文化發展等一系列關系和問題的意識狀態、價值追求和精神境界。[18]它要求教育傳承鄉村文化,守住鄉土根脈;尊重鄉村文化的主體性,樹立鄉土自信;賦予鄉村文化新的內涵,保持鄉土競爭力。這是一個在不斷對話中尋求認同的過程,是在維持與創新的張力中探索出路的努力。教育形塑的鄉村文化自覺是開放的文化生態系統,既能扎根具有歷史意蘊的土地,又能通達具有時代精神的世界。“土地”與“世界”正是兩種意識、價值和精神的表征。所以,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不是“東風壓倒西風”的二元對立關系,而是彼此對話、相互補充、積極學習的共生關系。教育也不再竭力調和兩者之間的沖突,而是為雙方提供可以對話的平臺,引導其構建協和的文化生態。鄉村文化自覺的根本目的是“繁榮興盛農村文化,煥發鄉風文明新氣象”。面向傳統的鄉土文化傳承與面向未來的鄉風文明改造是基于自覺與發展的現代化思維,超越“變與不變”“改造與承續”的二元沖突,同步制度建設與觀念建設,尊重鄉村文化自由權而獲具自適應性的時代使命。
此外,文化自覺的主體是擁有這種文化的人,而不是文化本體。[18]鄉村文化自覺的落腳點是人的自覺,這也是實現文化傳承的重要抓手。它致力于使鄉民在了解本土文化脈絡與認同區域文化身份的基礎上,形成以“真善美”為標準的文化理解力、判斷力以及適應時代發展的生命力。因為自覺本身即人們的自我意識高度成熟,能夠對自己的存在、各種責任擔當、處置各種關系的問題的能力狀況,以及對自己精神成熟度的高度認同的狀況。[18]所以,鄉民的文化自覺是以知識論為基礎的心理狀態,包括對鄉村文化歷史的自覺識認和對鄉村文化身份的自覺認同。鄉村教育是培養鄉民文化自覺最重要的途徑,一方面建立鄉民與鄉村文化的歷史關系,引導其熟悉文化成長的完整脈絡,另一方面建立鄉民與鄉村文化的情感關系,喚醒其對滋養祖祖輩輩鄉土的“深沉熱愛”。由此可見,文化自覺又非停留于認識論上的文化感知,而是嵌入價值論的情感認同,即文化自覺之上的文化自信。一種基于理性認識之上的精神成熟度表現,既非自卑,也非自大,而是一種文化上知己知彼的高度自覺。[18]簡而言之,鄉民能夠吶喊出“我是農民的兒子,我深愛著這片土地!”
(二)鄉村群體現代化
教育現代化的根本目標是促進人的現代化。英格爾斯指出:“在整個國家向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人是一個基本的因素,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的人們是現代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的人格……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19]人的現代化是指人的現代性發生、發展的現實活動,包括人的價值觀念、思想道德、知識結構、行為方式由傳統性向現代性轉變,由傳統人向現代人轉變的過程。[14]在此意義上,鄉村群體現代化是指向未來美麗鄉村的完整意義上的人的現代化改造。謝岳和曹開雄指出:“人的現代化說到底就是一個文化現代化的問題。”[20]人是由文化形塑而成,人的現代化即文化現代化的表征。人又是文化的承續者,文化的現代化必須依靠人的現代化。所以,中國教育的宏大目的本質上是在探索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培養何種意義上的現代人,塑造何種意義上的現代生活方式。那么,鄉村群體的現代化就與鄉村文化的現代化建立起了同一性,而后者又是文化自覺的重要表征之一,如此一來,共生理念的兩類內涵也形成了互為推證的邏輯關系。
因此,人的現代化的根本目的是“文化人”的培養。現代性從根本上來說是為了轉變人的意向性結構,即在深層次上重構人的價值秩序。[21]鄉民的現代性價值內核即立足本土立場,具有開放視野,成為自覺賦予世界以意義的“頂天立地”的人。“頂天”是未來指向的后喻思維,能夠與外部世界自由對話,適應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在向世界和未來不斷敞開的過程中保持自信和學習力。這也是一種文化的“創新”能力,持續賦予鄉村文化和文化主體新的生命,提升其在時間(未來)和空間(世界)向度的競爭力。“立地”是歷史指向的前喻思維,在扎根與發展的邏輯下成長為有文化修養的現代人,“維持”“我曾經是誰”和“我現在是誰”的價值統一,建立主體與文化之間的“知情”關系。所以,了解鄉土根脈成為鄉民最核心的競爭資本,這也是城市在快速發展過程中所遺失的珍貴品質,例如歷史、人情、生態、沉思等等。
鄉村群體的現代化是面向整個鄉村世界的現代化改造,鄉民能意識到身處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張力之間的責任,并且能在其中張弛有度、游刃有余。鄉村群體的現代化既是一種能力,又是一種態度,并最終表現為主體的文化觀念。以“培養人”為目的的教育正是走向鄉村群體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知情意行等方面將鄉民培養成具有現代化素養的“文化人”。腳下土地的歷史、經驗、情感、智慧等需要教育去傳承,參與外部世界和未來社會決策和改造的話語、能力、責任等需要教育去培養。鄉村文化和群體現代化的邏輯前提是鄉村教育的現代化,它們共同構成一個整體性的鄉村現代化生態,而后者又以民主性和公平性、終身性和全時空性、生產性和社會性、個性性和創造性等為特征。[22]
由此可見,“文化自覺”和“現代化”最終都作用和指向于人,并在教育中形成內在統一,即“頂天立地的文化人”的形塑。前者偏向心理維度的身份構建和內省,后者強調發展維度的能力獲得與敞開。城鄉教育一體化與鄉村文化傳承在此建立了共同作為的邏輯起點和價值指歸。需要補充的是,義務教育是城鄉教育一體化的重心,但“一體化”絕非局限于此,它是以義務教育為基,統合基礎教育、社會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生態。因此,教育現代化的文化自覺是一種系統思維,而且具有較強的未來指向性。
四、城鄉教育一體化與鄉村文化傳承的共生策略
如何創造一種既適應現代化的挑戰又根基于中國文化特性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是中國教育現代化之真正問題所在。[15]教育現代化文化自覺的共生理念是價值層面的應然預設,其仍然需要在鄉村教育的實然土壤落地生根。從共生理念到共生策略實質上是鄉村教育文化自覺的現代化設計,是化解城鄉教育一體化與鄉村文化傳承困境的可行性和操作性論證。
(一)利用現代化的教育理念重塑鄉民的文化觀
城鄉教育一體化的目的是人的培養,鄉村文化傳承的核心是人的責任,所以共生策略的關鍵在于鄉民賦予文化的態度、理解和判斷,即鄉民的文化觀。在鄉村振興的轉型階段,鄉民文化觀的形塑將經歷極大的挑戰,它需要克服外部文化、生產方式變革、人口流動、數字化生活等諸多因素的干擾,而教育是突破這一困境的最佳路徑。
轉變落后文化觀,重塑新型文化觀,必須利用現代化的教育理念。首先,突顯教學區域特色,引導鄉民了解本土文化。鄉村教育應積極創建具有本土優勢的教學環境,充分利用地方性教學資源,增加鄉土知識的教學融入,創新教學方式的地域風格,幫助鄉民系統地走近、理解和體悟鄉村文化。由于文化本身的復雜性、模糊性和難以言說性,教育應重視對生活常識和故事的挖掘,引導鄉民與鄉土文化的“相遇”(encounters),在日常“敘事”(narratives)中達成文化形塑。當前,鄉村學校已經開始了相關探索和努力,并取得顯著成效,“國家教學成果獎”中頻繁出現的鄉村學校身影可見一斑。其次,利用多元文化教育的價值理念,培養鄉民文化認同。將鄉村文化放入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視野,引導鄉民感受不同文化的特色與價值,尊重區域間文化差異,在“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價值指引下培養鄉土文化主體意識。多元文化對鄉土世界的長期旁觀,一方面說明鄉村文化身份未獲覺識,另一方面也揭示一元邏輯對鄉村改造的“統籌”支配。所以,多元文化教育不僅是對鄉村文化地位和發展邏輯的修正或補償,更提供一種重構教育價值的全新思路。最后,推動鄉村教育對外開放,鼓勵鄉民進行文化改造。鄉村教育應建立與外部世界的合作關系,保證鄉民享有公平優質的教育服務,在開放的教育環境中,拓展鄉民的文化視野,培養文化創新精神與能力。落后、保守、封建、貧瘠等標簽被貼在鄉村文化身上的很大原因在于鄉村的封閉性,而只有努力通過教育以及讓教育走出去,發出自己的聲音,才能真正重塑文化形象,四川、江西、江蘇等地鄉村小學的聲音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聽到。
(二)構建城市教育與鄉村教育的“區隔—合作”機制
城市教育與鄉村教育的關系是橫亙在城鄉教育一體化與鄉村文化傳承之間最核心的問題。城鄉教育一體化致力建立相互融合的關系,鄉村文化傳承則堅持彼此的區隔發展。化解沖突的關鍵是找到更為合理的關系運行機制,消除兩者在城鄉教育關系上的分歧。“區隔—合作”機制是建立在雙方對“關系需求”共同滿足基礎上的最優方案,要求城市教育和鄉村教育保持獨立的運行邏輯,在相互區隔的系統結構中,建立平等互惠共享的合作關系。
城市教育與鄉村教育是兩種相互區別的教育系統,而且這種差異性會持續存在。任何盲目將兩者“合二為一”的機械邏輯都是對現實與教育規律的違背。在即定環境下,鄉村教育不需要“你送我一所學校”,更希望“我有自己的學校”。它能結合本土文化,發揮教育智慧,利用鄉村資源,建立區域教育特色,培養學生在未來可以自由遷移的知識、能力、情感、態度和價值觀,使鄉民成為在不同文化間自由流動的人。誠然,我們希望破除二元結構,但要建立二元思維,在尊重差異和利用差異的基礎上因地制宜。鄉村教育要探索出能夠發揮自身特色和優勢的區隔道路。盡管國家教育方針對人才培養的總體規格不變,但是鄉村教育在“殊途同歸”的邏輯下依然能夠尋找結構化的區隔點,核心在于其構建思路是“自我的”,而非“他者的”。從教學目標(階段性)、內容、方法、手段、模式等方面祛除“看齊”或“模仿”思維,在不斷的回身中尋找“差異”和“特色”。簡而言之,城市有引以為傲的“城市學校”,鄉村也要有為之自豪的“鄉村學校”。
此外,城市教育與鄉村教育合作的難點又非采用何種視角與立場,而是教育公平的實現。在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下,城市教育資源明顯優于鄉村,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何以保證資源的合理配置。一方面,鼓勵城鄉教育合作,通過教學理念、教學資源、師資等方面的優勢共享,共同提高教育質量,實現城鄉教育均衡發展,例如遠程教學、教師輪崗等。這里的抓手主要在于利用政策推動和現實驅動,促進教育資源在城鄉間合理流動。另一方面,面對城鄉資源配置不均無法短期解決的局面,鄉村學校在深挖本土資源的同時,還應積極尋求各種形式的支持,包括政府、企業、社會、個人等基金或項目,而非被動地等待資助。同時,他們還可以通過對特色教育的宣傳,合理利用“暈輪效應”,擴大社會影響,尋求資源補償。
(三)探索鄉村教育文化自覺階段化與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城鄉教育一體化是以目標為導向的階段化發展模式,包括鄉育城市、城鄉分離、城鄉對立、城鄉融合和城鄉一體五個步驟。[23]它遵循在體制框架內穩步發展的規律。鄉村文化傳承是代際間文化繼替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旨在保證本土根脈一代代源遠流長。它遵行在觀念層面上長遠發展的規律。鄉村教育文化自覺在兩者的共生過程中自然要恪守共同的發展規律。
一方面,遵循穩步發展的規律,探索鄉村教育文化自覺的階段化發展模式。鄉村教育文化自覺應當立足社會和教育現實,結合文化特征和屬性,走科學穩健的漸進式發展道路。根據城鄉教育一體化的發展模式和文化傳承的要求,鄉村教育文化自覺可以劃分為政策推動的文化寫入階段、環境催動的文化合作階段和需求驅動的文化自覺階段。第一階段,完善鄉村教育政策,要求將鄉村文化融入教學活動。文化寫入是政策的強制推動,通常包括目標設計、內容編排、任務執行等方面。然而,政策的落地效果主要取決于中觀和微觀層面的實施效力,兩者之間的一致性受操作影響較大,很容易產生價值偏差。我們當前正處于這一階段。第二階段,加強鄉村教育與其他(非)教育系統的合作,積極滿足環境變化的需求。合作的初衷是資源互補和互惠,所以它是鄉村教育向外部系統尋求對話或者被問尋的過程,其本質上是二元或多元思維的表征。城鄉教育一體化的邏輯起點即著眼于此。第三階段,激活鄉村教育的文化自覺意識,實現鄉村社會文化傳承的自動化。在鄉村、鄉村文化和鄉村教育真正實現現代化之時,整全意義的文化自覺才真正可以實現,它是在理解、內化和繼替過程中的完全自動化。盡管如此,文化自覺的理念依然可以在前兩個階段發揮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遵行長遠發展的規律,探索鄉村教育文化自覺的可持續發展模式。鄉村教育文化自覺是在長期的教育生活中生成,并服務于教育與文化長遠發展的使命。教育和文化傳承都具有長期性,鄉村教育文化自覺的培養也不能一蹴而就,應保持與教育和社會現代化同步,在鄉村教育與鄉村文化的逐步轉身中耐心調整與適應。文化自覺是一種能力、意識、價值和境界,它是在鄉土的棲居中伴隨著主體性的增強而顯現的。所以,它要求人在教育世界與鄉土文明持續對話,在一次次的“相遇”、述說和沉思中,漸漸形塑主體的能力、意識、價值和境界。此外,當前社會習慣以改革的邏輯看待一切事物的發展。然而,冷靜之于改革的意義要遠遠高于熱情,因為理性才是發展的洞見,教育尤其需要這份冷靜。鄉村教育的文化自覺不能追求斷崖式的功利改革,應著眼于鄉村教育和鄉村社會的未來,以科學發展觀指導城鄉教育一體化與鄉村文化傳承的共生、共融和共榮。
[1] 褚宏啟. 城鄉教育一體化:體系重構與制度創新——中國教育二元結構及其破解[J]. 教育研究, 2009(11): 3-10, 26.
[2] 習近平.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EB/OL]. (2017- 10-27)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3]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EB/OL]. (2018-02-05) http://www.moa.gov.cn/ztzl/ yhwj2018/zxgz/201802/t20180205_6136444.htm.
[4] 費孝通. 鄉土中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1.
[5] 霍爾,尼茲,周曉虹. 文化:社會學的視野[M]. 徐彬,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2: 25, 20.
[6]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EB/OL].(2018 -09-26)http://www.gov.cn/xinwen/2018- 09/ 26/ content_5325534.htm.
[7] 李玲,宋乃慶,龔春燕,等. 城鄉教育一體化: 理論、指標與測算[J]. 教育研究, 2012(2): 41-48.
[8] 魏峰. 城鄉教育一體化:基于文化視角的分析[J]. 復旦教育論壇, 2010(5): 20-24.
[9] 克利福德·格爾茨. 文化的解釋[M]. 韓莉, 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 1999: 5.
[10]王樂. 村落文化的傳承與鄉村學校的使命[J]. 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 2016(6): 26-32.
[11]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第一卷[M].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5: 672.
[12]楊衛安,鄔志輝. 城鄉教育一體化: 范圍、實質與研究路徑[J]. 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 2013(4): 5-9.
[13]鄔志輝. 當前我國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的核心問題探討[J]. 教育發展研究,2012(17): 8-13.
[14]褚宏啟. 教育現代化的本質與評價——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現代化[J]. 教育研究, 2013(11): 4- 10.
[15]高偉. 論中國教育的現代化——基于文化現代化的視角[J]. 陜西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5(6) : 33-140.
[16]費孝通. 文化自覺的思想來源與現實意義[J]. 文史哲, 2003(3): 15-16.
[17]費孝通. 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思考[J]. 思想戰線, 2004, 30(2): 1-6.
[18]邱柏生. 論文化自覺、文化自信需要對待的若干問題[J]. 思想理論教育, 2012(1): 14-19.
[19]英格爾斯. 人的現代化[M]. 殷陸軍, 譯.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86.
[20]謝岳,曹開雄. 現代化意義上的文化自覺——改革開放 30 年文化現代化的過程與經驗[J]. 上海交通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6): 15-22.
[21]劉小楓. 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M].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1998: 16.
[22]顧明遠. 試論教育現代化的基本特征[J]. 教育研究, 2012(9): 4-10.
[23]周加來. 城市化·城鎮化·農村城市化·城鄉一體化——城市化概念辨析[J]. 中國農村經濟, 2001(5): 40-44.
Dilemma and Resolu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WANG Le, MA Xiao-fang
(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approach toward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serves a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national spirit. The realistic struggle of rural culture reveals the logical dilemma arising from the systematic difference between overall thinking and unitary view, openness and conservatism,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natural inheritance, and 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To resolve these dilemmas, the authors argued that steps can be taken to enhance the symbiotic concept of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set aside differences, and seek value consensus on different logical paths. The symbiotic strategy is an operational design to resolve the logical paradox through using modernized educational concepts to reshape the cultural views of rural residents, constructing the “jurisdiction-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and exploring the phased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 of rural education .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rural cultur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auto-psyche
G40-02
A
1008-0627(2021)01-0019-1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一般項目“西部城市邊緣區失地農民的生存壓力與教育支持研究”(17SZYB22);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重大招標課題“振興鄉村戰略中的農村教育現代化研究”(VHA180004);2019年留基委青年骨干教師出國研修項目
王樂(1984-),男,安徽宿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多元文化教育和教育基本理論。E-mail:leowang@snnu.edu.cn
(責任編輯 周 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