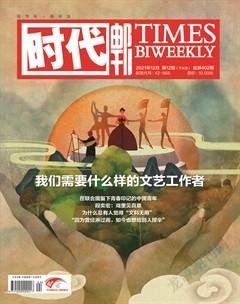文藝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任冠青
有人說,文藝是那些與生活基本需求無關,沒有它卻令心靈空虛、使人生蒼白的事物。文藝工作者踏足深耕的,正是一片片神圣如斯的靈魂之地。我們期待德藝兼備、人格卓越的文藝工作者,是因為我們對美好生活有著無限向往,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懷以光明期冀。
談及“文藝工作者”這一具體指稱,很多人可能會產生相對晚近的印象,可若說起中國人從事文藝創作的歷史,卻堪稱源遠流長。伏羲畫卦,倉頡造字,不僅開啟了中國書畫同源的先河,也由此造就了中國藝術創作的濫觴。自此之后,一代代留名青史的文學、藝術家們,窮盡丹青之妙,探究文字之美,在音樂、園林、瓷器、戲劇、影視等諸多方面均有建樹。他們見證著時代精神的變遷,亦在時代大潮的滋養下綻放光彩。
魏晉之際,是中國諸多文藝形式的發源時期,也展露出不少中國德藝追求的價值導向。文學上,曹丕面對社會動亂立下“救民涂炭”之志,曹植“勠力上國,流惠下民”的抱負,無不映射著中國文人心懷家國的思想基調。
顧愷之以《洛神賦》為靈感,用綺麗而唯美的筆觸,重現了曹植與洛神的相遇場景。這一“神還原”背后,不僅是繪畫技藝的高超,更是一位藝術家注重人文意識,力圖傳達人之豐富情感的不懈追求。書圣王羲之“飄若浮云,矯若驚龍”的行書,離不開他苦練書法、洗筆成墨池的不懈努力;《蘭亭集序》中“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感悟,則展現出其作為文學家對人生多重況味的深入探討。
大唐盛世,包容開放,文教勃興。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柳宗元、顏真卿、歐陽詢、吳道子……如雷貫耳的名字,奢侈地在同一個時代綻放生命。他們也許風格迥異,卻共同譜寫了開放、多元的文藝盛景。
由于重用文臣,獎勵學藝,宋代才學之士輩出,支撐起長達三百余年的昌盛文運。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揮筆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蘇軾一生屢遭貶謫、歷經坎坷,卻仍有“一蓑煙雨任平生”的瀟灑曠達和“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人間大愛,這些有關人生的思索,時至今日仍給世人以慰藉和力量。
從唐詩、宋詞,到元曲、明清小說,從書法、繪畫,到音樂、京劇……幾千年來,中國的文化瑰寶燦若星辰。新中國成立以來,不管是在小說、話劇,還是電影、影視劇領域,同樣涌現出一大批腳踏實地、低調謙遜、獻身藝術的文藝工作者。
話劇領域,話劇演員于是之始終堅守“戲比天大”的原則,為了扮演好一個角色,他認真揣摩其個人經歷和心理,最后寫出了8000多字的人物小傳。他將《茶館》中王利發的形象詮釋得如此貼切,以至于這部戲首演時,作者老舍難抑激動,回家便寫下一副對聯:“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幾乎?”而收到對聯后的于是之,并未拿給任何人炫耀,只是將其悄悄鎖在抽屜里珍藏。他的名片上,沒有任何讓人炫目的頭銜,只有平平淡淡五個字:演員于是之。
在影視劇領域,老一輩演員對“演員”這個職業尤其癡迷和執著。演員秦怡一生經歷極其波折,在一人照顧患有重病的丈夫和兒子的沉重負擔下,依然塑造了“芳林嫂”“馬蘭”等經典女性形象,直到年逾九旬,還登上青藏高原,自籌資金自編自演拍攝了電影《青海湖畔》。每次出現在人們面前,她總是那樣優雅和美麗,眼眸明亮而有神,永遠彰顯著“演員”的精氣神。
演員于藍從《翠崗紅旗》《龍須溝》,再到《林家鋪子》《烈火中永生》,在銀幕上塑造了或光彩照人或英勇無畏的角色,處處都是掌聲和喝彩,她卻因自己臉部受傷淡出銀幕,轉身投入兒童電影的制作,致力于為中國兒童拍出屬于他們的影片,直到80歲才退休。
新時代的中國也涌現出一批有使命有擔當的文藝工作者。近幾年,鋼琴藝術家、聯合國和平使者郎朗的藝術基金會持續向各地捐贈“快樂的琴鍵”音樂教室,幫助鄉村學校改善音樂教學條件,提高音樂教學水平,他說:“音樂家不能只是構建自己精彩的舞臺人生,而要開始去思考,如何讓音樂表達我們對世界的愛,讓每個孩子都能從音樂里面得到心靈的提升。”青年歌唱藝術家李玉剛為了深刻地演繹昭君故事,曾率團隊重走昭君3000多公里出塞之路,先后百易其稿、耗時6年多時間,將之注入舞臺,雕琢委婉細膩的昭君形象。青年音樂人張藝興說:“青年人應當積極投入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揚中去,其間無數文化‘寶山富礦’值得去守護、發掘、傳揚。當代青年要用心呵護民族文化寶藏金山、書寫中華文化新篇章。”
文學領域,莫言用一個小村莊的故事,剖析著人性,展現著一位中國作家對現實的觀察和洞見。2012年,他成為首位中國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有力推動著中國文學與世界的深入對話。作家劉慈欣則用“旺盛的精力建成了一個光年尺度上的展覽館”。他的《三體》三部曲既有豐富的想象力,又有對人性善惡的終極追問,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科幻文學的里程碑之作……
可以說,一部中國文藝工作者簡史,正是滿目星辰、可圈可點的中華文明史。一代代技藝精湛、積累深厚的文藝賢達,總是能為人帶來無盡的審美愉悅和迷人的精神享受,他們以敏銳的觸角捕捉時代脈搏,讓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不斷煥發活力。
在探討文藝工作者的重要意義之前,不妨展開這樣一番思想實驗:試想一下,沒有文藝、沒有文藝工作者的世界會是怎樣的?
當你感到煩躁、焦慮時,再也無法拿起耳機,用舒緩的音樂撫平內心的褶皺。無聊時,再也沒有藝術展覽、話劇、脫口秀供你消遣、社交和思考。父輩和年輕人之間,再也沒有經典作品作為彼此交流的載體。人生,將如二進制一般簡單、乏味而單調。通過這樣的思想實驗,文藝工作者的社會和文明價值也漸次浮現。
優秀的藝術工作者,能夠將人引入藝術臻境,給人帶來跨越語言、民族的審美享受。2001年,譚盾憑借《臥虎藏龍》中的音樂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音樂獎。即便不熟知劇情,人們也能感受到譚盾音樂中的俠氣傲骨,其中有刀光劍影,也有桀驁不馴的靈魂,總能讓人聽得感慨萬千,深深思索電影“江湖里臥虎藏龍,人心又何嘗不是”的主旨。韓愈在《聽穎師彈琴》中,曾有這樣兩句精辟的表述: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無論是音樂、文學還是繪畫,優秀的文藝工作者都能通過自己的感知,超越形式和語言的束縛,讓人產生關于慈悲、熱情、自然、悲愴等不同面向的藝術美感。
潛移默化地影響時人、后人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也是文藝工作者的獨特作用。
2020年,一場“千古風流人物”大展在故宮文華殿展出,78件(套)與蘇軾有關的精品文物同觀眾見面。蘇軾,一直是中國歷史上無法繞開的文化標桿。其實,他的一生并不順遂,做官屢遭貶謫。人們之所以對其難以忘懷,更多是因為他作為文學家、書法家所傳達的那種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被貶后,他并未怨天尤人、愁容滿面,而是瀟灑地吟出那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明知是來到并不受重視的小城、頂著無關痛癢的頭銜,他卻能盡力為百姓做實事,最后坦蕩地說出“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文藝工作者是高舉時代旗幟、反映社會思潮的先驅。2019年,學習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八家出版機構聯合推出了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透過這套書籍,人們能清晰地看到我國人民生活圖景和社會的全方位變革。王蒙、陳忠實、賈平凹、王安憶、路遙、畢飛宇……這些作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既有對日常瑣碎的獨到觀察,又有對時代脈搏的深刻洞察。他們用如椽巨筆刻畫了楊子榮、李云龍、孫少平等經典角色,記錄了新中國初期從百廢待興到蓬勃發展的艱辛歷程,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探索,以及改革開放后銳意改革、敢為人先的時代風貌。
魯迅先生曾說過:“要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藝。”時隔多年,人們會發現,總有一些文藝工作者的肺腑之言、傾心之作能打破時空界限,凝結成永恒的民族記憶。
抗疫至堅至難之時,志愿者們最愛引用的是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是李白的“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在中國人民全力抗戰的危急時刻,徐悲鴻以一幅充滿力量、振奮人心的《愚公移山》,傳達了一個古老民族勢不可當的決心與毅力;“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這首創作于40多年前的歌曲,時至今日仍具有凝聚民族身份認同的動人力量。
這些文藝工作者用心血和真情灌注的傾心之作,總能打破時空界限,引發廣泛而持久的情感共鳴,最終凝結成永恒的民族記憶。
如今,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中國故事展現出無與倫比的時代魅力。與此同時,隨著移動媒體和大眾文娛的發展,包括藝人、明星在內的文藝工作者更是成為熱搜和頭條新聞的常客。他們在做什么,背后呈現出怎樣的道德準則和價值指向,會對大眾起到不容忽視的影響。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毫不諱言當下文藝創作中的問題。他曾同幾位藝術家交談,談及當前文藝最突出的問題,他們不約而同地說了兩個字:浮躁。
一些創作者粗制濫造、胡編亂寫,抄襲模仿、機械化生產的問題時常見諸報端;部分演藝人員全然丟失了專業人士的較真、講究和體面,在現場隨意改動劇本,甚至不記臺詞,只念出一大堆“123456……”的數字來做假;偷稅逃稅,涉嫌吸毒、強奸,更是擊穿了法律和道德的基本底線。
當此之時,激濁揚清、弘揚藝德正道尤顯必要。
明辨是非,注重人品、藝德修養,是文藝工作者的必修課。清代畫家王昱曾有言: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概;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筆端。其實,“文如其人”所說的,又何嘗不是這個道理。
歷史上,梅蘭芳“有所不為”的藝格傲骨曾讓無數人動容。在家國危難之際,他蓄須明志,堅決不為日軍表演。直到抗戰勝利后,梅蘭芳才剃掉胡須,重新為中國觀眾表演。文藝工作者的是非之辨,關乎為誰服務這一根本方向;人品藝德的修養,決定著藝術作品的氣韻底色。
刨除雜念、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文藝工作者的安身立命之本。談及汪曾祺的文字,世人常有宛若天成之感。然而這“妙造自然”的效果,卻是作者一筆筆用心打磨的。汪曾祺曾說自己寫小說有如揉面,一字一句都在腦中反復揉,直到軟熟、筋道、有勁兒了才下筆。
前段時間,《紅樓夢》等經典老劇在網絡上線,吸引眾多年輕人刷屏觀看。這部老劇之所以能在34年間重播1500多次,離不開當年文藝創作者的共同努力。為使演員了解時代背景,劇組特地邀請周汝昌等紅學專家授課;由于原著中有不少類似“花梨大理石大案”“汝窯花囊”等家居描述,主創者還專門聘請沈從文、朱家溍等大家作為顧問。文藝工作者能用心、講究至此,創作出的作品又怎會不擊中人心呢?
厚積薄發,不斷提升自己的知識儲備和文化素養,會使文藝工作者走得更遠。畫家董其昌曾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不管是繪畫、為文,還是表演,如果沒有深厚的內功和文化積淀,創作出來的作品就很容易流于表面、過于膚淺。
表演藝術家李雪健為演好《楊善洲》,曾徒步考察他生前走過的山山水水。在扮演焦裕祿之前,他還會精細到閱讀不同版本的人物傳記。李雪健說:“我認為想當一個稱職的好演員,不學習不讀書不行,書可以幫助一個人從藝匠變成藝術家,這是我的理想。”用踏實對抗浮躁,在腳踏實地的積累中從事藝術工作,呈現出的將是厚積薄發的無盡力量。
著眼現實,與時代同頻共振,是文藝工作者不容推卸的責任。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文藝工作者要學習社會,這就是說,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和各自狀況,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藝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
前段時間,一些都市劇之所以被網友吐槽過于“懸浮”,正是因為編劇、導演等創作者并未扎根現實。當然,文藝創作應該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不是簡單照搬。作家孫犁就曾強調“洗煉”的重要性,他認為:作家如果把群眾的口頭語言“隨拉隨用,任意堆積”,就是誤入歧途,而是要像淘米一樣洗去泥沙,像煉鋼一樣取出精華。
以文藝載道,傳遞真、善、美的價值觀,是社會期待看到文藝工作者的樣貌。傅雷在給傅聰的家書中強調:真誠是第一把藝術的鑰匙。如今,我們去聽傅聰彈奏的肖邦,就好像流水一般,全無矯揉造作之感,那是真誠與美感的完美結合。相反,如果只是把文藝當作一種“生意”,甚至向流量低頭、傳遞扭曲的價值觀,文藝創作就是毫無靈魂的。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相信在文藝界激濁揚清、逐漸規范化發展的今天,必將涌現出更多崇德尚藝、充滿活力的文藝工作者。我們期待看到他們用精湛的技藝創作出不朽的作品,以深刻的洞悉記錄當下,譜寫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