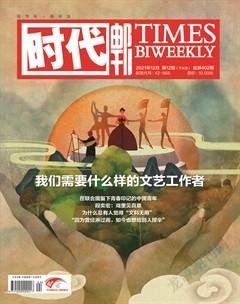許淵沖:我的同學楊振寧
許淵沖

在人生成功的過程中,要具有三種因素:一是天才。二是努力。三是命。
在我認識的同學中,楊振寧的成功是三種因素都具備了的。第一,先談天才。他四歲就認字,他的母親教了他三千多個字;而我四歲時才學會三百個字,我的母親就去世了。他五歲讀《龍文鞭影》,雖然不懂意思,卻能背得滾瓜爛熟;而我只會看白話小說,背《水滸》一百零八將。只有造型藝術方面,他用泥做的雞讓他的父親誤以為是一段藕,而我卻會畫唐僧取經。可見我長于形象思維,而他的邏輯思維卻遠遠超過了常人。
馮友蘭先生說,成功的人考試分數不一定高。這話對我來說不錯,因為我雖然翻譯了幾十本詩詞,但“翻譯”課和“英詩”課考試的分數都在80分以下;而楊振寧卻是分數高,又很成功。他考入西南聯大時,是兩萬人中的第二名。“大一英文”的期末考試兩個小時,他只一個小時就交了卷,成績是全班第一。而“物理”和“微積分”課的考試,他不是100分就是99分,無怪乎他小時候就說將來要得諾貝爾獎了。這不是天才嗎?
成功的第二個因素是努力。每個人應該做的事如果做得盡善盡美,那就是成功。楊振寧在初中的兩個暑假里,跟清華大學歷史系的高材生丁則良學上古的歷史知識和《孟子》,結果他全部《孟子》都背得出來。這不是盡善盡美嗎?而我的歷史知識卻是聽鄉下大伯講《三國演義》,自己看《說唐演義全傳》等書得來的。至于《孟子》,我只會背開頭一句:“孟子見梁惠王”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我是學文的,他是學理的。這樣一比,更看得出差距多么大了。
楊振寧的父親武之教授說:“1928年我回國時,振寧六歲。在廈門和在清華園,我已感到他很聰明,領悟能力很強,能舉一反三,能推理,還善于觀察。他的表達能力也不錯,在北平崇德中學念書時,參加演講比賽,得過兩個銀盾。他的演講稿是他自己準備的。”比起他來,我的領悟力、推理力、觀察力都相差很遠;只有表達力,他更善于說理,我更長于抒情。我在小學演講得過第二,中學英語演講也得過第二,所以后來在大學講課,還能有吸引力,甚至有感染力。
振寧的二弟振平說:“六歲的大哥常去海濱散步,很多孩子都在拾貝殼。大哥挑的貝殼常常很精致,但多半是極小的。父親說他覺得那是振寧的觀察力不同于常人的一個表現。”而我在畫牛魔王的時候,卻只畫了牛魔王的兩只角,沒有畫耳朵。因為我不知道牛耳朵畫在什么地方,可見我的觀察力差。
振平又說:“振寧生來是個‘左撇子’。母親費了一番精力把大哥吃飯、寫字改成右手,可是他打乒乓球、彈彈子、扔瓦片,仍舊自然地用左手。因為人的左腦控制右手,而右腦控制左手。我常常在想他后來異乎尋常的成就也許和兩邊腦子同時運用有關系。”我寫字、打乒乓球,從來都用右手,所以重文輕理,不如他文理兼優了。
振平還說:“念書對振寧是很不費勁兒的。他七歲就進了小學三年級。一般孩子對念書覺得是苦事,他則恰恰相反,他生來就有極強的好奇心……有時翻開大哥高中時的國文課本,記得在李白的《將進酒》長詩后面有他寫的幾個字:‘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絕對!’多年以后我問他為何把王維《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將進酒》的一句湊在一起,他說那是父親當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個酒家看到的一副對聯。”

振平還說:“大哥常和一群年紀相當的教職員子弟騎車在清華園到處跑。他說他們常常從氣象臺所在的坡頂上騎車沖下來,在一段沒有欄桿而只用兩片木板搭成的小橋上疾馳而過。車行急速,十分過癮。”
我在中學時也喜歡騎自行車從坡頂上沖下來,但不是沖上獨木橋,而是平坦的陽關大道。江西南昌第二中學從大門到二門之間有一道門檻,門檻正中有個缺口,只能過一輛自行車,但前輪和后輪必須成一直線,否則車子就會摔倒。我也喜歡騎車從缺口過,過了就得意洋洋,過不了也不會摔跤。這說明振寧騎車力求盡善盡美,我卻甘居中游。
武之先生總結說,振寧“天資聰穎,得天獨厚,又刻苦努力,竟集學問之大成,成為世界級的科學家,已對人類作出重要貢獻,為中華民族爭光”。這就是說,在取得成功的三個因素中,他既有先天的才能,又有后天的努力。那么,第三個因素人生的機遇如何呢?
楊振寧自己說:“從1929年到抗戰開始那一年(1937年),清華園的八年在我回憶中是非常美麗、非常幸福的。那時中國社會十分動蕩,內憂外患,困難很多。但我們生活在清華園的圍墻里頭,不大與外界接觸。”這就是他得天獨厚的童年。1938年,他在昆華中學念高中二年級,卻以同等學力考取了西南聯大。據振平說,他是兩萬考生中的第二名。我也在同一年考取聯大,是外文系的第七名。第一名是江蘇才女張蘇生,她“大一英文”的成績最高,比振寧和我都高十分。但大二時上吳宓教授的“歐洲文學史”,我的考試成績居然比她高出兩分,這就增加了我學好外文的自信心。有一次我和她合作打橋牌(潘家洵教授音譯為“不立志”),本來是一副“大滿貫”的牌,她卻“不立志”,只叫到“三比大”就剎車了。這似乎預示了我們后來不同的命運。1942年,她和楊振寧同時考入清華研究生院(那時叫研究院)。我因為應征到美國志愿空軍去做英文翻譯,直到1944年才入研究院。
1944年,楊振寧考取清華公費留學美國,這是他一生成功的一個重要機遇。同時考取的有聯大工學院的助教張燮,張燮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他和熊傳詔同班。熊傳詔是文科冠軍,張燮是理科冠軍,曾得江西省數學比賽第一名。來聯大后,楊振寧是理學院的狀元,張燮是工學院的狀元。但1957年楊振寧得諾貝爾獎時,張燮卻在云南大學被打成了右派,從此一蹶不振。兩個天才的命運如此不同,真有天淵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