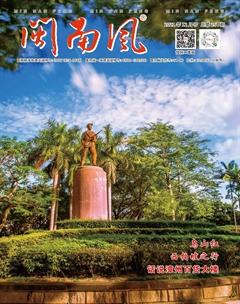詩山我的故鄉
陳金福
詩山,一個富有詩意的地名。早在古唐朝以前,就有“山頭城”之稱。南宋理學家朱熹瞻謁“開八閩文風之先”的歐陽詹,見歐陽詹在高蓋山讀書處留下的眾多詩詞佳作,而感嘆“此詩山也”。從此,詩山地名一直延用至今。
詩山,我的故鄉。它是著名的僑鄉,亦是南安五大古集鎮之一。歷史悠久,人杰地靈。
多少時光,隨風雨飄過,多少流年,在歲月里浮沉。我游走他鄉,顛簸陌上,一顆心依然拴系著家鄉。綿綿的鄉愁,牽念著煙雨江波、溪水田園、稻麥飄香。
光陰荏苒,歲月如梭。離開家鄉47載,似水的流年,帶走一次次淡淡的鄉思;漫漫的歲月,沉淀著一份深深的眷念;濃濃的鄉愁,伴隨時光走遠,愈發在心海里涌動著波濤。莫不是歲月風霜,青絲染鬢而感嘆鄉愁漸漸地凝重。
詩山,在我的心里,如慈母般具有寬厚的情懷,淳樸、堅毅、柔韌、包容。走出家鄉日久,漸漸感受故鄉蘊藏著深厚內涵,飽蘸著泥土芳香,疊加了歲月的醇厚,增添了我思鄉的那份情愫。
詩山,一個不算大的古鎮,面積96平方公里,人口9萬人。是一個人脈廣博,聯絡著世界,情牽東南亞、港澳臺等地區,有著絲絲縷縷的海外人文融合、生活浸染、信息交流的脈絡,猶如四面來風,吹拂著這片養育我的土地。
我是一個地道的詩山人。鄉音重,鄉愁濃,在這片土地,度過學生時代,渾身浸透著濃厚的鄉土味。時光遠去,沖刷著我十八載珍藏的記憶,依然割舍不斷那份鄉愁的纏綿。
詩山,是一片丘陵地帶,四面環山。小山低矮,河床岸窄,溪流水少,一條條淺淺的小溪,穿梭在山間田野。潺潺流水聲,宛如清亮悠揚的音樂,遠遠近近,回蕩在茫茫的曠野。
高蓋山,我家附近海拔最高的山。站在家門口,一眼就能望見她雄偉高大的身軀。每天早晨,聳立的山峰,漂浮著薄霧輕紗,縷縷白云繚繞,輕漫舒卷,微微歡笑,悠悠蕩蕩,讓我看得入神,怡然陶醉。

我從小吮吸著家鄉山水的乳汁,在這塊小盆地溫暖的襁褓里長大。家鄉的山水,一草一木,村莊、田野、山巒、溪流……像一幅地形圖,凹凸的地形,蜿蜒的田間小路,村中的池塘,房前屋后的龍眼、荔枝樹,一點一滴、深深淺淺地標注出來,刻印在心里;家鄉的鹵面、炸肉丸、炒地瓜粉、珠包、麻棗等風味小吃及特產,香溢在嘴里。一串串綿綿的鄉愁,如麥芽糖似的牽扯不斷,一直縈懷在我記憶的腦海,時而泛起一道道漣漪。
家鄉的山水,淳樸、溫婉、清新、甜潤,看起來不顯眼的山谷,淌下去水不深的溪流,傾吐著甘泉乳汁,像母親哺育兒女一樣,無私奉獻,恩澤著一代又一代人。
家鄉這塊土地,從不向災害低頭,從不向貧窮屈服,總是笑迎風雨,挺起腰,昂著頭,艱難地跋涉,養育著一方百姓,滋潤著十里八鄉。
早在20世紀30年代,這里人稠地狹,田園不足于耕,為生活所迫,逃避壯丁,一批批男兒勇闖天涯,紛紛踏波蹈浪,離鄉別井,漂洋越海下南洋,投奔到東南亞國家苦渡謀生。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成了很多詩山人棲居、謀生、創業的選擇。他們艱苦卓絕打拼,從小到大,慢慢立足成長,成就了自己一番事業。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有一批接著一批詩山人,到港、澳、臺等地區打拼求職,安家樂業。旅居外地的人與家鄉有著血緣、情緣、商緣的牽連,編織了一條條紐帶,情系著家鄉,夢牽著海外。詩山這個僑鄉,至今旅居海外及港澳臺約 16萬之多。
每逢新春佳節,詩山的海外、港澳臺親人紛至沓來,帶著思念,帶著投資熱情、項目資金、商貿信息,交流互通,傳遞資訊。他們帶來了觀念、穿著、追求、時尚的變化,讓古老的重鎮注入了青春活力,驅動了發展。

家鄉在旅居海外、港澳的僑賢扶助下,興業創業,經濟發展,充滿生機。雨傘在這里撐開了一片天,一夜間,家鄉變成中國雨傘城。“南安雨傘創奇跡,世界十把有其一”。2020年9月1日,阿里研究院公布當年淘寶鎮,詩山榜上有名。
家鄉的詩山,又是一個古跡傳承歷史的地方。鳳山寺是家鄉一座聞名遐邇、香火鼎盛的寺廟。建于五代后晉天福初年。曾遭破壞、損毀,歷經重建、修繕的波折。今天的鳳山寺,在不斷修葺的過程中,自有別樣的風韻,吸引游客景仰的目光和贊嘆。它矗立于詩山鎮西北角鳳山麓,與高蓋山相遙望,相呼應,俯瞰“山頭城”全景,周圍茂林蔥翠,花草飄香,秀麗如畫。每天來自八方的信徒,蜂涌而至,虔誠膜拜。新春佳節,更是人山人海,香火繚繞,一片熱鬧喧囂,盛況空前。
“詩山公園”始建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距今有85年的歷史。公園內有祖祠、廟堂;有古樹花草、休閑涼亭、錦魚水池、散步廊道;有古老的圖書館、紀念碑;有球場、影院。
離別家鄉好久、好久,每一回返鄉,我走近山山水水,腳踏田園溪邊,親昵樹木花草,漫步房前屋后,虔誠膜拜鳳山古寺,重游古老滄桑的公園,情依依,心纏綿,難以平靜。仿佛回到從前,一切都顯得親和、淳樸、富有詩情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