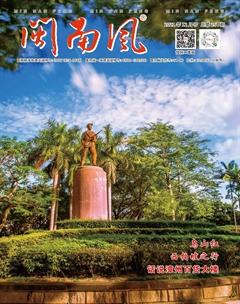史詩般的愛情明鏡
怡霖
“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此為漢代毛蘋的《上邪》樂府民歌,毛蘋為秦漢時期長沙王吳芮的妃子,史上著名才女之一,相傳《上邪》系她所作。從《上邪》的極至忠貞誓言,到曹雪芹所著古典名著《紅樓夢》中賈林的凄美之戀,愛情作為文學主題自始至終在線,是永不消磁的磁鐵石,撼人心魄的“電閃雷鳴”,常演常新,激蕩人心。
近十年,承蒙王蒙先生贈書多部,而《生死戀》是我攜手身旁的最愛,是我艱難謀生的人生讀本。輾轉千山萬水之中,每回開車累了,我常停車于服務區翻讀這本書養神充電,每每多有收益。這部小說集分別有《生死戀》《郵事》《地中海幻想曲》《美麗的帽子》等篇。

《郵事》為非虛構小說,講述作者幾十年來因為領取稿費而與郵政、郵儲打交道的經歷和感受,樸實真切。《地中海幻想曲》與姊妹篇《美麗的帽子》講述小說女主角隋意如是眾人眼中的“人生贏家”,有著顯赫的家世、學歷、榮譽、身份等,卻在談婚論嫁的問題上屢屢觸礁,小說以意識流寫法講述了她登上地中海幻想曲號郵輪后,在雅典的旅行經歷和心理起伏,世道無常,讓人唏噓不已。
最能體現王蒙先生中篇小說集藝術智慧的是這本書中的中篇小說《生死戀》,《生死戀》也是小說集的“壓臺戲”,且是先生84歲高齡時的作品,凝聚著他一生的智慧和心血。
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面旗幟,王蒙先生的小說始終反映著歷史滄桑、社會變遷,飽含著濃濃的家國情懷。而這篇《生死戀》中,先生站在人性的高度書寫愛情,把愛情故事寫得波瀾壯闊、驚心動魄,反映了浩瀚而廣闊的時代變遷,融合了廣博豐富的社會、文學識見,令人嘆為觀止。
《生死戀》體現了對愛情始終保持著飽滿而恒定的興趣。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只要一寫小說,每一個細胞都在跳躍,每一根神經都在抖擻。日本有一種說法叫成長到死。那么小說也可以創造到老,書寫到老,敲擊到老,追求開拓到老。”亦如序言所寫:“王蒙老矣,寫起愛情來仍然出生入死;王老衰乎,寫起戀愛來有自己的觀察體貼。”先生曾任團干部、作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長,訪問過60多個國家和地區,獲得國外兩個名校的名譽博士學位,作品被翻譯為20多種文字,自執筆創始已逾70年,出版過近50卷的文集,作品2000多萬字。從50年代飽含革命激情的青春歌賦激蕩文壇,到70年代的異域風情與時代隱喻,再到80年代的藝術探索與內省哲思,直至90年代的“季節系列”,都在記錄生活與心緒,記錄著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豐富歷程。在詩意與美感的書寫中,見證生命與滄桑,在滄桑之后,又展現出嶄新的活力。《生死戀》是王蒙式的生死戀,精神之戀,是貫穿歷史到現代的中國式愛情的修辭與詠嘆,是借愛情來觀照中國社會進程的史詩樂章。
《生死戀》將文學的古老母題愛情演繹得看似波瀾不驚實則靜水流深,看似稀松平常實則纏綿悱惻。這部“天的構思”之作,是一部有著時間縱深漫長及內部空間宏闊的小說。時間跨度從1898年戊戌變法開始,歷經革命年代、建設時期、改革開放,縱向穿越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空隧道。空間跨度從北京的四合院,直到大洋彼岸的美國。小說以三進的大雜院為原點,講述了蘇家和頓家跌宕起伏的命運及其難分難解的恩怨情緣,既有逆向的對過往迷霧的追溯,又有契合時代潮流的揚帆追遠。
小說雖是中篇的篇幅,卻有著宏大敘事的品質,在這種背景之下,作為主人公的蘇爾葆,從青蔥少年到年逾知天命,他的理想和成長,他的愛情和婚姻,他的堅守和困惑,既帶有普遍性,又有獨特性。由此引發的道德與自由、迷失與覺醒、自我與超我……靈魂上的拷問,是作者在經歷,何嘗又不是讀者在經歷,對他的拷問其實也是對讀者的拷問。這一切都沒能逃脫作者如手術刀般鋒利的剖析、追索,讓我們對主人公經受的苦痛、煎熬、分裂、震蕩感同身受,體驗切膚刻骨,與之一同接受精神上的洗禮,并努力找尋愛情和生命的終極意義之所在。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生死戀》中蘇爾葆首先面對的是來自于單立紅的愛情——蘇爾葆從出生的那一刻就墮入了對自身身份無法指認的尷尬,名義上的父親呂奉德不承認他這個兒子,而生身父親始終沒有浮出水面。這過早釀成了他矛盾、敏感、猶疑的性格。當呂蘇的三口之家遭遇之時,作為紅小兵小隊長的少女單立紅向他伸來了友誼的橄欖枝,蘇爾葆也沒有錯過這根救命稻草,而最終是她幫他撐起了一片遮風擋雨的天空,充當了他的救世主,成了他的幸運女神。由此發展,蘇單的婚姻看似必然,在蘇爾葆這邊卻是被動的,更多是恩情重于愛情。這種婚姻的基石本身就不牢靠,這也為后來蘇爾葆同丘月兒的戀情埋下了伏筆。蘇丘的愛情,如果用世俗的眼光來看,是蘇爾葆經受不住誘惑的出軌,若是從精神的立場來體察,則是對愛情自由的自我覺醒,是主動的,在小說中顯然屬于后者。但這種覺醒也是被動的,丘月兒對他的進攻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長達五年。丘月兒說“無論如何燒灼這么一次,不論付出多少代價……最后成了灰,也是幸福的”。小說中,蘇爾葆果真成了灰,可他是幸福的嗎?至此,丘月兒那些炙熱的話語毫無疑問淪為了謊言,她只不過假借愛情之名來掩飾其對物欲的貪婪。她對愛情的理解更像是做買賣,當蘇爾葆凈身出戶時,她的離開勢所必然。
在同丘月兒的“燒灼”中,蘇爾葆身陷撕裂的痛苦深淵,對傳統道德的背叛與墨守,對愛情自由的追求與妥協,舊我新我的幽閉與破繭……始終有兩股背道而馳的力量在拉扯,在廝殺,誰也無法讓它們化干戈為玉帛。這種撕裂之痛并非主人公獨有,置身現代社會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處在無路可逃的撕裂的進行式中,都處在進退維谷的困境中。撕裂的不單是愛情,還有親情,友情,鄉情……囊括了人類所具有的美好情愫。蘇爾葆沒有勇氣沒有力量走出撕裂的重圍,最終只能按下人生的詠嘆鍵,只有隕落,只有自我毀滅。而蘇爾葆之死不僅僅是對愛情的絕望,當他離婚后丘月兒卻另嫁,倒回單立紅身邊也決無可能,兩個孩子對他的態度同樣冷淡,這時候的他已是走投無路,四面楚歌,更加渴望愛與被愛,從這個意義上說,蘇爾葆是死于孤獨。對生活的絕望,即是對愛的絕望。這也是現代人無法祛除的病灶,社會越來越繁榮,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可人與人越來越隔膜,人的內心越來越孤獨。往蘇爾葆的上一輩探究,他從沒露面的生身父親頓永順,屢犯“作風問題”,卻是拿得起放得下,頓永順說“一個男人不能對好女人轉過臉去。你可以犯殺頭的錯誤,你也不能讓她們失望,而且丟臉……”頓永順患絕癥而死時臉是柔軟的,臉上帶著笑容。小說中的另一個人物頓開茅,幾乎是蘇爾葆的對立面,更是頓永順的對立面。頓開茅從他父親頓永順身上吸取教訓,“躲避著當真的情感,更不要身體與器官的丑陋”,而在他的妻子明光看來,也是“吞吞吐吐、遲遲疑疑”。在情感上,明光比單立紅的殺伐決斷更為果斷,“人有好也有壞,人有施恩也有欠情,但是人應該堅決些”,或許明光才是清醒者。明光對頓開茅的審判,何嘗不是針對蘇爾葆呢。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這是先秦《鄭風·子衿》千古傳唱的愛情詩,是《詩經》眾多情愛詩歌作品中藝術境界較高的一篇,女性大膽表達愛情,對情人刻骨之思,在歷代文學作品中少見,且朗朗上口,韻律和諧悅耳,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樸實的戀情千古傳誦。同樣,《生死戀》從精神層面來抒寫“出生入死”的愛情,既有驚心動魄的故事情節,又融合了波瀾壯闊的時代變遷,既讓我們體會了跨文體的縱橫捭闔的文本力量,又讓我們欣賞到豐富多彩、狂歡式的語言魅力。

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得主李洱曾用“晚騷”來概述王蒙的晚年創作,李洱認為:王蒙先生是中國的“貝多芬”。很多人在學習和模仿貝多芬,但卻永遠達不到,而很多人也在學習和模仿王蒙先生,也是遠遠達不到,遠遠模仿不像,先生說:“我不是非要寫愛情,而是這些愛情讓我寫。”此中可見敏銳的文學智慧。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龔曙光說:“任何一個文學家所寫的東西,其實都是帶有真實性的,這個真實性,如果不是故事本身的真實性,那就是情感經歷的真實性。”
《生死戀》在某種意義上,初看是先生對愛情、生命與死亡的設問與解讀,細讀可知《生死戀》所承載的愛情,已遠遠超越了愛情本身,是透過生死之戀的哀婉而凄美之悲歌,愛恨情愁在小說中波瀾壯闊,行云流水力透紙背;家長里短生老病死,寄托著對世間萬象人生悖論深度的審美思考,而且,小說所體現出來的生命哲學、美學厚度以及當代年輕人對純真愛情的迷惘,特別對當下社會物欲橫流、人心不古的風氣,對愛情觀與人生觀起到了很好的審美導向作用。我們從這篇小說,既可以認識復雜深刻的人性,認清愛情的真實面目,還可以汲取更多為人處世的智慧和營養。
《小說選刊》轉載《生死戀》時在卷首語中有一段話,請允我摘錄幾句作本文的結尾:“有論者認為王蒙先生作為共和國文學的一面鏡子,就像托爾斯泰是俄國的一面鏡子一樣,此論出自十余年前,時過境遷,當王蒙同時代人慢慢淡出文壇,而王蒙新作不斷,其‘鏡子’價值更是越發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