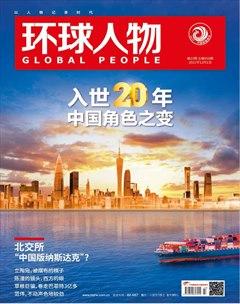鄭律成,在延安彈響曼陀鈴

2021年11月,鄭律成之女鄭小提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李璐璐/攝)
“我是延安娃!”一見(jiàn)面,鄭小提就對(duì)《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shuō),“我在延安出生長(zhǎng)大,那里是我的家鄉(xiāng),也是父親念念不忘的地方。”
鄭律成出生在朝鮮半島的全羅南道光州,當(dāng)時(shí),朝鮮半島已淪為日本殖民地。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長(zhǎng)大的鄭律成,產(chǎn)生了濃烈的抗日情懷。由于中朝兩國(guó)共同的抗日目標(biāo),許多朝鮮愛(ài)國(guó)志士輾轉(zhuǎn)跨過(guò)鴨綠江,來(lái)到中國(guó)參加抗日斗爭(zhēng)。1933年,19歲的鄭律成跟隨一批進(jìn)步的朝鮮青年來(lái)到南京,參加朝鮮人的抗日革命組織“義烈團(tuán)”,開(kāi)始了一邊革命,一邊學(xué)習(xí)音樂(lè)的生活。

鄭律成(1914年—1976年)
背著小提琴去延安
來(lái)到中國(guó)后,鄭律成結(jié)識(shí)了冼星海及“左聯(lián)”的一些革命音樂(lè)家,并加入了抗日救亡組織“五月文藝社”。在參加抗日救亡歌詠運(yùn)動(dòng)的過(guò)程中,他接觸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讀懂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七七事變”之后,在黨中央的號(hào)召下,進(jìn)步青年紛紛奔赴延安。冼星海和他的救亡演劇隊(duì)也離開(kāi)上海,來(lái)到延安。在上海婦女救國(guó)會(huì)負(fù)責(zé)人杜君慧的引導(dǎo)下,鄭律成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
當(dāng)時(shí),鄭律成的俄籍聲樂(lè)老師克里諾娃非常賞識(shí)他,想引薦他去意大利繼續(xù)學(xué)習(xí)聲樂(lè)。經(jīng)過(guò)一番思考后,鄭律成毅然選擇去延安。“因?yàn)閷?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了解,使我父親看到中國(guó)抗日斗爭(zhēng)勝利的希望是在延安,所以他下決心要去延安。”鄭小提說(shuō)。
鄭律成開(kāi)始為奔赴延安做準(zhǔn)備。由于沒(méi)有路費(fèi),在朋友的引薦下,他向民主戰(zhàn)士、民主同盟領(lǐng)導(dǎo)人李公樸求助。李公樸得知鄭律成要去延安,立刻拿出30塊銀元給他當(dāng)路費(fèi)。八路軍總部的高級(jí)參議宣俠父給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寫了一封親筆信,告之鄭律成將去延安一事。就這樣,鄭律成背著小提琴和曼陀鈴,帶著兩本《世界名曲歌集》,和無(wú)數(shù)革命青年一樣,義無(wú)反顧地選擇了抗日救亡之路。
1937年冬天,鄭律成越過(guò)層層封鎖,來(lái)到延安,先后進(jìn)入陜北公學(xué)、魯迅藝術(shù)學(xué)院音樂(lè)系學(xué)習(xí),不久后擔(dān)任抗日軍政大學(xué)音樂(lè)指導(dǎo)、魯迅藝術(shù)學(xué)院聲樂(lè)教員。鄭律成發(fā)現(xiàn)延安雖然生活艱苦,卻生氣勃勃,青年們思想活躍,沒(méi)有森嚴(yán)的等級(jí)差別,而且處處是歌聲,群情激揚(yáng),他感覺(jué)自己來(lái)到了一個(gè)前所未有的新世界,被深深打動(dòng)了。
“那時(shí)候,學(xué)校、單位每天都會(huì)組織大家唱歌,開(kāi)飯前唱歌、開(kāi)會(huì)前唱歌,甚至很多人走路時(shí)也唱。大家唱《義勇軍進(jìn)行曲》《大刀進(jìn)行曲》……這些歌聲給了我父親精神上的振奮,他被充滿革命氣息的延安所感染,他渴望歌頌延安,歌頌革命。”鄭小提說(shuō)。

1939年,鄭律成在抗大女生一隊(duì)指揮唱歌。
1938年4月的一天傍晚,鄭律成和同事爬上延安北門外的一處高坡,放眼望去,只見(jiàn)延河邊上,操練的戰(zhàn)士們喊著整齊嘹亮的口號(hào),在夕陽(yáng)中充滿激情地歌唱。此情此景,讓鄭律成再也無(wú)法按捺心中蓬勃的情感,他對(duì)身邊的魯藝文學(xué)系的莫耶說(shuō):“給我寫首歌詞吧!”莫耶同樣被眼前的景象所感染,當(dāng)即允諾。回去后,莫耶在窯洞里揮筆創(chuàng)作,寫出了激情澎湃的歌詞,鄭律成看了之后非常喜歡,當(dāng)下將自己關(guān)在屋里,經(jīng)過(guò)一天一夜的冥思,很快譜好了曲,《延安頌》就此誕生。
1939年的春天,延安大禮堂里,女高音湯榮枚和男高音鄭律成氣勢(shì)恢宏地唱響《延安頌》:“夕陽(yáng)照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春風(fēng)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jié)成了堅(jiān)固的圍屏。啊延安,你這莊嚴(yán)雄偉的古城,到處傳遍了抗戰(zhàn)的歌聲……”演唱結(jié)束后,毛主席高興地鼓起了掌,很多人激動(dòng)得熱淚盈眶。《延安頌》很快傳遍延安,傳遍蘇區(qū)。

1937年,鄭律成(右)到達(dá)延安。

延安時(shí)期的鄭律成。

鄭律成、丁雪松夫婦合影。
鄭律成在回憶這段創(chuàng)作歷程時(shí)曾說(shuō):“當(dāng)時(shí),延安還很荒涼,山上光禿禿的沒(méi)有樹,生活很艱苦。但是,延安是革命圣地,是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人民的燈塔和希望,人們懷著對(duì)革命的向往從全國(guó)各地來(lái)到這里,又從這里把革命的火種帶到四面八方。延安充滿了朝氣,到處洋溢著熱情和明朗的歌聲……我深深地愛(ài)上這個(gè)朝氣蓬勃、充滿了青春氣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著,想寫支這樣的歌,它應(yīng)當(dāng)是優(yōu)美的、戰(zhàn)斗的、激昂的,以它來(lái)歌頌延安。雖然我當(dāng)時(shí)沒(méi)有專門學(xué)過(guò)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筆創(chuàng)作這首歌。”
在延安,鄭律成還結(jié)識(shí)了詩(shī)人公木(張松如)。當(dāng)時(shí),公木在抗大學(xué)習(xí),并被任命為抗大政治部宣傳科干事。擔(dān)任宣傳科音樂(lè)指導(dǎo)的鄭律成就住在公木的隔壁,經(jīng)常到他的住處玩。公木在延安創(chuàng)作了很多詩(shī)歌,鄭律成看到后,提出為他的詩(shī)歌譜曲。公木聽(tīng)了非常高興,說(shuō):“一首詩(shī)變成一支歌,那確實(shí)是一個(gè)質(zhì)的飛躍。”兩個(gè)人經(jīng)過(guò)商量,決定創(chuàng)作“八路軍大合唱”。于是,在延安的窯洞里,公木思如泉涌,先后寫出了《八路軍軍歌》《八路軍進(jìn)行曲》《騎兵歌》等。鄭律成在窯洞里敲著盆、拍著腿為這些歌詞作曲,他說(shuō):“給詞作曲如虎生翼。我們的虎是吃日本鬼子吃反動(dòng)派的虎,生了翼更兇、更猛、更厲害!”
公木回憶鄭律成的創(chuàng)作過(guò)程時(shí)說(shuō):“沒(méi)有鋼琴,連手風(fēng)琴也沒(méi)有,他只是搖頭晃腦地哼著,打著手勢(shì),有時(shí)還繞著屋當(dāng)中擺的一張白木茬桌子踏步轉(zhuǎn)悠……”
《延安頌》《八路軍進(jìn)行曲》等歌曲從延安飛向全中國(guó),直至海外。許許多多的革命者唱著這些歌,不畏艱難萬(wàn)險(xiǎn),不畏犧牲,在革命的洪流中英勇斗爭(zhēng)。
解放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八路軍進(jìn)行曲》更名為《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進(jìn)行曲》。1988年7月25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經(jīng)黨中央批準(zhǔn),中央軍委決定將《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進(jìn)行曲》定為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軍歌。”
在延安,鄭律成還收獲了愛(ài)情。鄭小提告訴記者,爸爸和媽媽正是在抗大相識(shí)的。丁雪松出生于重慶,是新中國(guó)第一位女大使,20世紀(jì)70年代末先后出使荷蘭和丹麥,歷任中共中央對(duì)外聯(lián)絡(luò)部朝鮮處副處長(zhǎng)、國(guó)務(wù)院外事辦公室秘書長(zhǎng)等職。
1938年,丁雪松來(lái)到延安,進(jìn)入抗日軍政大學(xué)第三期學(xué)習(xí)。她在回憶初識(shí)鄭律成時(shí)說(shuō),一個(gè)傍晚,她和抗大女生隊(duì)的幾個(gè)同志到延安北門外散步,初次見(jiàn)到一個(gè)體形瘦削,腰桿筆挺,眉宇間顯得英俊而剛強(qiáng)。身穿黃色軍大衣的人。他是隊(duì)長(zhǎng)趙玲的客人鄭律成——一個(gè)來(lái)自朝鮮的革命青年。在丁雪松擔(dān)任隊(duì)長(zhǎng)以后,又常常看到鄭律成活躍的身影,他有時(shí)穿著灰色的軍裝,有時(shí)穿件褐色的茄克。當(dāng)鄭律成在晚會(huì)上出現(xiàn)的時(shí)候,他的節(jié)目很獨(dú)特,嘴里吹著口琴(用鐵絲把口琴系在頭上),懷里彈著曼陀鈴,腳下踏著打擊樂(lè)器,一身而三任。丁雪松想這也許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在當(dāng)時(shí)延安這樣簡(jiǎn)樸而熱烈的晚會(huì)上,不正需要這些來(lái)自四面八方、有著各種藝術(shù)才能的青年們‘八仙過(guò)海,各顯神通’,以活躍大家的文娛生活嗎? 有時(shí)他引吭高歌,那宏亮抒情的男高音,具有一種感人的魅力……”
鄭律成在抗大擔(dān)任音樂(lè)指導(dǎo),經(jīng)常到女生隊(duì)教唱歌,和丁雪松漸漸熟悉起來(lái)。他們時(shí)常在一起漫步、聊天,無(wú)話不說(shuō)。有一天晚上,丁雪松回到自己的窯洞,驚訝地看到窗臺(tái)上放著一瓶盛開(kāi)的鮮花,桌上還有兩本小說(shuō)《安娜·卡列尼娜》和《茶花女》,書的扉頁(yè)夾著一張字條:送給小鬼女軍官。署名鄭律成。丁雪松怦然心動(dòng),音樂(lè)、文學(xué)以及共同的理想將二人聯(lián)系在了一起。

鄭小提與父母合影。

新中國(guó)成立后,鄭律成(右一)重返中國(guó),尋找創(chuàng)作素材。
然而,由于鄭律成的國(guó)際身份,多次受到詢問(wèn)和審查。有人勸說(shuō)丁雪松放棄和鄭律成的交往,但她一直堅(jiān)信鄭律成的清白。終于,1941年,在魯藝的一間大平房里,鄭律成和丁雪松舉辦了婚禮。那時(shí)延安的生活非常艱苦,物質(zhì)匱乏,為了辦好婚禮,鄭律成去山里打獵,捕獲了兩頭黃羊。他用其中一頭黃羊和老鄉(xiāng)交換了黃米和紅棗做成年糕,另一頭黃羊則烤成羊肉串,招待客人。在魯藝副院長(zhǎng)周揚(yáng)的主持下,婚禮熱熱鬧鬧地舉行,賓客紛紛前來(lái)祝賀。
一年后,鄭律成和丁雪松的女兒鄭小提出生。營(yíng)養(yǎng)不良的丁雪松沒(méi)有乳汁喂養(yǎng)女兒,鄭律成只得把一直陪伴他的小提琴賣掉,換回一頭帶羊羔的母羊,用羊奶喂養(yǎng)女兒,才算渡過(guò)難關(guān)。為了銘記這段難忘的歲月和那把救命的小提琴,鄭律成和妻子為女兒取名鄭小提。
“我在延安度過(guò)了幼年時(shí)光,當(dāng)時(shí),為克服經(jīng)濟(jì)上的嚴(yán)重困難,黨中央號(hào)召軍民開(kāi)展大生產(chǎn)運(yùn)動(dòng),一部分部隊(duì)開(kāi)始了農(nóng)副業(yè)生產(chǎn),幾乎家家戶戶自己種菜、養(yǎng)豬、做鞋等。”鄭小提說(shuō),“一邊是熱火朝天的勞動(dòng),一邊是嘹亮的歌聲,我是聽(tīng)著魯藝的歌長(zhǎng)大的。”
抗戰(zhàn)勝利后,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發(fā)布第6號(hào)命令,朝鮮義勇軍隨八路軍進(jìn)軍東北,以達(dá)成解放朝鮮的任務(wù)。于是,鄭律成攜帶妻女,離開(kāi)延安向東北進(jìn)發(fā)。鄭小提回憶說(shuō):“一路上,母親牽著一頭毛驢,毛驢載著垛子,一邊垛子里放著生活用品,另一邊裝著我。行軍路上要經(jīng)過(guò)封鎖線,我們小孩子被反復(fù)叮囑不能哭鬧。也許是那時(shí)的環(huán)境影響,過(guò)封鎖線時(shí)真就沒(méi)有小孩子哭。有一次,毛驢爬山時(shí),不小心失蹄了,我差點(diǎn)從垛子掉出來(lái)翻下山去。”
朝鮮半島光復(fù)后,鄭律成又帶著妻女隨300多名朝鮮義勇軍回到朝鮮北部工作。在那里,他參與創(chuàng)建了朝鮮人民軍協(xié)奏團(tuán),并創(chuàng)作了朝鮮人民軍軍歌《朝鮮人民軍進(jìn)行曲》。1950年,鄭律成重返中國(guó)并正式加入中國(guó)國(guó)籍。此后,他的足跡踏遍了中國(guó)大地,到處尋找創(chuàng)作素材,到1976年12月7日病逝,鄭律成留下了300多首膾炙人口的歌曲。
長(zhǎng)大后的鄭小提多次回到延安,參觀過(guò)延安大學(xué)校史陳列館,在圖書館查閱了鄭律成、丁雪松在延安時(shí)期的相關(guān)資料,參觀了王家坪,并在父母住過(guò)、也是她出生的土窯洞前留了影。2018年,人民音樂(lè)家鄭律成生平事跡展在延安橋兒溝革命舊址舉辦,鄭小提在開(kāi)展儀式上分享了自己重回延安的感受。
“父親那一代人的所作所為和革命信仰影響了我,如今傳承著魯藝紅色基因的院校、院團(tuán)、藝術(shù)家也遍布全國(guó)各地。延安是一個(gè)可以讓人們很好地感受和傳承老一輩藝術(shù)家、革命者精神的地方,也提醒著我們,紅色精神一直在。”鄭小提說(shuō)。隨后,她輕聲吟起了《延安頌》。
原名鄭富恩,出生于朝鮮(現(xiàn)韓國(guó))全羅南道光州,1933年來(lái)到中國(guó)參加抗日斗爭(zhēng),1939年加入中國(guó)共產(chǎn)黨,1950年加入中國(guó)國(guó)籍,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被譽(yù)為“軍歌之父”,代表作有《延安頌》《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進(jìn)行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