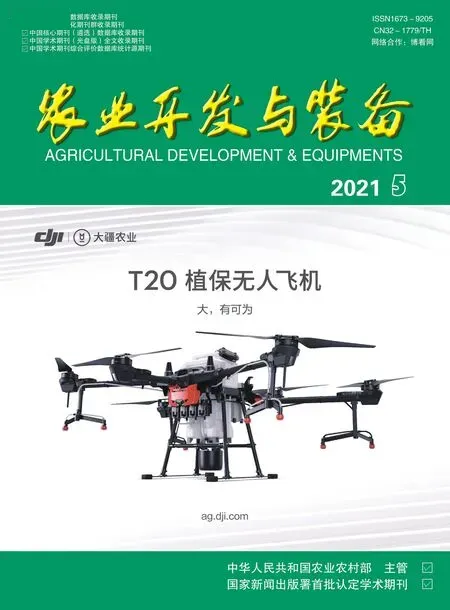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的構建與完善
丁劭泊
(山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山西太原 030024)
1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源于我國20世紀50年代初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是指農民將土地、耕畜和大型農具等生產資料投入集體所有,由集體統一經營管理,村民共同參加勞動,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一般設立在自然村或行政村的范圍內,成員具有特定的人身屬性,與土地和農民的身份有天然的依賴關系,具有明顯的封閉社區的特征。另外,具有企業的經營性質,以營利為目的。因此,與社會團體不同,與行政機關不同,與普通企業不同,有獨特的組織形式和運營機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村范圍內的具體體現。
從性質上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和必要的財產,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具備法人條件,屬于法人組織。然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治理卻存在諸多問題,相關法律制度長期空白,嚴重影響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從十八大到十九大,從“精準扶貧”到“鄉村振興”,國家實施了一系列關于農村的重大改革,其中就包括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為了鞏固脫貧攻堅的偉大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制度亟待建立。相關法律法規需要根據農村的實際情況進行構建,以激發農村經濟的集體活力,使之規范運行并保障農民的集體權益。
2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的問題分析
2.1 法律主體的長期虛設
改革開放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既然是統分結合,就要有統有分,各村應該根據實際情況處理好集體和農戶的關系,不能搞一刀切。然而,大部分農村的實際情況是分散經營發展良好,統一經營被大大削弱了。從全國范圍來看,包括土地等集體生產資料分的多,留的少。根據官方數據統計,全國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農村集體經濟收益在五萬元以下或者沒有收益。這使得村集體的很多事務都難以開展,村容村貌破爛不堪成了普遍現象。沒有了經濟基礎的支撐,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主體身份變得有名無實。連很多本村的村民都不知道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存在,更不用說外人了。然而,在《憲法》《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中都有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規定,這就使得法律主體出現了虛設問題,長期以來被虛化和弱化。
2.2 村黨委、村委會與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混亂
村黨委是黨在農村執政的根基,是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在農村貫徹落實的核心,領導和支持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村委會是在農村范圍內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主要承擔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職能,并輔助鄉鎮、縣級政府完成相應的工作,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帶有行政職能的機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主要負責本村集體資產的經營管理,保值增值和收益分配。三者性質不同,職能不同,不能相互替代。然而,一方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主體長期虛設。相關法律條文作了相互補充的規定,例如《民法典》規定“未設立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村民委員會可以依法代行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其他涉及農村的法律也有類似的規定。另外,農村的人員特殊情況使得很多事情在實際運行中變成了牌子不同,一套人馬。結果就是職責不清,關系混亂。很多村民也搞不清三者的區別,甚至連村委會成員也說不清楚。
2.3 集體成員的權利難以保障
法律主體的長期虛設,部門交叉關系混亂,人員重合職責不清,必然會導致正常的管理活動不能有序進行,難免會損害各方利益。沒有村集體的由村委會代行職能。設立村集體的與村委會又是一套人馬。所以,從實際運行情況來看,有沒有似乎也沒太大差別。更重要的是村委會的職能、組織機構、表決事項及辦法與集體經濟組織不同。村民委員會有明確的法律規范,受其制約。集體經濟組織規范的法人制度尚未出臺。如何保障集體成員的表決、選舉和被選舉、集體資產收益分配、知情、監督、訴訟等重要權利?村委會代行職能該如何監管?村委會與集體經濟組織混同,如何防止內部少數人控制?這些問題都需要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制度。
3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的構建與完善
3.1 明確法律主體地位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備法人的一般特征,符合法人的資格要求。最新施行的《民法典》已經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界定為特別法人,賦予了明確的法律主體地位,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參與市場經營活動。2018年起,縣級以上農業農村管理部門對本行政區域范圍內的各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放登記證,并賦予統一社會信用代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終于有了自己的“身份證”,可以名正言順的開展工作。近年來,農村不斷推進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從確權登記到清產核資再到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集體資產有了明確的界定和歸屬。集體經濟組織的財產得到了充實,集體經濟組織不再虛設,在名義和實質上都有了堅實的基礎。
3.2 法人治理制度的構建
有了明確的身份只是第一步,還需要建立相應的法人治理制度。其中關于部門重疊關系混亂、集體成員權利難以保障等問題,都需要明確解決。有的專家學者認為,既然農村人員關系緊密,部門不同而人員重合的現象普遍存在,不如干脆取消集體經濟組織,不必單獨立法,由村委會代行一切職能,合二為一。既可以減少開支,又可以避免法律與實踐的沖突,把問題簡單化。個人認為并不合適,村委會與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完全不同,一個是以管理和服務為目的,一個是以經營和分配為目的。目的不同過程不同,過程不同結果不同。假設財務收支、組織機構、運行機制等重大問題都混為一談,那么,村委會、村集體和村民各方面的權利都將難以保障。所以,需要建立不同的法人組織加以規范。人員可以重合,職責必須分開。20年11月,農業部發布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示范章程》,以指導各地規范運行。具體表現為各村或組成立相應的經濟合作社或者股份經濟合作社,將集體經營性資產折股量化到本社成員,作為年終收益分配的依據。同時賦予了成員表決、選舉和被選舉等一系列重要權利,并成立三會組織確保其正常運行。目前,國家正在加緊制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以建立一套完整的法人治理制度,對成員的身份確認、相互的權責劃分、組織登記和機構運行、資產財務管理、法律責任、監管防范制度等作出全面的規定。
3.3 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長期以來,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規定散見于多部法律。在《憲法》《民法典》《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和《村委會組織法》中都有體現,這就客觀上造成了很多事項的依法不明。尤其是土地發包、集體資產經營管理等重大事項,村集體可以管,村委會也可以管,到底誰來管。沒有村集體的,村委會可以代行,那有村集體的,村委會可以干預嗎?兩者的地位是否平等,是否存在隸屬關系?在實際工作中,村委會插手干預的現象比較普遍,內部一言堂和小團體控制的問題很多,村集體和成員的利益經常被侵害。個人認為兩者是獨立的法人組織,不存在上下級關系。相關法律法規應當及時修訂完善。特別是《村委會組織法》和正在制定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都應當加以明確。建立相應的監督和預防機制,確保兩者的規范運行,促進集體經濟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