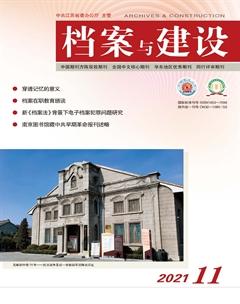解放記憶
吳麗霞 邱北海
今年年初,筆者有幸獲得一本日記,名為《政治學筆記》,作者為夏英倫。根據散佚史料記錄,夏英倫解放前在南京某鐵路學校實習,1948年12月分配至常州戚墅堰火車站,1949年下半年考入浙江大學,1953年畢業后分配到浙江某地區農業研究所,再后來調入南京。日記記載時間從1948年8月開始,至1949年6月結束,時間跨度為解放戰爭前后。本文以此日記為依據,依照時間順序,從主人公視角還原那段真實的歷史。
一、國民黨統治后期通貨膨脹,人民生活維艱
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國民政府軍費急劇增加,引發財政赤字直線上升。為支付軍費,國民政府大量印制法幣,導致物價瘋狂上漲,國統區社會經濟面臨崩潰。1948年通貨膨脹達惡性時期,為挽救其財政危機,維持日益擴大的軍費開支,國民政府決定廢棄法幣,改發金圓券。1948年 8月19日,金圓券正式發行,直至1949年7月才停止流通。
金圓券對人民生活的真實影響,從夏的日記內容可見一斑。他在1948年8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自全國幣發行以來,在外表上物價可以說是穩定了一些,然而內里還仍舊上漲啊!但這次幣制改革,決不是兒戲,直接影響現實政府的存亡,戰亂軍事的勝負……看看皮鞋的標價,普通的七八元一雙,最便宜的五元。聽說最好的有六十五元一雙,這太奢侈了……”當時市街上雖然商品并不十分短缺,但因通貨膨脹,普通民眾無力購買。夏英倫的日記說明,金圓券的推行并未帶來實質改變,百姓物質生活依舊極度匱乏,舉步維艱。
面對空前動亂的大時代,夏感到渺小與無奈。他在12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好些日子未看報,真的沒有看頭,世界的情勢,內戰的戰況,總是那樣死不死、活不活的令人煩愁。……這樣生活已覺痛苦了,但想到遭受戰爭迫害的難民,有了飯,吃飽肚子,已經足夠幸福了。”他的想法反映了當時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心理狀態,可以看出時人對未來生活的迷惘,對眼下生活境遇的不滿。
二、戚墅堰站過新年,炮火彌漫到長江一帶
1948年12月26日,夏英倫前往南京下關京錫運輸段報到。28日,乘十一時列車,前往分配地戚墅堰報到。29日,暫被派與同事學習售票。
戚墅堰站始建于1908年4月,隸屬于滬寧鐵路管理局(即上海鐵路局前身)。該站民國時期有到發線3股,其他線2股。戚墅堰站靠近京杭大運河,夏英倫每天到飯館里吃飯,都要經過運河邊岸。運河岸邊的景致雖美,但隨著戰火的蔓延,人們已沒有太多的心情去觀賞。
因為工作原因,夏英倫1949年農歷新年是在戚墅堰站度過的。在1月29日(即正月初一)的日記中,他寫道:“今天的世界,今日的中國,都處在紛亂和戰爭的恐怖中……如今內戰正酣,民窮財困,生靈涂炭……炮火的彌漫,已經及至長江邊而到京滬一帶了……”
2月2日(正月初五)的日記記載道:“憑窗覽眺,外面小溪一畔,站著幾個黃衣的軍人和一些面帶新年愉快而身著新衣的老百姓,忽然溪里傳出了爆炸聲,溪水升起而四濺,原來那幾個兵士在擲手榴彈,以為游戲,看他們的情形是愉快的,好像時局已經和平了,所以也不惜乎此彈……”
日記中的文字流露出一個普通百姓樸素的祈求和平的愿望,而其中國民黨兵士往溪水中擲手榴彈的情節似乎也是國民黨政權即將敗北的真實寫照。早在夏英倫1948年12月25日的日記就已見端倪:“晚間約十一時,永興路我們宿舍里,來了許多南京國防部撤退的官員,我們業已入睡了,后開門開燈讓他們進來……”當時,淮海戰役就基本見到分曉,國民黨軍大勢已去,南京市政府于12月10日發布《關于疏散職員眷屬之訓令》,大量國民黨軍開始著手撤退。
三、親歷常州解放,戰后鐵路恢復
1949年4月22日,夏英倫在日記中寫道:“駛往上海的列車,車頂上、車廂內堆滿了逃難客,其中服裝狼藉的兵士也不少,一輛一輛駛過去,其密度之驟增,令人想到時局緊張的程度。炮聲轟轟的傳來,時而夾著斷續的微弱的機槍聲,那服裝狼藉、意志頹喪的兵士,稀疏零落的向我們車站集中。”
“午餐以后,來到房間中作一小歇……耳聽得外面一聲槍響,接著有機槍聲,先不以為然,一會兒連著炮聲不斷響起來……知道交兵之地就在面前,看到這種情形一切不顧的拔腳就跑,一口氣跑到運河邊上……跑近運河邊的時候,就移進一幢茅屋中去,承蒙茅屋中的女主人給一束稻草使我躺在地下……停了約一小時的功夫就和解放軍見面了,這是我(們)第一次的相逢。”
與他日記內容相對應的是,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華東警備6旅作戰科科長周時敏回憶:1949年4月23日,該旅隨23軍連夜渡江。部隊在南岸魏村、圩塘、桃花庵一帶登陸,星夜兼程至龍虎塘,天已拂曉。沿途國民黨軍不斷空襲。解放軍整隊輕裝,組織入城,浩浩蕩蕩由東西北方向開進常州城,16團在城東北,團部在天寧寺,17團在常州方暉女子中學,并以一部乘火車去戚墅堰機車車輛廠警戒防空。常州終于獲得解放。
據《常州交通志》記載,4月23日常州解放后,5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常州軍事管制委員會生建處船舶管理處成立,5月13日常州軍事管制委員會生建處汽車管理處成立,之后各路交通逐漸恢復。夏英倫的日記也印證了這點。1949年5月16日他寫下這樣一段文字:“今晚開始通車,從上月二十三終斷,迄今已二十三天了……今晚是值得記憶的一宵,是我們鐵路解放后第一次通車……我們要迎接新的事業和新的光明……”根據夏的描述,說明在解放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常州鐵路業便得以恢復,解放如同賦予新生命一般,給鐵路工人們帶來了新的曙光。
四、乘坐勝利號去上海,新生活的開啟
戚墅堰機車車輛廠地處常州市戚墅堰區,前身是清光緒年間興建的吳淞機廠。自建成起至20世紀20年代,逐步發展為滬、寧、杭鐵路工人最集中的大廠和上海地區鐵路工人運動的中心。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被日軍占領,廠房設備遭到嚴重破壞,后于1936年從上海遷入常州戚墅堰。1949年2月,戚機廠工人發動了“反饑餓,求生存”的二月大罷工,這是常州歷史上重要的工人運動,一度中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交通命脈京滬、京杭兩線,鼓舞了人民群眾與敵人作斗爭的信心。此外在內戰時期,戚機廠建立地下黨組織積極配合中共工作。上海于1949年5月27日解放,戚機廠踴躍舉行文娛活動赴上海慶祝。夏英倫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段歷史。
6月1日記載:“(戚機廠人員)上午十時乘著由戚墅堰機廠開出的勝利號到上海去,勝利號的車身別有一番裝潢,機車上掛著用紅綢和柏枝編成的彩繩,頭下面又有一個大紅星,紅星的中央掛著毛主席的肖像,紅星上端以及煤水車的兩邊,都寫著很大的‘勝利號’幾個字……我是坐在守車里的。”此處的“紅星”與“毛主席肖像”成為鮮明的時代印記,象征了人民群眾對毛主席的愛戴,也象征了共產黨權威的樹立。解放后,南京、常州、上海等地為維持社會秩序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以布告的形式發出政令,對文教、新聞、廣播、出版等事業單位,以及官僚資本的經濟機構和工廠企業進行全面接管,迅速著手恢復社會秩序,穩定人心。夏英倫跟車抵達上海后,“在北站替班宿舍借宿一宵,一大早就起身上街,買了一些東西,上海市繁華如舊,蘇州河的一段橋上還停留一輛綠灰色的坦克炮車,許多大馬路中心還有巷戰用的土碉堡,樣子煞是狼狽,但是經常來往的行人也不覺得稀奇”。可以看出,雖然內戰剛剛結束,不免留下戰爭痕跡,但是社會秩序還算良好。
6月2日記載:“十二時一刻即乘車離滬……窗外的風景一幅幅流過,都極美麗……車子順一條澄清的小河向前跑,清幽的河水可以見底,浮在上面的木船……油漆過的船板放著沒有一絲微塵,穿著淺藍老布的船女,光著腳露著小腿,柔軟地在船面上走動,撐著槁子,兩只健康膚色的膀子,多么有力而又多么美麗,這樣的鏡頭真太美了。這種‘美’完全建立在清潔、樸素的自然生活上。”行文歡暢淋漓,夏英倫對新生活的美好向往與憧憬躍然紙上。
五、結語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是歷史事件的親歷者、見證者和書寫者。薄薄的一本日記記載了夏英倫的所見所聞,豐富了時代記憶庫,成為常州解放前后這段歷史最直接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