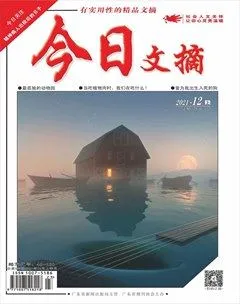縹緲的“最高價值”

在舊金山,友人甲前幾年買了一棟建于20世紀40年代的房子,因太老舊,雇請工人,耗時一年多,里外來個徹底翻修,終于大體完工,甲一家遷入。接下來,一些零碎活要完成,如給新安裝的柜子門安把手,在浴室安裝掛浴巾的鉤子,在書房裝書架。甲請來乙干。我去參觀時,聽到甲和乙的對話,話題是房子的地下。房子的地下前半部分是車庫,后半部分是一個小單位。這小單位從前就有,年久殘破,樓上裝修時捎帶把它拆掉了。眼前一片凌亂,墻上布滿洞,地上堆滿雜物,洗手間的天花板塌了。
“修好它,無論自住還是出租都不錯。”乙惋惜地說。
“光是裝修樓上就把我累死,花錢似流水,也沒工夫心疼。”甲說。
“這地方,如果全交我處理就好了。”乙邊說邊搓著因常年操勞而粗糙無比的大手,邊發出嘖嘖的感嘆,“我家上至太太下至孫輩,都反對我上班。我不是沒錢,不敢退休是因為缺這個……”乙指著這亂七八糟的空間,“技癢難耐”的表情一如餓漢面對滿桌美食。
隨后,乙扳著手指頭,把心底的“藍圖”略做交代:哪里建開放式廚房,哪里安落地窗,如何改造嫌矮的天花板……滿臉倦容的甲被乙鼓起了勁,兩人一本正經談論樓下的工程。
我認識乙多年,明白他的個性。他出生于貧困山區,從前在村中務農,后來在車衣廠操控裁床,出國后當建筑工。他不愛旅游,不煙不酒,唯一的嗜好是干活,能讓他獲得存在感、成就感的只有工地,老板從餐館買來的盒飯最對胃口。可惜不知不覺就老了,小病一個接一個。一次他從高處摔下,在家養傷三個月。他好一點后,一拐一拐地在家小修小補。兒女勸他他不聽,只好把他的工具箱鎖起來。
我明白乙的心事,于他,為晚年所作的完美設計,是一個“有活可干”的空間。哲人謂,體現“生命最高價值”的空間和時間具有相同的特點,那就是:未被占據。這樣的空間,讓你按自己的喜好布置;這樣的時間,讓你自由自在地休閑。然而,如果僅及于此,尚嫌空疏。一如你手拿可隨意消費的巨額鈔票,馬上面對“買什么”的問題。
遺憾的是,為數不少的老人拿到這輩子唯一可實現“最高價值”的空間和時間后,竟手足無措。早上起來,早餐吃過,心里一片茫然,自問:要干點什么才熬到天黑?這時,老人們才驚覺,再也沒有家庭和經濟負累的晚年,擺平“無聊”是何等緊迫的大事。這問題,對善于品味生活的優雅者不存在,一本好書,一闋音樂,一壺清茶,清風明月,妙趣無窮。可惜,我們往往一輩子只習慣一個生活方式——上班。當生活賦予人近乎完整的自由,人生反而變為失去壓艙石的小船,無目標,無支撐,只好以生閑氣消磨光陰。
從這個角度看,如果讓乙選擇——一棟設備嶄新、齊全,拎包即可入住的房子;一棟百廢待舉的破房——他會二話不說就拿走后者。同是修房子,上班只為飯碗,束縛諸多,如今變為純粹的消遣,用什么材料,怎么做,做多久,他是獨立王國里至高的王。他要盡量放緩進度,以一錘一鋸重新建構一個全部由自己主宰的“人生”,身體與靈魂在工具的交響樂里達致圓融的和諧。
和乙告別以后,我的視覺出現奇異的變化——從街旁因拆遷而留下的瓦礫、雕塑家工作室的石頭,到家里打印機里的白紙,都與縹緲的“最高價值”有關聯。
(楊紫凝薦自《義烏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