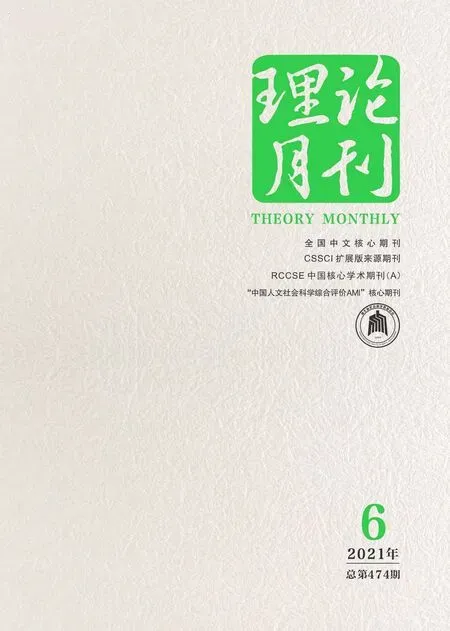正義與德性
——荀子政治哲學新探
□ 張 新
(1.復旦大學 哲學學院,上海200433;2.杜克大學 哲學系,美國 達勒姆27708)
一、問題的提出
基于各個國家以及全球范圍內人們在基本善(primary goods)(包括財富、機會、權利、尊嚴、職業、社會地位等)的享有上存在著巨大差距,正義問題日益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與難點①本文所說的“基本善”包括“物質善”與“社會善”。除此之外,“基本善”還包括自尊的社會基礎與個人能力發展等內容。。然而,在當下關于正義理論的學術探討中,基于西方傳統的正義觀念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正義的理念》一書中指出:當代政治哲學關于正義問題的討論,因其關注點僅僅停留在西方著述中,故而有著局限性乃至狹隘性;事實上,諸如正義、公平等緊密關聯的理念在世界上許多不同的地方都為人們所追尋,但這些理念在全球范圍內存在這一事實卻因當代西方話語的主導性傳統而被忽視或邊緣化[1(]xiv)。與此相應,早在1997年陳迅武即明言,儒家思想遭到了當今西方正義話語參與者的輕蔑式拒絕[2]。
平心而論,非西方哲學傳統中的正義思想被有意或無意地邊緣化乃至于無視,并不利于對正義問題的真正追問。如果將對于正義問題的探索局限于西方傳統,便會錯失解決正義問題的可能線索[1](xv)。而將儒家思想在當代正義話語中排除,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2]。也許正是基于這一原因,儒家的正義觀逐漸得到了英語世界學者的關注①本文的“英語世界”是在較為寬泛的意義上使用的,主要指以英文為表達語言而呈現出的學術世界。,近年來更是出現了關于儒家正義觀的系統性詮釋與體系化表達②相關的綜述性與評論性文章,參見Erin M.Cline,“Justice and Confucianism”,Philosophy Compass,2014,9(3),pp.165—175;Tim Murphy and Ralph Weber,“Ideas of Justice and Reconstructions of Confucian Justice”,Asian Philosophy,2016,26(2),pp.99—118;黃勇:《儒家政治哲學的若干前沿問題》,譚延庚譯,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需要指出的是,就國內學界而言,黃玉順先生基于對周公、孔子、孟子與荀子思想的現代性詮釋,從而構建了“中國正義論”。參見黃玉順:《中國正義論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倫理學傳統》,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
英語世界關于儒家正義觀的學術探索對于扭轉儒學在正義問題上所處的邊緣性地位具有重要的糾偏作用,亦為正義問題的追尋提供了一個大有裨益的、非西方傳統的思考視角。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英語世界的學者在闡述儒家正義觀時雖不乏對荀子思想的片段式借鑒,卻少有對荀子正義觀的個案性與專門性研究。這一學術現狀一方面與英語世界中的荀學熱極不相稱,另一方面也遮蔽了荀子在儒家正義問題上相較于孔孟而言的獨特性貢獻。本文的目的即是結合英語世界與中文學界關于荀子思想的相關研究,試圖厘清荀子政治哲學的內在理路,以辨明荀子在儒家正義觀上所作出的創造性推進及其當代啟示。
二、性惡論與荀子式自然狀態
裴文睿(R.P.Peerenboom)指出,孔子思想中不具備現代正義觀并不令人驚訝,而真正令人驚訝的是在孔子的詞典中竟然找不到一個詞與“jus?tice”相匹配;但他緊接著指出,由于荀子持有一種人性自利觀,故其十分關注稀缺的社會善(social goods)的適當分配,“justice”很可能是對《荀子》中“義”的最恰當的翻譯,而接下來的問題自然演變為荀子與孔子在哲學主張上的差異所在[3]。荀子相較于孔孟而言最突出的特點即是其性惡論的主張。事實上,學界對于荀子性惡論的研究存在著三種十分不同的解釋角度,即本體論或形而上學的視角、倫理學或道德哲學的視角以及政治哲學的視角。雖然這三種解釋視角并非截然不同而是深度關聯的,但無疑第三種視角更能切中荀子主張性惡論的真實意圖。荀子之所以從政治哲學的視角出發對性惡論進行剖析,主要是將其看作由“偏險悖亂”之惡政向“正理平治”之善治轉變的理論起點。
如果說司馬遷所謂的“言治亂之事”[4](p2851)是稷下諸子著書立說的思想關切所在,那么,分析影響政治—社會運行機制的治亂因素便成為荀子思考的首要對象,正所謂“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富國》)③以下凡引《荀子》,皆只注明篇名。。根據楊伯峻的統計,“治”“亂”在《論語》中分別出現6次與15次[5(]p251,282),在《孟子》中分別出現44次與18次[6(]p370,418)。而根據筆者的統計,“治”“亂”在《荀子》中出現的次數分別高達253次與231次,其中“治”“亂”二字連言就出現了17次。在荀子看來,導致政治—社會失序的基礎性因素就是“性惡”。梁啟超認為,《性惡》篇“為荀子哲學之出發點,最當精讀”[7(]p935)。事實上,由于受到《正名》篇中“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這句話的影響,荀子思想中的性、情、欲等概念往往被視為同一個東西的三個名稱[8(]p205)。然而,需要辨明的是,荀子在《性惡》篇中闡明“人之性惡”時依次提到了“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惡”“生而有耳目之欲”。根據荀子的言說脈絡,“生而有好利”所描述的是人先天的逐利傾向,“生而有疾惡”指向人的自然情感,而“生而有耳目之欲”指向人的感官欲望。耳、目、鼻、口、心等感官所欲求的對象即“芻豢”“文繡”“輿馬”“余財蓄積”(《榮辱》)等滿足官能欲望的物質善(material goods)。另外,荀子認為,人所追逐的核心利益還包括權勢、爵位、官職、土地等社會善,對于社會善的追逐實際上為上述“生而有好利”的先天逐利傾向所涵蓋。對于物質善與社會善的無節制的追逐必然引起爭亂狀態,關于這一點學界多有精彩的闡發,無須贅言[9]。
然而,在荀子看來,生而即有的自然情感如“疾惡”等亦可以獨自地引發爭亂狀態。楊倞在注“疾惡”時指出:“疾與嫉同。”[10(]p513)根據楊倞的注解,“疾惡”可以被理解為“嫉妒”與“憎惡”。樓宇烈在《荀子新注》中將“疾惡”注釋為“忌妒,憎恨”[11(]p474),即是采用了楊倞的看法。英語世界中的四個《荀子》譯本中的三個,即德效騫(Homer Dubs)本[12(]p301)、華茲生(Burton Watson)本[13(]p157)、諾布洛克(John Knoblock)本[14(]p151)均采用了楊倞的看法。與 此 不 同 ,王 天 海[7(]p936)、熊 公 哲[15](p542)、董 志 安等[16(]p1224)則將“疾惡”理解為“憎惡”“厭惡”①需要指出的是,董志安認為“疾惡”與“好利”皆為動賓短語,故“疾”讀本字即可而不必假借“嫉”。。何艾克(Eric Hutton)的《荀子》譯本與這一理解相一致[17(]p248)。如果不拘泥于訓詁學上的考察,這兩種不同的注解其實是可以兼容的,前者涵蓋“嫉妒”與“憎惡”兩義,但相較于后者更突出了嫉妒這一負面的自然情感;后者雖然只具備“憎惡”義,但“嫉妒”可以看成是“憎惡”的具體表現形式。
事實上,荀子對于人的自然情感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有著清晰的認識與深刻的考察,例如《榮辱》《正論》《儒效》等篇對于人所具備的榮辱感及其引起的爭斗的辨析,《禮論》篇對于“吉兇憂愉之情”的闡發,《正名》篇對于“好、惡、喜、怒、哀、樂”之情的研判。蔡仁厚在闡發荀子言性的內容時將其分為“感官的本能”“生理的欲望”與“心理的反應”,并在“心理的反應”中點明了自然情感這一內容[18(]p389)。與此略有不同,柯雄文(Antonio S.Cua)將性惡的內容分為“欲望”與“情感”兩部分,相較而言著重突出了情感這一維度[19(]p7-8)。總之,荀子認為,這些自然情感在生活世界中的無序化的、無節制的、沖動式的表達必然引起爭亂狀態,正所謂“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樂論》)。
不過,在諸多自然情感中,荀子的確對于“嫉妒”之情格外關注,《不茍》《仲尼》《王霸》《臣道》《成相》《大略》《堯問》諸篇皆論及嫉妒這一負面情感,其主要指向因嫉賢妒能而產生的相互猜忌、排斥與傾軋,如“妒嫉怨誹以傾覆人”(《不茍》)、“爭寵嫉賢利惡忌;妒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成相》)。這一方面說明嫉妒這一情感及其引發的政治惡果已經成為荀子所處時代的普遍現象,另一方面表明荀子充分意識到了嫉妒對于理想的政治秩序所具備的破壞性與瓦解性。聯系到荀子對于賢能治理的推崇,可見嫉賢妒能在政治實踐中所產生的實際危害是難以估量的。荀子明言“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賢者謂之妒,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薉孽也”(《大略》),并以“飛廉知政任惡來”說明“世之災”在于“妒賢能”(《成相》)。而桀紂等“暗主”的滅亡正是其“妒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臣道》)的結果。這里之所以強調自然情感在荀子分析社會治亂問題時的相對獨立性,一方面在于因嫉妒與榮辱等情感所引發的爭亂固然可以指向對物質善與社會善的爭奪,但更是涉及個人能力、尊嚴的相互比較與社會認可問題;另一方面在于自然情感會像化學催化劑一樣加速人類對于物質善與社會善的激烈爭奪,從而產生無限爭亂的“惡循環”局面。
可見,雖然可以籠統地說,在荀子看來欲望是引起爭亂的基礎性因素,但荀子在《性惡》篇的論述中還是對人的好利傾向、自然情感與感官欲望作了相應的區分。上述關于政治—社會陷入爭亂狀態的因素的分析主要立足于人的主觀條件,而荀子有關導致爭亂的客觀環境的剖析亦相當精當。
如果人類生存的客觀環境在上述物質善、社會善以及個人能力發展、自尊的社會基礎等基本善上是極度富足的,那么即使人類先天地欲求這些東西,依然不會導致爭、亂、窮的生存境況。因為客觀環境的極度富足決定了每一個體都可以獲得最大限度的滿足。故而,荀子在《性惡》篇中并沒有呈現其政治哲學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前提,即荀子在《榮辱》《王制》與《富國》諸篇中論述的“物寡”“物不能澹”的問題。荀子認為,人類生存的真實的客觀環境在基本善上存在著稀缺,而這構成了人類爭亂的客觀條件,即“物不能澹則必爭”。主觀方面的欲望之無窮與客觀環境在基本善上的匱乏構成了荀子式自然狀態的一個基本矛盾,亦是荀子政治哲學的出發點[20]。然而,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荀子所謂的“物寡”“物不能澹”究竟是何種程度上的匱乏。畢竟,荀子強烈批評墨子“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實乃“墨子之私憂過計”,而“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富國》)。荀子認為,墨子之所以主張“節用”“非樂”,在于其認為人類的生存資源是極端匱乏的,故而在生活上主張“衣褐帶索,嚽菽飲水”,在政制安排上倡導“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富國》)。從荀子對墨子的批評來看,“物寡”絕非生存資源的極端匱乏,故而不必像墨家那樣忍受生活上的貧苦與政治建制上的簡約與均等①需要指出的是,《富國》篇中關于“物寡”“不足”的論述分別屬于不同的言說脈絡,前者是為了論證“分”的必然性,后者主要是批評墨子的政治方案。。因此,荀子所謂的“物寡”只能是一種中等程度的或者適度的匱乏(moderate scarcity)。
羅思文(Henry Rosemont)曾指出,“欲多而物寡”反映了古代中國嚴酷的氣象、地形與土壤環境,這構成了荀子思考問題的限制性的客觀環境,并認為“斯巴達式原則”適用于中國[21(]p1-38)。仔細審視羅思文的觀點,則會發現其對中國生存環境的定位是基于中西比較的視野,而非從荀子思想的內在理路出發。這亦決定了其對“物寡”的理解更接近生存資源的極端匱乏狀態,而沒有有效切中荀子思想的實情。荀子之所以認為客觀環境所具備的生存資源是一種中等程度的匱乏,是因為其看到了人類群體合作的必然性及因合作而帶來的滿足社會生活需要的基本善的增益。如果說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是因自保而引發的每一個人反對每一個人的戰爭,那么荀子的自然狀態則不僅僅有著個體之間的利益爭奪,而且有著因共同利益的存在而產生的群體合作。原因在于,荀子式的自然狀態并不像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那樣預設了離群索居的原子化的個體。“能群”“善群”既是人的本質規定,“人生不能無群”(《王制》)、“離居不相待則窮”(《富國》),又是人區別于動物的特質所在,“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王制》)。
在荀子看來,離群索居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走向困窮,而人類之間的群體合作則能使每個人過上更好的生活。這是因為,人類之間的合作會極大地改善衣食住行等社會生活條件,“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王制》),進而帶來基本善在整體意義上增加,即“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王制》)。然而,問題的關鍵是,人類因共同利益而合作,但由于“人之性惡”,故每個人都想從因合作而增加的共同利益中取得更大的份額,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因此,在人類相互合作的過程中又存在著內在的沖突,這就是荀子所說的“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王制》)。因此,荀子式的自然狀態便存在兩個深度關涉的維度,即“欲多而物寡則爭”與“群而無分則爭”②趙汀陽先生認為,荀子的自然狀態理論優于霍布斯的,原因在于荀子主張初始沖突是在初始合作之后由于分配不當才產生的,這可能是沖突的更深刻的原因。參見趙汀陽:《荀子的初始狀態理論》,載《社會科學戰線》,2007年第5期。。前者可謂是人類沖突的基礎性、根本性的因素,而后者表明因合作而產生的共同利益的不合理的分配同樣會導致爭亂狀態。綜上可知,荀子將導致群體爭亂的因素歸結為三點:(1)主觀欲望之無窮;(2)客觀生存資源的中等程度匱乏;(3)因群體合作而產生的共同利益的不合理分配。
三、“分義”及其正義內涵
從邏輯上講,找到了導致爭亂的具體因素,對應的藥方必然從克服這些因素入手。就主觀欲望而言,如果說欲望之無窮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爭亂,那么合理的解決方案便可能是“寡欲”“去欲”乃至于“無欲”。然而,荀子堅決反對“寡欲”與“無欲”,認為“欲”之有無、多寡實乃“異類”(《正名》),而非治亂所系,其主張則是“養欲”“導欲”與“節欲”。因此,群體秩序由“亂”轉“治”的重點便落腳于克服后面兩種因素,即找到合理的群體合作與分配方式,使基本善與人之欲求在相互增益的過程中維持一種相對均衡的狀態。荀子指出:“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禮論》)荀子所給出的方案是實行禮義,而其核心則是“分”。“明分使群”“明分達治”是荀子政治哲學的基本思路,故而儲昭華指出,“明分”是貫穿于荀子整個思想體系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論[22(]p137-139)。
事實上,對于“分”的強調并不是荀子分析政治運行機制的思想特質。佐藤將之指出,“分”是稷下學者尤其是慎到分析治亂問題的核心概念之一,而荀子對于“分”的彰顯是受了稷下學者的影響[23(]p133-138)①另外,東方朔(林宏星)先生從不同的角度剖析了荀子與慎到思想之異同。參見東方朔:《“有治人”與“無治法”——荀子論權威與秩序的實現》,載《中國哲學與文化》,2019年第17輯。。 荀子超越稷下學者之處與其對儒家哲學的創造性貢獻,在于他將“分”與“義”進行結合,并提出了“分義”這一概念。荀子指出: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王制》)
這段引文對于理解荀子的整個思想脈絡十分重要,原因在于其指明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兩種特質“義”與“群”,并認為人之所以能夠“群”的依據在于“分”與“義”。然而,漢語學界的諸家注本對于引文中的“義”解釋甚少,楊倞將“義”理解為“裁斷”[10(]p194),熊公哲直接以“禮”來解釋“義”[15(]p182-183)。而中文學界對于這段文本中“義”的解釋往往是依據人的另一特質“辨”來求其確解。例如,韋政通認為:“荀子以‘義’‘辨’互用,又以‘分’‘義’連稱者,這不是矛盾,亦非觀念之混淆,而正表示義、辨、分都同是代表禮的作用,都同是要盡外王之治的。作用與目的既相同,所以位置可以互換,亦可互為其根。”[24(]p38)韋政通的解釋是將“分”“義”“辨”相并列,從而認為其可以互換、互釋。然而,盡管這三個概念在荀子的思想世界中是相通的,但韋政通的解釋并不符合上述引文的論證邏輯。荀子是將“義”看作“分”的根據與基礎,而并非在并列與等同的意義上使用這二者。陳大齊即指出:“欲分不亂,必須依義以為分別。”[25(]p149)那么,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理解荀子所說的“義”。如果將“義”與“辨”結合起來加以理解,則“義”可被理解為理性的區別、裁斷能力,但正如佐藤將之所說,“‘辨’并沒有‘分配’的意涵”[23(]p338),故而此種理解容易遮蔽“分”與“義”之間的深度關聯;而如果將“義”與“分”結合起來加以理解,則“義”可以被詮釋為“群分”的規范性基礎②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將說明“義”“辨”是如何結合在一起的,這里不具體展開。。
有意思的是,英語世界中的《荀子》譯本及其研究一直對“義”保持著敏銳而審慎的分析。總而言之,《荀子》譯本在翻譯“義”時使用了不同的對應詞,如正義(justice)、公正(righteousness)、義務(duty)、權利(rights)、原則(principle)等。更為重要的是,即便是同一個譯者,在翻譯“義”時亦使用了不同的詞匯。這固然折射出中西文化在核心概念的使用上所存在的差異性,但亦反映出“義”在語言用法上的多義性。這里并非是為了尋找關于“義”的最佳翻譯,而是通過《荀子》譯本所反映出的“義”的內涵的多樣性,更好地審視荀子“義”觀念在現代世界中所具有的政治哲學意涵。英語世界通用的諾布洛克本即是以“正義”(justice)為基準來對譯上述引文中的“義”的,顯然是認為“義”與“正義”存在更多的一致性;《荀子》的第一個英譯本(德效騫本)在翻譯“義”時也主要采用了“正義”一詞①需要指出的是,荀子是在人與水火、草木、禽獸的實質區別中來論述人的特質“義”的。所以德效騫與諾布洛克將“義”理解為人“生而即有”的特質,分別將其翻譯為“權利感”(sense of human rights)與“道德和正義感”(sense of morality and justice)。德效騫將此處的“義”翻譯為“權利感”依然是以“justice”為基準的,這與他將《荀子》中的“義”大多翻譯為“justice”是一致的。但德效騫與諾布洛克的翻譯引發了英語世界關于荀子人性理論是否具有一致性的討論,何艾克先生基于此一問題給出了富有啟發性的闡發。參見Eric Hutton,“Does Xunzi Have a Consistent Theory of Human Nature?”,in T.C.ClineⅢand P.J.Ivanhoe(eds.),Virtue,Nature 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2000,pp.220-236.。
德效騫與諾布洛克之所以能夠用“正義”來翻譯《荀子》中的“義”,主要原因在于,荀子明確地將“分”與“義”掛鉤并創造性地提出了“分義”這一概念,而“分義”所指向的是具有規范性的分配模式。盡管德效騫與諾布洛克知道“義”與英語中的“正義”不存在嚴格的等同性,但他們亦明確認識到“義”與“正義”一詞在具體內涵上的可對應性②黃玉順先生用“非等同性”與“可對應性”來處理荀子“義”觀念與“justice”之間的差別與聯系。參見黃玉順:《中國正義論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倫理學傳統》,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321頁。。正如前述裴文睿所說,由于荀子十分關注稀缺的社會善的適當分配,“正義”很可能是對《荀子》中的“義”的最恰當翻譯[3]。而荀子之所以提出“分義”這一概念,是要在描述性的“分”概念中加入規范性內容,以提出一種正義的合作與分配模式。佐藤將之指出:“從‘分義’的角度來看,社會成員之間的妥善角色區分,以及根據此區分而有的資源分配,應該要依循道德和社會正義。”[23(]p337)事實上,荀子的“分義”觀包括兩個互相涵蓋的目的:一是“去亂”。既然不合理的分配模式會導致爭亂,那么建構正義的分配與合作制度便是止亂的內在要求。這是“分義”的消極目的,正所謂“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大略》)。二是增加人類所欲求的基本善。這是“分義”的積極目的,正所謂“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王制》)。
“分義”構成“群”的規范性基礎,而荀子用“四統”說明“群道”的具體內容,即“生養”“班治”“顯設”“藩飾”(《君道》)。“生養”作為四統之首與“分義”的積極目的相應,而其主要內容即是富民與教民。荀子指出:“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大略》)可見,“分義”的目的體現出的是充足主義(sufficientarianism)主張,即共同體中的每一個體應該有足夠的經濟資源(如田宅)與基礎支撐(如大學、庠序),從而過一種有物質保障的、德性與能力可以獲得發展的良善的生活。正是基于此充足主義,荀子明言包括天子與庶人在內的每一個體的等同之處在于:“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君道》)這在荀子看來實乃“群居和一之道”的根本目的所在。因此,“充足主義”所彰顯的是荀子正義觀的主要目的,而非一個具體的分配原則③陳祖為先生基于孟子與荀子的思想將“充足原則”(principle of sufficiency)闡釋成儒家正義觀的一個原則,本文采用陳先生的這一提法,但將其看作荀子正義觀的目的而非原則。參見Joseph Chan,Confucian Perfection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pp.169—173.根據黃勇先生的相關介紹,“充足主義”(sufficientarianism)的代表人物是哈里·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其具體主張呈現出復雜面向。分別參見Harry Frankfurt,“Equality as a Moral Ideal”,Ethics,1987,98(1),pp.21-43;黃勇:《儒家政治哲學的若干前沿問題》,譚延庚譯,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換言之,一旦荀子正義觀的具體分配原則與這一目的不兼容乃至于相沖突,則立馬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原因在于,在君—民關系或者執政者—民眾關系中,“民”才是目的與根基所在,正所謂“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大略》)。由此出發而構建的差等的政治安排,如“列地建國”“列官職,差爵祿”等,皆非為了“貴諸侯”“尊大夫”(《大略》),而恰恰隸屬于富民與教民這一分義的主要目的。
而“群道四統”的后三者“班治”“顯設”“藩飾”所彰顯的是,基本善的分配應遵循差等原則。其中,“顯設”是核心所在。“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君道》)故而差等原則主要指向的是政治職務的分配與社會職業的分工,而基本善的分配就內嵌在政府職位的分配與社會職業的分工之中,其依據則是個體的德性與能力。荀子指出:“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正論》)荀子強調的是“德”與“位”,“能”與“官”,“賞”與“功”,“罰”與“罪”之間的相稱性,正所謂“分割而等異之”(《富國》)。這種相稱性體現出差等原則其實是一種比例正義原則,即政治職務的分配、社會職業的分工與個體的德性與能力成正比。故而荀子雖然強調“上下有差”,但同時更強調上下之間的流動性①李晨陽先生借助亞里士多德對“數目平等”(numerical equality)與“比例平等”(proportional equali?ty)的區分重新詮釋了先秦儒家的分配正義觀,其對于“比例平等”的闡發主要是基于荀子的思想;與此相應,陳喬見先生分別參照亞里士多德與羅爾斯的正義論對荀子的正義觀進行了厘定。分別參見Li Chenyang,“Equality and Inequality in Confucianism”,Dao,2012,11(3),pp.295-313;陳喬見:《差等、度量分界與權利——荀子義概念中的正義觀》,載《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荀子指出:王公的后代如果不能“屬于禮義”則必須“歸之庶人”;而普通民眾的后代如果能“積文學,正身行”“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王制》)。荀子的真正意圖是要徹底打破以血緣與身份為基礎的世卿世祿制,從而主張政府公職與社會職位應該向所有人開放[26(]p241-242)。
在荀子看來,依據比例正義所建構的制度安排能夠達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的至平效果,農、賈、百工、士大夫、公侯皆以其德、能、技、職“盡田”“盡財”“盡械器”“盡官職”(《榮辱》)。而且,這種關于政府職位與社會職業的分配模式可以獲得每一個體的真心認同,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榮辱》),因而能夠避免人與人之間的爭亂從而實現“不同而一”。
然而,純粹按照個人能力來分配社會的基本善的話,則社會中的每一個體在基本善的享有上的差距將是巨大的。這對于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而言很明顯是不正義的。事實上,上述比例正義僅僅是荀子正義觀的一個原則,而其另一個原則即要求政府在社會善的分配上向這些最不利的群體傾斜,這其實是荀子“分義”所指向的目的“富民”與“教民”的內在要求。荀子指出:
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王制》)
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王制》)
所謂“五疾”,指的是身體有聾、啞、瘸等障礙的殘疾人。荀子認為,對于“五疾”“孤寡”,政府應該收養他們并提供衣食,根據其實際能力給予適當的職位,并對貧窮的人給予補助。荀子雖然認為根據個人能力與德性而產生的社會差距是合理的,但他明言,政府在分配中應該向這些社會最不利群體傾斜。差等秩序的證成取決于社會效用的增益,即“養天下之本”(《王制》),而社會效用的增益雖有利于共同體每一成員的利益,但差等秩序本身卻最有利于社會精英群體。而荀子要求政府給予“五疾”“孤寡”“貧窮”以物質保障與精神關懷則是對這種差等秩序所依據的比例正義原則的限制與矯正①對于社會最不利群體或者弱勢群體的關懷及相應的制度保障始終是儒家政治哲學的核心主張之一,這一主張肇始于《尚書》,經過孔子、孟子、荀子的繼承與系統闡發,對整個中國政治哲學及其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故而,不管中文學界還是英語世界,學者在分析儒家政治哲學及其正義觀時,對這一點著墨頗多。。同時,對于比例正義原則的限制與矯正亦是其被荀子正義觀的充足主義目的所指引、規范的表現。
因此,荀子的“分義”觀有著明確的正義內涵。“分義”的目的體現出的是充足主義,即每個人應該有足夠的經濟資源與基礎支撐,從而過一種有物質保障的、德性與能力可以獲得發展的良善的生活。而“分義”的具體實施則體現出比例正義原則與對于社會最不利群體的制度保障。比例正義原則指向的是政治職務的分配、社會職業的分工與個體的德性與能力成正比,社會最不利群體的制度保障要求政府在基本善的分配上向這些最不利群體傾斜。后者是對于前者的一種限制與補充。
四、“義”的德性之維
如上所說,荀子的“義”觀念在內涵上是多維的、豐富的,其“義”觀念不僅涵蓋正義的內涵及其原則,而且還指向個體德性的內在養成,這兩者有機地統一于荀子思想之中。個體德性的內在養成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與“分義”相應,要求個體具備內在的道德動機去履行其職分或其角色所規定的義務。“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奸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遍矣。”(《君道》)“無靡費之用”“無流淫之行”“無怠慢之事”“無奸怪之俗”“無盜賊之罪”等表述是以否定的形式表達“天子諸侯”“士大夫”“百吏官人”“眾庶百姓”等應具備相應的德性要求。而這種德性要求并非僅僅停留于政治職務、社會分工所確定的職分,更是涉及生活世界中的倫理—政治之域。荀子提出了“君臣之義”“父子之義”“長幼之義”“子弟之義”“禮節辭讓之義”“告導寬容之義”來處理君臣、父子、長幼、鄉親、朋友等因具體角色的轉換而應該具備的不同的內在德性②參見《荀子·非十二子》。。何艾克指出,“義”首先指向一種規定了其角色的制度或秩序,而“義”作為一種美德則指的是一個人履行自己角色的職責并具有相應的動機[27(]p2)。“義”的德性之維的第一個方面的內容很明顯與“分義”所指向的具體角色深度關涉,甚至可以說是以個體在政治、社會、倫理生活中所成為的角色為前提的。
然而,雖然每一個體必然會成為不同的角色,不同角色有其內在的德性要求,但是,每一個整全意義上的個體并不能被分解為不同的角色,而是有著超越于具體角色的自我觀,這正是德性養成的第二個方面的內容。羅哲海指出,一個人的具體角色的規定并不是決定性的,“義”具有超出其角色限制的內涵[28(]p114)。而這正與荀子“義”觀念所指向的君子人格的養成有關。例如,荀子指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子道》)在正常的君臣、父子關系中,作為臣、子所應具備的德性乃是忠與孝,而在這里荀子則提出了超出其角色本身的道德標準——“道”“義”。荀子明言:“義之所在,不傾于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榮辱》)事實上,“義”所指向的超出其角色本身的德性要求即是“公義”或“公道通義”,即荀子所謂“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修身》)。“公義”與“私欲”的強烈對比其實是荀子對于儒家義利觀的進一步深化與彰顯,其實質是要求君子必須養成公正的道德品質。正是在“公”與“私”的對比中,荀子區分出了不同層級的人格特質。
人論: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為修也;甚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眾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問,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儒效》)
從上述引文看,荀子是從“志”“行”“知”三個角度來區分“眾人”“小儒”與“大儒”的人格特質的。眾人的內在志向“曲私”卻希望別人稱贊其公正,其發于外的行為“污漫”卻希望別人認同其有修為,而在認識層面上則是愚昧無知卻希望別人評價其有智識。與眾人不同,小儒能夠克服自己的私欲,其意志能夠公正,其發于外的行為能克制自身的情性且展現自身的修養;而在道德認識層面則能夠做到明智而好問,其人格特質可以被概括為“公正有修養并能決斷”[29(]p335)。而大儒超越于小儒之處在于,其意志與行為不再需要依靠頗具改造與被動意味的克服,而是已經具備穩固的公正品格與道德修養;其在道德認識層面則是能夠認知與貫通統類。從荀子的論述看,“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是理想的君子人格所應具備的三個深度關涉的構成性要素。
事實上,公正的道德品質之具備恰恰與“知通統類”的道德認識能力深度關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荀子指出“義者,循理”“義,理也”(《議兵》)。成為一個公正的人恰恰需要認知與遵循“類”所蘊含的“理”,原因在于“倫類以為理”(《臣道》),“類不悖,雖久同理”(《非相》)。而君子之所以能夠“以義變應”,恰恰在于能夠通過對于“類”所蘊含的“理”的認識而為生活世界中的具體行為提供規范性指引,正如荀子所謂“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不茍》)。佐藤將之指出:“由于荀子同時闡述了‘理’基于‘義’且‘義’也循‘理’的互補性,他似乎主張‘理’和‘義’互為不可分割的一體。”[30(]p226)就義、理、類三者的關聯而言,“義”其實包含著一種德性認知—判斷能力,即“知則明通而類”(《不茍》),而這種能力恰恰與荀子所說的“人道莫不有辨”相對應。
故而,中文學界往往以“辨”為參照來理解荀子在《王制》篇中所闡發的人之為人的特質“義”。這種解釋進路雖然容易遮蔽“義”尤其是“分義”所蘊含的正義指向,但亦從另一個側面切中了荀子對人的德性認識能力的彰顯。更進一步地講,荀子之所以能夠主張“處仁以義”,恰恰在于“類”中之“理”所導向的行為公正性能夠矯正仁愛情感所可能產生的偏向性,正所謂“推恩而不理,不成仁”(《大略》)。與孟子強調“仁”對于“義”的奠基不同,荀子更強調“義”對于“仁”的輔成。因此,“義”的德性之維所指向的具有公正品質的君子人格的養成,既要求“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王霸》)等內在動機、意愿、志向、情性的實質改變、提升與穩固,又要求提升德性認知能力從而能夠“知慮明”“知通統類”。其目的是實現“公道通義”,從而支撐儒家之“仁”的真正落實,正所謂“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王制》)。
總而言之,荀子的政治哲學有著清晰的邏輯理路:荀子首先給出了“自然狀態”中導致群體爭亂的主客觀因素,進而提出“分義”概念以解決基本善的分配與增益問題,最后落腳于個體道德人格尤其是公正品質的養成。暫且拋開荀子所建構的以差等為主要標識的政治—社會秩序不論,其正義觀所體現出的充足主義目的、比例正義原則以及對于社會最不利群體的制度保障,在今天看來都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尤其可以彌補程序性的先驗正義之不足。而荀子關于培育個體公正品質的大量論述,實乃儒家哲學之所長,更可以為當今的正義論建構以及正義感的培養提供有益的理論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