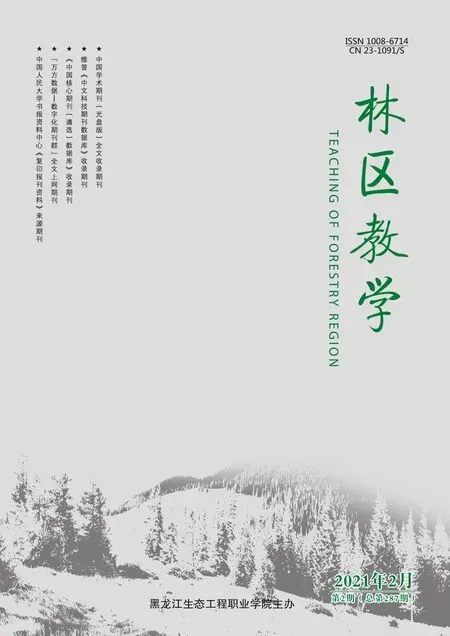《美狄婭和她的孩子們》敘事視角研究
程文強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 100089)
引言
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1943—)作為當代俄羅斯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被譯成多種語言而蜚聲世界。1992年其短篇小說《索涅奇卡》 為她帶來巨大聲譽,2001年獲得俄羅斯布克獎,2007年、2016年獲得大書獎。她以獨特的女性視角和細膩的筆觸描寫了女性的命運際遇和情感體驗,成為當代俄羅斯文壇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長篇小說《美狄婭和她的孩子們》首次被刊登在文學雜志《新世界》上,被稱作“家庭小說”。小說講述了在20世紀近百年歷史變遷的大背景下西諾普里家族在美狄婭的守護與引領下不斷繁衍及壯大的故事。小說通過家族一員的“我”展開敘述,講述了大家族中以女性精神象征般存在的美狄婭一代以及年輕一代的生活經歷。美狄婭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在克里米亞,她所經歷的時代與蘇聯時期基本重合,家族的“小歷史”無時無刻不受到社會政治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農業集體化、斯大林的“民族大遷移”、勃列日涅夫外松內緊“停滯”時代的影響都反映在這個大家族成員的生活中。烏利茨卡婭說:“我的長篇小說《美狄婭和她的孩子們》是一本獻給老一代的書,在一定意義上,是我對家的呼喚。”書中的政權更迭與政策變化奪取了家族中多數男性的生命,美狄婭卻以自身的堅強與獨立、堅守與忍耐承擔著家族的苦難與重任,最終成為家族的守護神。
一、小說的敘事視角
自西方現代小說理論誕生以來,從什么角度觀察故事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1]。敘述視角又稱作聚焦。學界對視角的界定眾說紛紜,20世紀初至今西方敘事理論在形式主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等流派的影響下經歷了“盛—衰—盛”的發展歷程,90年代以來隨著后現代敘事理論的興起,敘述視角問題研究不斷得到豐富。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將視角看作是“與讀者交流的藝術”,俄羅斯學者烏斯賓斯基更將“視角”問題看作是“結構的核心問題”。
敘事學對敘事視角的研究始于20世紀初,對敘述視角的界定向來眾說紛紜,戈爾什科夫在《文學修辭學》中認為敘述視角可分為作者視角和講述人視角,而與作者視角密切相關的是概念即“全知”和“客觀化”,而講述人視角則不同于作者視角,使用第三人稱講述,一般是講述人自己講述,多采用第一人稱形式(“我”或者“我們”)進行講述,此外,講述人同樣也可以以第三人稱方式出現。作者視角與講述人視角都存在敘述的主觀化問題,主觀化的產生主要是由于人物語言的存在,作者視角或講述人視角中人物語言(人物視角)的呈現情況導致了視角的轉換,構成了不同的敘事布局特色。基于上述理論闡釋,結合小說中敘述視角的轉換手段分析烏利茨卡婭作品中的審美效果與主題表達。
二、全知視角下的歷史演進
烏利茨卡婭小說創作極具個人“氣質化的寫作風格”。“烏利茨卡婭是當代俄羅斯重要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大多數小說都以第三人稱展開敘述。從敘述者的語言和態度方面來看,作品中的敘述者常常是一個來自日常生活、善于觀察又貼近主人公生活,特別是熟悉女性生存狀態的講故事的人。”[2]《美狄婭和她的孩子們》中講故事的人“我”正是來自這個大家庭又詳知家族歷史的女性。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主要是一種客觀的全知型敘事,以尾聲部分出現的“我”增加了文章的真實感,拉近了讀者與作者的距離。
作者視角的敘事一般具有全知全能的作用,全知視角“提供全方位的審美感知,注重新奇多變的情節設置。給人以錯綜復雜、變幻莫測的審美快感”[3]。作為現實主義作家偏愛的全知視角,其本身的特性決定了它能夠反映較為廣闊復雜的社會歷史生活。作家托爾斯泰、肖洛霍夫等正是運用全知視角描繪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圖景。全知視角在《美狄婭和她的孩子們》中的使用主要體現在背景鋪陳以及人物介紹層面。
在小說開篇部分描寫美狄婭家族的來歷、現狀以及美狄婭的生活背景時即采用了全知視角描述:“早在遠古時代,這個希臘家族就移民到與古希臘有親密關系的克里米亞海岸來”“現在,美狄婭是這個家族中最后一個純血統的人”“迄今為止,美狄婭的后裔們不斷來到小鎮——俄羅斯人、立陶宛人、格魯吉亞人、朝鮮人……”[4]作為描寫家族紀事型的小說,全知視角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寥寥數語就從古代寫到未來,呈現出宏大的時間維度,美狄婭老一輩與兒女新一輩的故事才能在跨越近百年的政治歷史背景下緩緩展開。而烏利茨卡婭筆下的全知型敘事呈現出其獨有的特色。
首先,對社會歷史、政治背景“輕描淡寫”。在家族近百年的生活經歷中,重大歷史事件僅僅一筆帶過,一方面表面雖然看似美狄婭與社會變遷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她總是對政治保持著疏離,因為在她那里“所有政權都一樣”,而政權統治時期家族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災難,實際卻是個人或家族在社會歷史面前的無奈選擇;另一方面也使“家庭”“家族”的內涵得到豐富與延伸,家的延續與維系依靠更多的不是外在的社會影響,而是內在的道德堅守、無私的愛與家族精神,是文化傳承中獨立的、不依附于男性的美狄婭式的女性。
其次,敘事時間呈現非線性化特征。作者并沒有采用順序式的時間敘事,而是對時間點進行了散落式的處理。故事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四月中旬”,對于年份的確定只能從美狄婭的信件落款日期尋得蹤跡。而故事的發展時間也聚焦在70年代,此時正值美狄婭的晚年,通過她的視角追憶家族人物,回憶親人過往。正如王加興所言,“小說的整個敘述時間,自然是逐漸向前推動的。但由于作者與人物主體域的對立,作者的敘述時間就常常被屬于人物意識的時間所切斷。這樣,時間的運動就取決于不同主體域的相互穿插。”[5]例如,文中通過美狄婭在海灣尋得以前丟失的戒指,回憶了與妹妹1946年夏天的戰后重逢,進而寫到了妹妹年輕時代的生活狀況。可見,時間的發展以人物的視角與事件為導向,時間呈現出不斷回溯的特點。
三、人物視角主觀化手段
人物語言的出現使主觀化得以產生,無論是作者視角還是講述人視角,戈爾什科夫認為在轉向人物視角時主要有兩類手段:一是語言手段,二是結構手段。視角的轉換使得文本從客觀的描述轉向人物的感知感受,人物視角的運用“可產生短暫的懸念,增加作品的戲劇性”[1]。
1.語言手段
烏氏在全知視角的運用中總是掌握著極強的“分寸感”,體現在小說中的全知敘述者并非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或者說即使知曉一切,卻做了很多“限知”的處理。這種對讀者的“限知”是從講述人的視角轉向了人物的視角,戈爾什科夫指出詞匯手段是客觀敘事向敘事主觀化轉變的重要手段,主要的語言手段有直接引語、非純直接引語以及內部言語。烏氏在小說中對非純直接引語的使用既營造了懸疑,又為之后的情節埋下伏筆。例如,“她丈夫是一位快活的猶太人、牙科醫生,具有十分突出的小缺點和隱藏得很深的大優點”[4],作者沒有繼續進行描述,只通過點到為止的方式向讀者“賣關子”。很顯然,這里的“小缺點”與“大優點”是美狄婭的感受與認知,所謂的缺點其實是丈夫對美狄婭堅守的婚姻出軌與背叛,美狄婭僅用了幾天時間就消化了背叛帶來的痛苦,繼續照顧身患重病不能自理的丈夫。此外,作者在對美狄婭丈夫出軌的描寫繼續“拖延”,僅以“那件事”“尼卡的額頭像極了丈夫的額頭”作出提示,這些都是美狄婭視角下的心理感受與所指,利用這種非純直接引語的方式進行鋪墊與伏筆,盡管為讀者設置了理解上的“障礙”,卻不斷激發著讀者的閱讀與探索興趣,為讀者提供豐富的聯想與想象空間。直到丈夫死后美狄婭才知道他的秘密,尼卡是丈夫與妹妹亞歷山德拉之女,這對她來講是一種巨大的打擊,她不僅承受了來自丈夫背叛的痛楚,還要面對倫理道德難以越過的心結。通過非純直接引語的使用將視角從全知型轉向人物內心,巧設懸念,推動了情節的發展。
2.結構手段
講述人視角向人物視角轉換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蒙太奇”(монтаж)式手法的使用,“蒙太奇”這一術語來源于電影藝術,但文學中早已存在類似的手法。修辭學家奧金措夫在《篇章修辭學》中指出:蒙太奇的實質在于,它不僅完全符合人物的視點,也與人物的運動相吻合。它既呈現出場景的運動變化,也反映出人物本身的運動過程。人物的視點在空間上發生了位移,由此形成了鏡頭的轉換(如全景鏡頭、近鏡頭、特寫鏡頭)[6]。
布托諾夫去基什尼奧夫出差路上的景物描寫正是運用了蒙太奇手法。“瓦列里走到了集市。廣場地方不大,卻擠滿了各種車輛和驢騾牛馬。頭戴暖皮帽,蓄著下垂小胡子的矮個子男人們來回拖著籃子、框子和箱子。”[4]此處作者借用布托諾夫的視角對廣場上的人和物進行了鏡頭般的掃描,隨后“他看見了公共汽車癟進去的后屁股……車是空的,瓦列里坐了上去,幾分鐘之后司機鉆進了駕駛室”[4]。人與物的呈現隨著瓦列里的移動而不斷發生空間上的轉變。除了蒙太奇手法的運用,結構手段的另一種是展示手法,戈爾什科夫認為該手法與陌生化手法相似,都是將日常、尋常事物通過不尋常的、奇怪的方式展現出來。小說中多處使用了這種具有陌生化效果的人物視角,例如布諾托夫說“對不起,演出結束了”[4],將布托諾夫與瑪莎的情愛關系隱晦地表達了出來;再如“亞歷山德拉自由言談舉止便受著左腳的支配,美狄婭永遠無法理解這個不可思議的‘左腳’法則”[4],左腳的支配即輕浮愛情的支配。什克洛夫斯基首次提出“陌生化”的概念,指的是將人們習以為常的現象用新的詞語方式表達出來,“增加了感受的難度和時間長度。”[7]瑪莎渴望得到靈魂與肉體完美統一契合的愛情,而布諾托夫只是一個注重觸覺感知的人,無法理解瑪莎的詩歌與內心。在羞恥與失落感中瑪莎陷入深深的精神危機,最終患上了精神分裂癥,小說中對瑪莎病癥的描寫頗具浪漫色彩:“天使出現了。……她聚精會神似乎按了一個電鈕——她的身體開始非常緩慢地脫離山峰。山峰也在輕輕地幫她完成這個動作。”[4]最終瑪莎“做了一個飛到空中去的體內動作……”[4]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陌生化的手段使用加劇了瑪莎死亡的悲劇效果,陌生化作為重要的結構手段在視角轉向人物過程中起著喚醒讀者新奇感、使人脫離生活麻木狀態的作用。
結束語
整部小說采用倒敘的方式,具有強烈的追溯往事的色彩,作者僅在最后一部分出現講述人“我”而將讀者拉回現實,美狄婭的故事發生在過去,但在最后一部分的現實中美狄婭的精神擁有了生生不息的傳遞,她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象征,家族成員遍布世界各地,但卻擁有一個共同的家,一個以美狄婭精神維系著的家園。烏利茨卡婭在與沙列夫的對話中指出,家庭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是寫作中關注的焦點,她認為,世界是一個大家庭,人越強大,個體意義越大,就能夠將更多的人聚集到身邊,這種聚集不一定依靠血緣關系,它可以是鄰里或朋友關系。美狄婭正是這樣一個強大的人,依靠自身的能量不僅將親人后代聚集到克里米亞,還將遺產留給了曾遭驅逐的巴維爾一家,令他們重返家園。
“女性寫作是多元的,烏利茨卡婭從‘細微的家庭敘事’中剝離出了女性的人生體驗,看到了女人在時代巨大變遷中對民族、政治、經濟、文化、重建等問題做出的歷史回應,找到了女人的歷史。”[8]女性自身之美的構建源自烏氏作品中敘述視角與策略的構建:烏氏在其小說中運用了各種不同的視角轉換手段,她通過敘事視角的轉換來調動讀者的鑒賞能動性,使敘事視角呈現出由全知敘事向人物敘事轉換的趨勢,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兩種視角功能各不相同,小說的主題呈現方式也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