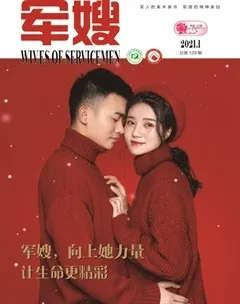裊裊炊煙故人來

隨愛人離開部隊家屬院已有十余年,但不經意間,一些小事常常勾起我對隨軍生活的記憶……當時的家屬院,雖說條件艱苦,但每每憶起,總覺得甜……
一
1993年5月,女兒出生不到100天,父親意外去世,隨后母親也走了,我內心悲痛至極。不久,便帶著襁褓中的女兒小雪,跟隨愛人從湖北黃岡來到遼寧錦州的北鎮。
時近深秋,北鎮更顯蕭條。冷進骨頭的天氣,陌生的環境,孩子的哭鬧,失去親人的痛苦……讓我越發悲觀失望——我想回南方。
家屬院按位置分上院、下院,我們所居住的上院條件相對較好。這里是抗美援朝時建的老院子,幾排紅磚房呈長方形,每戶隔成獨立小院。院墻不到一人高,相鄰兩家相互之間說話很方便。住在我隔壁的,是來自吉林延邊的秦嫂子,是個熱心腸。
初來乍到,我這個南方妹子啥也不懂,更不用說燒土炕了。生火燒炕是個技術活,掌握不好就是個“悶炮”——只冒煙,不起火,也熱不了炕。秦嫂子怕我和女兒凍著,天天大清早就讓女兒經緯抱幾根柴火先送過來。然后,自己過來手腳麻利地往“土暖氣口”加滿水,變戲法似的在火爐處點燃了柴火,火鉗子一鉤,蓋上爐蓋,再往蓋上放一壺水……整個過程一氣呵成,令我驚嘆。
不一會兒,炕熱了,我的心也熱了。
小雪太小,到陌生環境愛哭,比她大4歲的經緯只要聽到她哭,就立馬上炕抱著哄,小大人似的逗小雪笑。說來也怪,只要經緯一唱:“沒有花香,沒有樹高……”小雪就會安靜下來。
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整個家屬院都仿佛裹在白被子中,秦嫂子手把手教會了我燒土炕。兩個月后,當來自四川閬中的家屬董靈住到我家另一側時,她燒炕被煙熏成“黑貓警長”,還是我給她點燃了第一把火。
那時,我沒有奶水,“巧手廚娘”董靈煲湯時,總會給我端過來一碗讓我喝了催奶。
春暖花開時,家屬院綠意盎然,從沒種過菜的我也學著種上各種蔬菜。董靈是種菜能手,將小菜園打理得井井有條,尤其是辣椒長勢喜人。秦嫂子到董靈家菜園,隨手摘上一個辣椒,在衣服上蹭幾下,就直接吃起來,看得我們目瞪口呆。
在此之前,我從不生吃菜。后來,我家最愛吃的菜便是秦嫂子教我的——豆皮卷大蔥蘸大醬。多年以后,小雪出國留學,在世界各地嘗過很多美食,也仍然忘不了這一口。
嫂子小麗是遼寧錦州人,我倆偶爾喜歡炒幾個小菜聚一下。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奧成功那晚,當電視里喊出“北京”兩個字時,我和小麗一起沖了出去,在家屬院里高喊“中國萬歲”。那種澎湃的激情,永生難忘。隨后,我倆抑制不住興奮再次舉杯慶祝,至今想來都覺得幸福、自豪。
在異地他鄉,一群來自天南地北的家屬們,陪伴我度過了人生最艱難的日子,讓我和小雪在這里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溫暖,也終于堅定了安營扎寨的心。
在北鎮待了整整5年,給我留下印象的不僅是當地的景色和燒雞、豬蹄,最主要的還有這些軍嫂姐妹。因為有了她們,這里的一切才那么讓人留戀!
1998年,因部隊整編,我們這些花兒隨著號令各奔東西。大多數家屬隨愛人轉業回到地方,留在部隊的沒幾個,我和愛人禮明是其中一對。
二
1998年底,我們到了鄰近的義縣,開啟了又一段家屬院生活。
義縣與北鎮雖都隸屬于錦州,環境氣候卻大相徑庭。北鎮山清水秀,除了雪花漫天的冬季,樹是蔥郁的,風雖涼卻也柔和。而義縣地理位置特殊,風是從內蒙古吹來的,里面裹挾著沙子,人出門溜達一圈,回家鼻孔、耳朵里就有沙粒,嘴里咀嚼,就會有咬到沙子時的那聲“嘎嘣”響,毫不夸張。
這里家屬院的房子是土磚結構,據說還是抗美援朝時建的,土疙瘩墻皮直掉,還常有老鼠、蛇、蝎子出沒。
住在這樣的房子里,依然能感到生活的溫暖。
義縣的家屬院比北鎮的大,天南地北的人更多。照樣,我們這些家屬雖不熟悉,卻并不感到陌生。有了北鎮生活的底蘊,沒多久,我在義縣的生活也開始熱鬧起來。環境的惡劣阻礙不了我們的歡樂,我又結識了一個又一個好友。
家屬們都有著非同一般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因為愛吃新鮮黃豆,房前屋后的空地扒拉扒拉,就種出了大片大片的黃豆,家屬們隨便摘,隨便吃。想念家鄉的紅菜薹,我們照樣種出了一株又一株,還有竹葉菜、茄子、黃瓜……我們開墾了四季地,開墾了新天地。
住我隔壁的是軍工李阿姨。她帶我在院子里種玉米,還種一種叫“拌倒驢”的蘿卜。秋收時,真的是一地水靈靈的大蘿卜,大家都來拔,一人抱一袋回家,歡聲笑語灑滿院落。
身為義縣本地人的李繼紅,曾帶我去她老家的屯子吃小妹的婚宴,讓我見識了北方的流水席:幾口大鍋炒菜,盛菜到桌上,走馬燈似地換碗盞,沒幾下就吃飽了,那情景頗為壯觀。
湖北漢陽老鄉小方,是個心靈手巧、干凈整潔的女子,北方粗糲的風沙,絲毫沒影響她白白的皮膚。我們常常一起帶著孩子走那條土路到街上逛,買些水果和日用品,或坐在院子里織毛衣。那些日子織了無數件毛衣,都寄給了遠方的親人。
三
相聚時暖,別更難。2003年,禮明自主擇業,我隨他回到了老家。記得剛到家,便接到軍工李阿姨輾轉打來的電話。李阿姨說,常常看我住的屋子里頭的燈亮了,出來的人卻不是我(住進了其他人家)。說著說著,她老人家在電話那頭哭,我在電話這頭哭。
離開義縣已十余年,我和家屬院的小王一直保持著親人般的聯系。2019年深秋,她從老家湖南長沙回部隊辦愛人的病退手續,便拍了一組家屬院的照片和視頻發給我。她最懂我,知道我的這點念想。人老了,看著照片和視頻,不勝唏噓,眼眶不由自主就濕了。
視頻里,天很藍,房很新,但顯得空空蕩蕩的,沒有了往日的熱鬧和歡騰。有的地方徹底變了模樣,土房子沒有了,建成了樓房,整潔了不少。我努力找尋自己當年住過的那排房子,找不到,再也回不去了。我們這些家屬,已隨丈夫完成使命,分散到四面八方安居樂業了。
回想當年,小王的愛人在部隊被查出患了一種病,但她不離不棄,婚后毅然從長沙趕到義縣照顧,還生下了兒子仔仔,在土疙瘩房里、土炕上一人支撐起一個完整的家。她的臉上,從沒有愁苦的表情。她平時對我很好,只要我說肚子疼,她總是端來一碗當歸紅糖水,里面臥兩三個雞蛋。
如今,我們已過知天命之年,但保持聯系的幾個人依然時不時打個電話、發個微信,嘮叨著的是兒女的幸福,是身體的健康。我們相約,哪家孩子婚嫁,我們都要到場。
2016年小麗兒子結婚時,我們家不遠千里趕去參加。小雪從法國留學歸來,不顧旅途辛苦,剛飛回武漢就直接坐動車到錦州,說要去給哥哥送祝福(孩子們從小一起玩,感情深厚)。只是秦嫂子多年音信全無,不知她在遙遠的吉林延邊一切可好?經緯是否已嫁人生子?軍工李阿姨前些年已退休,每到春節,我都會打電話問候,祝福她老人家身體健康……
這些真誠的記掛,相信在家屬院待過的人,都有共鳴。
(作者丈夫曾服役于陸軍某部)
編輯/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