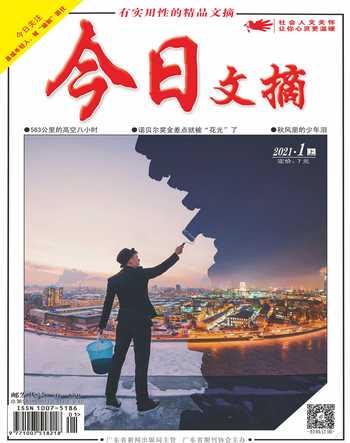縣城年輕人, 被“編制”困住

人總是被困住的。
社畜被格子間困住,外賣騎手被系統困住,工人被流水線困住……
那些畢業后回縣城工作的年輕人,大多被“編制”困住。
在那里,“編制”成了一個復雜的符號,它象征的不再僅是一份工作,還有父母終其半生的希望、社會地位和階層躍遷的假象以及未來可能美好的生活。但有些時候,對身在其中的年輕人來說,它更像是一個鳥籠,牢牢地將他們困在其中,從身體到精神,從開始到結束。
盡管他們中很多人知曉自己被困的現實,但就像是籠中鳥一樣,對飛出去后的人生,充滿恐慌。
“考”上的才叫工作
許佳覺得累,從畢業后開始考工作到現在工作都是。
2019年10月,她終于考上了帶“編制”的工作。于她而言,“終于”二字是必須加上的。因為這是她第八次考工作,但卻是第一次成功。
許佳現在在云南一個邊境小縣城體制內工作,談不上理想和喜歡,但這份工作是父母期望和被周圍人認可的。為此,許佳付出的是兩年的時間和很多個難眠的夜以及無數個否定、懷疑自己的瞬間。
在許佳最初關于大學畢業后的規劃中,回家考“編制”是很靠后的選擇,排在最前的是繼續求學。但到了大三要開始選擇人生下一階段的路徑時,父母的意見涌來了,“家里說我年紀太大了,先考工作吧”。許佳的父母一輩子做小生意,自覺那種生活又累又沒保障,所以最希望女兒能有個穩定有保障的工作。
許佳說,“年紀大”這一點的確戳中了她。她也開始覺得如果再讀三年書后,一切可能都太晚了。而且當時家里經濟狀況有些拮據,妹妹又即將讀大學,需要錢。考慮到這些,許佳順應了父母的希望。但其實所謂年紀太大,也不過是比周圍同學大了一兩歲而已。這起因于許佳高三復讀了一年,但這事她很少對人提起。
想好后,許佳一心撲到了考“編制”上。大三一結束,她就回家報了“國考”輔導班。學費很貴,但父母和她都咬牙交上了。本來她大四第一學期仍是有課的,但為了考工作,她請了長假。就這樣,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她進了考場。
“多少分不記得了,反正是沒考上。”許佳告訴我,國考失利后,她很快投入了下一場考試。繼續失敗,敗在了面試。下一個。她一點沒拖沓。
接下來她碰到了一個覺得是為自己定制的機會,因為當地很多年不招她那個專業的煙草集團今年突然有指標了。列出的職位要求,完全符合她的條件。當時,考進煙草集團成了許佳最迫切的愿望和目標,因為那是出了名的好單位。
筆試后,她順利進面。面試又敗了,但這次卻把她打倒了。出結果后,許佳查了自己的總評成績,離錄用她只差了0.04分。在她有限的經歷中,從未聽說過這種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分差。
許佳覺得當初所有的希望,都變成了壓力的巨石,一塊塊砸在了身上。“我在床上躺了快一個星期都沒有振作回來。”她說。同時,她對自己徹底失去了信心。“我已經這么努力啦,從來沒有這么努力過,都沒有成功,那我后面是不是都不會再成功了?”她問自己。
但她沒有停止考試。在那種深度懷疑自己和“萎靡”的狀態下,許佳還是參加了當年的省考和之后的事業單位考試。
悉數落榜。
求職的第一年就這樣過去了。應屆生,這個多少帶點優勢的身份也失去了。
在一次次的落榜后,父母總是幾天吃不下飯。盡管沒有直接的責怪,但總會喃喃地重復“怎么每次都差一點點。到底哪里出問題了?”許佳說,最難過的時候她能感受到父母的失望和無奈。
之后,許佳去媽媽做生意的城市緩了兩個月。感到狀態好轉后,她又報了輔導班開始準備第二次“國考”。一切又重新開始。那段日子,許佳的一天,除了短暫的吃飯和睡覺時間外,全被上培訓課、刷真題、背知識點填滿。
但許佳依然敗考了,之后的省考也是,仍然差了一點。到這一步,父母已經有了“認命”的表現,開始跟她提接班的想法。她也去母親做小生意的地方“見習”了一個月。
但許佳是幸運的,她之后接到了國考補錄的通知。最后,離家3小時車程的一個邊境縣城政府單位錄用了她。
回想過去的兩年,“把它(編制)當成安身立命的基礎”是支撐她堅持下來的動力,許佳說。
在工作的瑣碎里失去自我
“考”上工作的喜悅,沒在許佳的生活中持續太久。沒有周末、紀律森嚴、無意義的工作瑣事,使她感覺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她沒有想過諸如“存在”的意義這樣深刻的哲學命題,但她覺得工作后“存在”的意義似乎只是為了上班。那個被人們頻繁提及的“自我”好像丟失了。
葉雨也有著同樣的自我丟失感。她在重慶一個縣城做公務員,她原以為小縣城生活壓力小,生活會穩定且舒適。然而,回想工作這兩年,一點一點累積的壓力像一座山壓在心頭,她漸漸明白,“生活從來都是一地雞毛,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葉雨回家工作,也是不得已的選擇。大四第一學期,父親意外離世,徹底打亂了葉雨全部的人生規劃。她收起想去大城市打拼的心,一心回家頂上父親的位置。葉雨“考”上工作的經歷比許佳順遂,畢業跟工作順利交接。
葉雨不是個主動討好的人,但剛畢業的她對工作充滿熱情,“雖然不太會說話,但想努力工作,給領導留個好印象”。可葉雨這種溫和的性格和認真的工作態度,給她帶來的不是什么另眼相看,而是越來越多的工作。“單位所有的材料都推給我寫,加班成為家常便飯,堆積如山的文件,密密麻麻的工作便簽,沒完沒了的工作應酬,回家的時間從8點9點,慢慢變成11點12點。”葉雨說。
而家人和朋友認為,工作多是領導器重人的一種方式。所以,她得到來自家人和朋友最多的寬慰是“年輕人就要多干一點”。那段時間,母親還沒有從鎮里搬來縣城。葉雨一個人住在他們一家人咬牙買下的二手房里,完全沒有家的感覺。每次加完班回家已是深夜,迎接一身疲憊的是一屋子的冷清。“回到家孤零零的一個人,工作上的煩惱沒人訴說,很多時候只能捂著被子哭。就是這樣,我對未來的美好期待,一點點被磨光。”葉雨說。
積蓄、婚姻和未來
在很多一線城市的故事里,小縣城是逃離北上廣的人的退路,因為那里消費低、生活節奏慢還能存下錢。
葉雨不同意。
“工作兩年來,我并沒有什么積蓄。”葉雨說,到手4000多元的工資,一月下來根本存不下多少。我們印象中,縣城是物價低廉的象征,但都變了。葉雨所在的縣城,一份外賣平均20元,其中配送費5元。這已經跟一些大城市沒有太大的區別。跟朋友同事聚餐,每次也多是六七十元。而且葉雨家所在的縣城,宵夜氛圍濃厚,凌晨一兩點的大排檔仍然是人頭攢動。一頓宵夜下來一般不少于200元,這種邀約一周不少于三四次,一次兩次可以拒絕,多了也難為情。
但最讓她們難以接受的是當地的房價。葉雨自己也不知道,一個十八線的縣城,房價憑什么能漲到均價8000元的地步。看著年年上漲的房價和基本不漲的工資,葉雨覺得對這個雖然居住但并不太熟悉的縣城,又少了一份歸屬感。
離家近,催婚也催得緊。這不止來自父母,還有身邊幾乎所有的人。葉雨把這描述為:“在小縣城,處處充滿了對單身女孩子的惡意。”
剛工作,就有同事競相給葉雨介紹對象,并反復給她“洗腦”女孩的黃金年齡是25歲,過了這個年紀就不好找了。“尤其在體制內,優秀的單身女孩越來越多,優秀的男生卻是越來越少。”她單位有個28歲的同事工作了5年還沒有談戀愛,每天都為感情焦慮,擔心自己結不了婚。
在縣城,有編制的工作的確是最好的“歸宿”。這一點,許佳和葉雨她們也承認。但生活本身就像是座圍城,別人在羨慕自己進入體制內的時候,自己卻又想象著城外的生活。而這也讓許佳她們對未來既愛又懼。愛“所有人”公認的體制內工作能帶來的幾十年后的安穩和舒適,又懼這份工作當下的瑣碎和壓抑。
許佳沒有想太多以后的種種,只想做好當下分內的事情。葉雨有過離開的想法,但也只是離開工作單位而非體制。
“有時候走在路上,看著灰暗的天空,憤怒,焦慮,憂郁,沮喪,頹廢,種種情緒不可避免,我經常會想,離開這里會不會好過一點?今年9月,我試著考了一下市里的遴選考試,沒有進面。明年,我還想試試,想看看離開這里,我的選擇會更多嗎?我的空間會更大嗎?我的呼吸會更自由暢快嗎?”葉雨說道。
(江華燦薦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