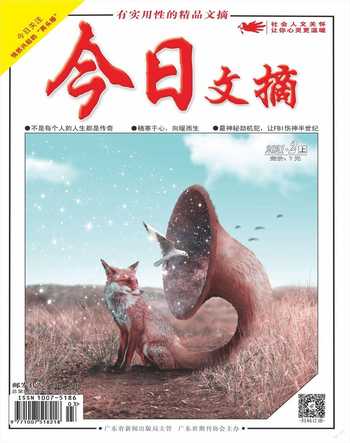你不是佛系,你只是在逃避

知乎上有人問起:“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變得佛系?”有一個高贊的回答是:“因為低估了佛系的境界。經(jīng)歷過生離死別、大風(fēng)大浪,嘗過人生百態(tài)卻能安之若素,才夠得上是佛系。年紀輕輕,人生才剛剛開始,就說自己佛系,只能說是活得太懶,缺乏激情,逃避現(xiàn)實罷了……”年紀輕輕,閱歷尚淺,人生的道路才剛剛啟航,大風(fēng)大浪,艱難險阻都在后面,卻被眼前的碎石逼迫得繞道而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孬種。
朋友趙海就是一個典型的“佛系青年”。這一年是他大學(xué)畢業(yè)的第二年,仍然在家鄉(xiāng)的小縣城上班,在輔導(dǎo)機構(gòu)做家教,每個月拿著4000元的工資。有一次,他邀請我去他家玩,飯后,我們一起坐在沙發(fā)上閑聊。我不禁好奇地問道:“趙哥,你怎么不出去發(fā)展?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在蘇錫常地區(qū)落戶嘛。”趙海一副參透世間百態(tài)的語氣答道:“你不懂,我在外地打拼了一年,終于是看透了,這外面的社會黑暗得很,都是人吃人的,沒點背景,抓不住機會,你根本混不下去,還是佛系一點好。你看現(xiàn)在我的生活一帆風(fēng)順,雖然工資不高,但足夠養(yǎng)活我自己了呀!”事實上,社會是讓人成長的最好環(huán)境,平臺越大,風(fēng)險越大,同時機會越多。需要的只是一個有足夠的勇氣,有過硬的本領(lǐng),不斷學(xué)習(xí)進步的意志。
年輕的時候,不求上進,靠著三四千的工資,養(yǎng)活自己是沒有問題了,可是以后的生活,可不只是養(yǎng)活自己這么簡單。一個健康的家庭算是成年人肩上最輕的擔子了。持續(xù)佛系,就是埋在未來生活上的一顆定時炸彈,只要一點小變故就可以引燃。
佛系青年們把佛系看成是一種極高的修養(yǎng),在旁人看來,只是頹喪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嚴格意義上來說,這跟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差不多,都是想辦法來包裝自己弱小和卑微而已。從來就沒有社會太黑暗,只是有人不愿奮斗。所以就把社會的不公平無限放大,用來給自己的懶惰做擋箭牌。知道自己懶惰,自己懦弱,卻又不愿承認,自然就只剩下一個辦法,那就是逃避。稱自己為佛系青年自然不失為最好的途徑。既如愿地逃避了自己不思進取的現(xiàn)實,也巧妙地維護了自己的體面。
值得被我們效仿的“佛系”,應(yīng)該是被今天的人們忽略很久的沉心靜氣。在表面看來,這與佛系差不多,但實際上,它卻舍棄了佛系的“不作為”。
錢鍾書就深諳“沉住氣”的道理。在那個是非混沌的年代里,縱使面對著不堪入耳的侮辱和無端的指責(zé),也坦然面對,依舊專心致志地創(chuàng)作。直到《管錐編》出版后,錢鍾書再次聲名鵲起,出人意料的是,錢鐘書先生并沒有到處講學(xué),接受采訪,取而代之的是閉門謝客。在他看來,把優(yōu)秀的作品留給世人品讀,在文壇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就足夠了,自己不需要再去出風(fēng)頭。
沉住氣才是我們應(yīng)該追求的一種佳境,絕非佛系,它是需要我們長期磨練自身才能獲得的一種品質(zhì)。
作為普通人的我們,應(yīng)該在年輕的時候敢于冒險,勇于嘗試,增長資歷,方能獲得內(nèi)心的充盈,以此達到沉心靜氣的佳境。真正的精致生活,源于刻苦,成于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