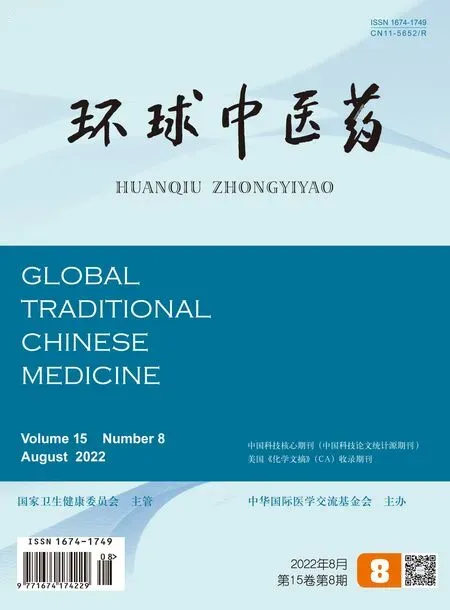薛雪《濕熱條辨》舌診辨證及用藥探析
侯森瀧 張福利
所謂濕熱,指濕邪與熱邪合而為一,進而侵犯人體,或伏留于人體內的邪氣。濕熱證,是指濕熱蘊結體內,臟腑經絡運行受阻,可見全身濕熱癥狀的病理變化。濕熱具有兩重性,兼有屬陰邪之濕邪與屬陽邪之熱邪的特性,其轉變既可隨過用寒涼而寒化[1],又可從素體熱盛而熱化[2]。濕熱證的證候表現,既有如惡寒、胸痞、不欲飲食的類似濕邪的癥狀,又有如但熱不寒、汗出、口渴的類似熱邪的癥狀。針對濕熱證的一般癥狀和特殊兼證,薛雪在《濕熱條辨》中將濕熱證分為“正局”和“變局”分別加以闡述[3]。但由于濕熱證的復雜性、多變性,單一憑借脈象診斷濕熱證的證型,特別在兼有特殊兼證時,便顯得捉襟見肘。正如《濕熱條辨》中的提綱注解所言,“濕熱之癥脈無定體,或洪或緩,或伏或細,各隨癥見,不拘一格,故難以一定之脈拘定后人眼目也”。脈診“難以一定”,則舌診的重要性便得以彰顯。當代國醫大師楊春波認為,舌象是濕熱病辨證中的首要和關鍵,并在其一則驗案中介紹了結合舌象變化治療濕熱泄瀉的經驗[4]。廈門大學醫學院王彥輝教授介紹其應用舌診治療濕熱病的經驗時也指出,舌象是判斷身體寒熱濕邪狀況的重要依據,在濕熱病辨證治療的過程中占據關鍵地位[5-6],這表明在濕熱證證候診斷與用藥治療的過程中,舌診的診察結果,有時會對證型判定和加減用藥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1 舌診在濕熱證辨證中的作用
《濕熱條辨》中與舌診有關的條文共十條,分別是第一條、第五條、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廿五條、第三十二條和第三十五條。其中,舌診的作用主要是在辨病位所在、辨病勢輕重、辨病程轉歸的三個方面;舌診觀察的角度主要是看舌苔多少、舌苔分布、舌苔顏色、舌質顏色、舌體變化五個方面。
1.1 由舌診辨病位所在
《濕熱條辨》中,載有通過舌診辨病位所在的條文有第十條、第十二條和第廿五條。第十條中記載:“濕熱證,初起發熱,汗出,胸痞,口渴,舌白,濕伏中焦。”[7]發熱、汗出、胸痞、口渴,這四個經問診所得的癥狀,若是熱證,亦可出現類似情況,但在薛雪看來,因為舌苔為白色,而未見舌苔黃或舌質紅等熱象,故認為此時侵犯人體的邪氣是濕邪而非熱邪。至于判定病位在中焦,則因為中焦乃氣機上下之樞紐,唯有濕伏中焦,氣機上下交互受到郁滯,上不得下,下不得上,故有胸痞;郁而化熱,故有發熱;上焦氣機尚通暢,故能有汗出;津液輸布亦須從中焦而行,因濕邪伏于中焦,輸布失常,故有口渴。僅從問診所得的癥狀難以判定邪氣性質及病位,薛雪用“舌白”這一舌象,察明邪氣性質為濕邪,再與其他癥狀相合,辨明此證為濕熱證,正處于初起的階段,其病位在中焦。
第十二條記載:“濕熱癥,舌遍體白,口渴,濕滯陽明。”[7]52舌遍體白,指的是舌苔顏色為白且分布于整個舌體。口渴而舌苔反白而滿布,說明并非是熱灼津傷,而是濕困氣機,津液不能布化而有類似津傷的癥狀,所受邪氣是濕邪而非熱邪。舌苔為胃氣所生,在此條中,其分布遍于全舌,是濕邪正中于足陽明胃并滯于其中,受胃氣蒸騰,上化而為苔所致,所以最終可辨其病位為足陽明胃。
第廿五條記載:“濕熱癥,身冷脈細,汗泄胸痞,口渴,舌白,濕中少陰之陽。”[7]56此處身冷、胸痞為外寒、氣郁之癥,汗泄、口渴好似熱癥,病位病性就這些癥狀來說難以把握。然從舌脈兩診來看,舌診僅有舌苔白,并未提及有苔黃質紅,或舌體裂紋、萎縮等典型熱邪傷陰的舌象,而脈診卻出現脈細,說明脈細并非熱邪傷陰所致,而是內有陽氣衰微,外有濕邪困阻,此消彼長之下,其人脈道較其體型而言為細,正如薛雪后文所說“肥胖氣虛之人夏月多有此病”,此證為濕邪所致,而非熱邪所成。足少陰腎乃人身之命門,其中相火為人一身陽氣之本,相火為濕所困,溫煦周身不利,郁而化熱,則易有外寒內熱、脈細舌白之癥。從這三條條文來看,舌診在濕熱證的辨證過程中可以起到先定邪氣性質,繼而由邪氣性質參合其他癥狀來明確病位的作用。
1.2 借舌診察病勢輕重
《濕熱條辨》中,載有通過舌診辨病勢輕重的條文有第五條、第七條、第十五條和第三十二條。第五條中記載:“濕熱證,壯熱口渴,舌黃或焦紅,發痙,神昏,譫語或笑,邪灼心包,營血已耗。”[7]50壯熱口渴、發痙、神昏、譫語或笑這些癥狀為熱擾心神的癥狀,心主血而屬營,故知其病位在營血;而其舌象為“舌黃或焦紅”,此處“黃或焦”當指舌苔,“紅”當指舌質。營和血,較衛和氣而言同屬于陰,陰當以平靜和緩為其本性,緩慢滲注、濡養全身當為其常態,故舌質以淡紅為佳。而條文中的舌質為紅,是由熱盛耗血動血所致;舌苔焦黃,是熱邪傷津,又不得營血所養,進而出現了由黃而焦、焦而欲黑,火極似水之象,故可斷為營血已耗。
第七條中寫道:“濕熱證,壯熱煩渴,舌焦紅或縮,癍疹,胸痞,自利,神昏,厥,痙,熱邪充斥表里三焦。”[7]51壯熱煩渴、胸痞、癍疹,是熱在上焦的表現;自利為邪在中焦;痙、厥為熱邪入下焦,傷于陰精,陰不斂陽而引起,僅由這些癥狀,雖可知患者熱勢已盛,遍布三焦,但對其病勢進展、危重程度的認識尚不直觀。而從舌診來看,所謂“舌焦紅或縮”,指的是舌苔顏色焦黃、舌質紅、舌體萎縮。舌苔顏色焦黃,說明熱盛在表,耗傷氣津且程度較深;舌質紅,說明熱盛于里,耗血動血;舌體萎縮,標明體內陰精大損。由舌象的診察可知患者體內熱邪早已充斥表里,遍及各層,且可直觀地看出熱邪對人體各層面損傷的程度已深,進而可以得出熱邪已充斥表里三焦,情況危重的結論。
第十五條中論述:“濕熱癥,四五日,口大渴,胸悶欲絕,干嘔不止,脈細數,舌光如鏡,胃火受劫,膽火上沖。”[7]54由舌光如鏡可知胃陰大傷,兼有脈細數可知胃火較盛;而口大渴、胸悶欲絕等癥看似上焦熱證,但在已知胃陰大傷的前提下出現這些癥狀,則不可武斷為上焦熱證,而是陰不斂陽,膽火犯胃所導致的兼證,此時病已入后期,需小心處理,且預后不佳。
第三十二條中寫道:“濕熱癥,經水適來,壯熱口渴,譫語神昏,胸腹痛,或舌無苔,脈滑數,邪陷榮分。”[7]58此處的“舌無苔”為判斷病勢輕重的指標,若有,則病勢較重,為邪陷營分且營陰大傷;若無,則病勢較輕,沒有到達營陰大傷的程度。從以上四條條文中可以看出,舌診在濕熱證的辨證過程中可以通過舌苔、舌質和舌體的變化,直觀地顯現出病勢的輕重,進而為醫者判斷其預后提供重要的依據。
1.3 經舌診明病程轉歸
《濕熱條辨》中,用舌診辨病程轉歸的條文有第一條和第十三條。第一條為濕熱病提綱:“濕熱證,始惡寒,后但熱不寒,汗出,胸痞,舌黃或白,口渴不引飲。”[7]47此條文中,“舌黃或白”不僅僅是體內寒熱狀態在舌象上的客觀反映,更是對于濕熱證后期病程如何轉歸的判斷依據。由于濕熱具有兩重性,既可寒化變為寒濕內盛,也可熱化導致化燥傷陰。若為舌苔黃兼有其他癥狀,即使兼有的癥狀是“惡寒”“不引飲”這種看似偏于寒邪傷人、陽氣虛衰的癥狀,也不過是濕邪在表而郁熱在里,整體為熱邪偏盛。雖然暫時有寒濕較盛的癥狀,其之后的轉歸極大可能會向熱證轉化;若是舌苔白兼有其他癥狀,即使兼有的癥狀是“但熱不寒”“口渴”類似熱證的癥狀,也是整體濕邪偏重而局部有郁熱,之后病程的轉歸基本會向濕重于熱的方向發展,若此時不慎投入較多寒涼藥劑,則易最終導致濕熱轉為寒濕。
第十三條則記述:“濕熱癥,舌根白,舌尖紅,濕漸化熱,余濕猶滯。”[7]53此條條文對于舌診中舌苔的分布、動態變化有了描述,從而直接的由此判斷濕熱證的病程轉歸。舌尖紅而舌根白,表明舌尖之處舌苔已然略顯稀疏而舌根部分舌苔相對致密,因此給醫生的直觀舌象是舌尖紅而舌苔白。而對“濕漸化熱,余濕猶滯”,這一在此舌象基礎上對濕熱證后期病程轉歸的判斷,薛雪在這條條文下自撰的注釋中如此解釋:“蓋舌為心之外候,濁邪上熏心肺,舌苔因而轉移。”[7]54也就是說,薛雪認為,舌苔轉移的原因是因為心開竅于舌,是心這一“內藏”在“外象”上的反映,而濁邪此處應當指濕熱夾雜而熱重于濕的穢濁之邪,熱重于濕,上熏心肺,而在舌苔上有所表現。而之后的病程轉歸,由于舌質紅而舌苔已有分散、減少的趨勢,所以被認為是濕熱走向熱化。雖有“余濕猶滯”,亦須加大寒涼藥物的用量。由此二條條文可知,舌診相較于其他癥狀明顯有異的征象,往往對之后濕熱證的寒化或熱化的轉歸有所提示;同時,舌象總處在不斷動態變化的過程中,而非一成不變或忽而轉變的,明確舌象動態變化的趨勢,對于辨明濕熱證的轉歸也具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2 舌診對后續用藥的影響
《濕熱條辨》中,舌診對用藥的影響主要從舌象本身來看。舌苔的多少、舌苔的分布、舌苔的顏色、舌質的顏色以及舌體的狀態決定了濕熱證用藥時藥物種類與用量的加減變化。具體而言,薛雪共列舉了三種濕熱證可見舌象,以此為示例對濕熱證舌診辨證及用藥進行闡述。
2.1 舌苔白、多且分布較廣則需辛味藥條暢氣機
在濕熱證中,舌苔顏色為白色、舌苔較多、分布較廣,多意味著濕盛而氣機不暢,或為脾陽虛衰而化濕無力。與其他癥狀合參,若兼有口渴、胸悶等癥,則為濕盛而氣機不暢,在兼顧其他癥狀用藥的同時,需用辛味藥條暢氣機。如第十條、第十二條和第十三條,均有舌白,而之后的用藥中,第十條濁邪上干、胃液不升、濕伏中焦,用藿梗、蔻仁、杏仁、枳殼、桔梗、郁金、蒼術、厚樸、草果、半夏、干菖蒲、佩蘭葉、六一散等味[7]52;第十二條濕邪極盛、尚未蘊熱,用厚樸、草果、半夏、干菖蒲等味[7]53;第十三條濕漸化熱,舌苔白之外兼有舌質紅,用蔻仁、半夏、干菖蒲、大豆黃卷、連翹、綠豆衣等味[7]53。三條條文中,均有厚樸、半夏、干菖蒲等辛味藥;若兼見脈細身冷,則為濕邪傷陽,脾陽虛衰而化濕無力,如第廿五條,濕中少陰之陽,此時正氣已虛,辛味藥雖能燥濕,但大開大合,透散耗泄之力較強,不利于正氣的恢復。故用人參、白術健脾補氣、固本培元,用茯苓健脾兼淡滲利濕,用益智仁、附子提振一身之陽,以共奏通補并用之效,達補正祛邪之功[7]56。
2.2 舌苔黃焦、苔少而舌質紅則兼甘寒藥清熱養陰
若舌苔顏色為黃色或焦黃、舌苔較少、舌質紅,則多象征著熱盛而有陰液耗傷,但耗傷不甚,此時用藥,若僅用苦寒類藥物清熱解毒,則易苦燥傷陰,使自身陰津被進一步耗傷,以致陰陽失衡,病入膏肓。因而對于這種狀況,需在清熱解毒,兼顧他癥的同時,兼以甘寒類藥物清熱養陰。如第五條中,壯熱口渴、神昏譫語,為濕熱致厥證。在用藥時,除用犀角、羚羊角、鉤藤息風通絡,連翹、銀花露清熱解毒,鮮菖蒲、至寶丹開竅醒神之外,另加生地、玄參等甘寒類藥物,以達養陰之效用。三類藥物相合,可成清養并舉之勢,達標本兼治之功[7]50。
2.3 苔焦黃、舌質紅而舌體萎縮則投清熱養陰重劑
若出現舌苔焦黃、舌質紅而舌體萎縮,則有陰傷過重、陰液耗竭之危象,此時則急需加大清熱及養陰用藥的劑量,增投力道更為強勁之藥劑,切莫躊躇不前,舉棋不定,以致錯失良機,徒呼奈何。如第七條中所述之證較第五條中為重,同為濕熱致厥證,第五條中癥狀僅出現壯熱口渴、神昏譫語,而第七條中癥狀除壯熱口渴、神昏之外,出現了心煩、斑疹、胸痞、自利等癥狀[7]51,此時已熱邪充斥三焦,陰傷更重,舌體亦出現萎縮,故薛雪在用藥時,用“大劑”犀角、羚羊角、生地、玄參、銀花露、菖蒲等味,并在此之外,又加紫草、方諸水、金汁鮮三味藥物。紫草甘咸而性寒,內可療臟腑之熱結,外可透斑疹與瘡瘍,為涼血活血、透熱于表之要藥。方諸水所指代之藥物眾說紛紜,一說謂其為鏡面所承之露水,另一說謂其為在月盛之時,以蚌殼摩擦生熱后置于月下所聚之水,第三說謂其為陰符所取之水。據李佛基[8]考證,清代醫家朱心農認為方諸水為活蚌水,并將體重五百克至八百克的活河蚌剖開,以其中二百至三百毫升體液為此藥,配伍治療時病和內、兒科急重癥,效果顯著。清代趙學敏在《本草綱目拾遺》中稱其“有清熱行濕治雀目夜盲之力”,為“真陰天一之精”。現代皖南名醫張必烈以方諸水挽救危重癥經驗頗豐,謂此物為血肉有情之品,可有草木難奏之捷效,并常以其沃將竭之真陰,屢建奇功[9]。金汁鮮即鮮金汁,又名“糞清”“黃龍湯”,由人的糞便制取而成,味苦性寒,能大解五臟實熱。石斌豪等[10]認為,其屬濁陰,出下竅,性速而能下泄,存極苦大寒之氣味,入足陽明經而制其陽亢,又因埋土時久,得土氣厚,去濁留清,更增其效。總體而言,在第七條中,隨著舌象的變化,用藥的種類進一步增多,劑量進一步加大,無論是作用范圍還是作用力度均有所增強,以此來挽狂瀾于既倒,急救亡而圖存。
3 總結與討論
《濕熱條辨》全書僅四十六條,其中涉及舌診辨證及用藥的條文便有十條,由此可見舌診對于濕熱證辨治的重要性。此十條條文,從其自身橫向而論,闡明了舌診所察之舌苔多少、舌苔分布、舌苔顏色、舌質顏色、舌體變化各自的“象”與對應的人體內生理病理變化的“藏”之間的聯系,并將如何運用舌診結果結合其他癥狀,判斷濕熱證病位所在、病勢輕重、病程轉歸的方法全盤托出;若將條文之間進行縱向對比,書中列舉的“舌苔白、多且分布較廣”“舌苔黃焦、苔少而舌質紅”“舌苔焦黃、舌質紅而舌體萎縮”三種濕熱證可見舌象,以及薛雪對應總結出的“用辛味藥條暢氣機”“以甘寒類清熱養陰”及“急投清熱養陰重劑”的用藥法則更可體現舌診結果對濕熱證用藥的種類、性味和劑量的影響,并可從中體悟濕熱證隨舌象變化加減用藥的理法。
就同期醫家而言,溫病四大家均重視舌診,且著作中多有對舌苔、舌質、舌體等各種舌象的診察,但葉天士、王孟英、吳鞠通側重基于衛氣營血辨證體系,對溫熱證的舌象診察規律進行總結,對濕熱證的認識有所不足[11-13];薛雪則更側重基于三焦辨證體系,對濕熱證的舌象變化及相應的用藥時機、種類、劑量進行了總結,為溫病濕熱證的診療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及經驗。而就當前《溫病學》教材的濕溫部分而論,雖汲取多名醫家的著作對濕熱證各種證型的舌象與用藥有所總結,較之《濕熱條辨》的一家之言更加全面,但也因此使得證型之間的銜接不夠連貫,易被理解為多個典型證型的集合,證型之間舌象轉化關系并不緊密,用藥風格迥異;且對單一證型的病機發生轉變時雖亦有用藥加減的描述,卻只是“癥狀+對應用藥”的列舉,而對舌象變化及其內蘊理法的解釋不夠詳盡,使得在臨床面對復雜病機,如新患濕熱卻兼有基礎性疾病、體質影響導致證型不典型等情況時捉襟見肘。而《濕熱條辨》中雖列舉證型不及教材全面,卻銜接緊密,多有“舌象—用藥—舌象變化—用藥變化”的描述并對其中理法進行了詳盡解釋,具有較高的臨床應用價值[14]。
然而,由于薛雪其人受《易》學影響頗深[15],推崇“融會古人,出以新義”,用藥風格靈活多變。林志斌[16]、孫利祥等[17]認為,薛雪用藥特色之一便是注重因證給藥創新方、師古方而不泥古方。在《濕熱條辨》中,各條文之后藥物均劑量不明且不組為成方,僅列舉多味可用藥物,表明薛雪作《濕熱條辨》之立意更側重理法大要的闡述,其用藥的種類及性味更似與前文理法相呼應之示例,這也使得《濕熱條辨》中對于舌診辨證與對應用藥之間的關系論述相對較少,雖有規律可循,卻也顯得綱要精準而細節不足。不過即使如此,《濕熱條辨》中對舌診辨證及用藥的闡述也較全面而翔實,其中體現出的“動態觀察舌象”“憑舌而不泥于舌”的思想,對于現代中醫舌診的臨床及科研也具有一定的啟發和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