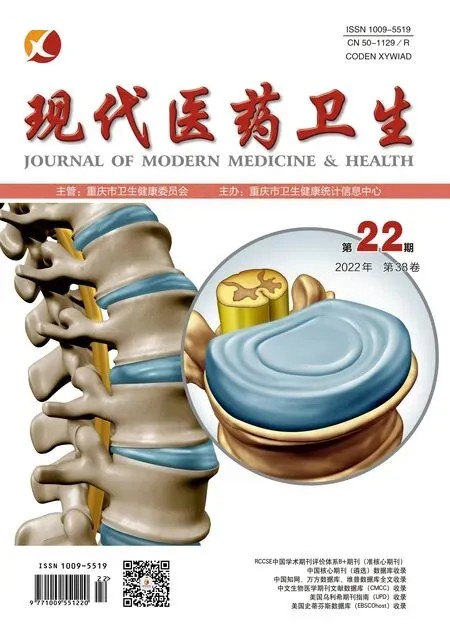睡眠障礙與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相關性研究進展
崔月萌 綜述,常 江 審校
(昆明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消化內科,云南 昆明 650000)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是指除過量飲酒及其他明確病因的肝損傷所致的、以肝實質細胞脂肪變為特征的一組臨床病理綜合征外,還涵蓋了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及進一步進展的肝硬化、肝癌。NAFLD是中國乃至全球慢性肝病的首要病因,中國大陸NAFLD患病率高達29.81%[1]。胰島素抵抗(IR)、肥胖、炎性反應、腸道菌群紊亂、遺傳易感性等都屬于NAFLD發病因素,而現有研究表明睡眠障礙與NALFD具有很大的相關性。
隨著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睡眠障礙已成為一種公眾健康問題。在第3版《國際睡眠障礙分類》中,睡眠障礙被劃分為失眠、睡眠相關呼吸障礙(如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嗜睡、晝夜節律睡眠-覺醒障礙、異態睡眠等[2]。其中,失眠是最常見的類型,以入睡困難和(或)睡眠維持障礙為特征。現有流行病學調查指出,全球失眠患病率為10%~40%,在三級醫院門診就診的老年人失眠患病率更是高達57.7%[3-4]。2011年中國15~69歲居民睡眠質量調查中[5],約有35.7%的成年人睡眠質量較差,且這一數值仍在不斷增長。睡眠障礙同NAFLD一樣,均已成為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公共衛生問題。人體內的代謝反應、炎性因子水平及活性、自主神經功能、腸道菌群組成及功能等重要生理過程都需要睡眠參與調節,這可能是睡眠障礙與NAFLD相關的原因。因此,隨著睡眠障礙、NAFLD二者發病率的逐年上升,研究睡眠障礙對NAFLD的影響具有重要臨床意義。
1 睡眠障礙與NAFLD的關系
現階段絕大多數關于睡眠障礙與NAFLD關系研究多是從睡眠時間對NAFLD的影響這一角度著手。睡眠占據了人類生命1/3的時間,原則上成年人應保證每日7~8 h的充足睡眠,考慮到年齡、性別、運動量水平的差異,適合具體個體的睡眠時長并不易界定。因此,當前關于睡眠時長對NAFLD發病影響尚存在爭議。在OKAMURA等[6]所納入的12 306例受試者的橫斷面研究中,首次證實了睡眠時間小于或等于5 h是NAFLD發病的高危因素。另外,午睡時間過長(≥30 min)[7]、晚睡[8]等睡眠不足均會升高NAFLD發病風險。在KIM等[9]的研究中,睡眠不足(≤5 h)與NAFLD發病風險增加的相關性在調整了體重指數(BMI)后僅在中年女性中存在,這說明了在探討睡眠時長對于NAFLD的影響時,年齡、性別、運動量水平等需考慮在內。但值得注意的是,現有關于長時間睡眠對NAFLD影響的研究較少。韓國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時間睡眠(≥8 h)與NAFLD風險評分升高相關[10]。一項關于睡眠時長與全因死亡率的meta分析結果顯示[11],長時間睡眠和短時間睡眠的死亡風險均明顯高于正常睡眠時間。而在日本的一項橫斷面研究中發現,睡眠時長與NAFLD發病風險之間呈現出一種“U”型關系,即睡眠時長處于6~7 h的女性NAFLD發病率最低,在小于或等于6 h及大于或等于8 h組中女性NAFLD發病率又逐漸增高[12]。
目前,對睡眠障礙的評估除睡眠時長外,還包括入睡時間、早醒、日間嗜睡、睡眠維持困難等睡眠質量方面。目前,國際上多采用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對睡眠質量進行評價。因此,在絕大多數關于睡眠質量與NAFLD關系的研究中,多采納了這一量表,這些研究均顯示睡眠質量不佳可增加NAFLD發病風險[13-15]。綜上所述,睡眠障礙與NAFLD發病之間具有明顯相關性。現階段大多數研究均證實了短時間睡眠可明顯升高NAFLD發病風險,長時間睡眠與NAFLD之間的關系還需進一步大規模、高質量的RCT研究。另外,在評估睡眠質量方面,現有研究中均存在評估方法過于單一這一問題,未來研究中還可以納入如Epworth嗜睡量表、睡眠狀況自評量表、社會時差量表等,以幫助臨床研究人員更全面地評估睡眠障礙與NAFLD之間的關系。
2 睡眠障礙影響NAFLD的可能機制
2.1IR和炎性反應 IR所致肝內脂肪蓄積是NAFLD發病的始動環節,肝細胞內炎性反應等“二次打擊”促進了肝細胞脂肪變。近年來,有研究證明,睡眠障礙可以誘導IR和炎性反應,所以睡眠障礙可能在NAFLD的發病及全球流行中發揮了一定作用。
2.1.1IR 一項研究通過噪聲干擾受試者正常睡眠后發現,受試者睡眠周期中非快動眼睡眠和慢波睡眠占比大幅下降,胰島素敏感性明顯降低[16]。BUXTON等[17]在對無糖尿病的受試者進行連續7 d睡眠限制后發現所有受試者均出現了明顯的IR。這說明睡眠質量下降和(或)睡眠時間受限均會導致糖代謝異常而出現IR,IR出現與睡眠障礙引發的應激反應有關。睡眠障礙屬于一種生理性應激源,可使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被激活。HPA軸及其所分泌的皮質醇受睡眠-覺醒周期調節,正常情況下皮質醇水平在覺醒后迅速升高,睡眠開始后逐漸下降。睡眠障礙會使HPA軸處于慢性持續活動狀態,升高皮質醇、胰高血糖素等激素水平,促進糖異生、誘導IR[18]。另外,IR的出現與自主神經系統(ANS)功能紊亂也有關,正常睡眠時交感神經活動受抑,睡眠障礙會導致交感神經過度活動而迷走神經活動受抑,從而使支配白色脂肪組織的交感神經活動增加,抑制其分泌脂聯素,而脂聯素具有改善胰島素敏感性、減輕肝內脂肪沉積的作用[19]。因此,睡眠障礙所致皮質醇等激素水平升高、交感神經過度活動,進而引發IR是NAFLD發生的原因之一。
2.1.2炎性反應 除IR外,睡眠障礙與炎性反應也關系密切。近期研究證實了睡眠障礙可升高多種炎性細胞因子水平(如TNF-α、IL-6、IL-1β、hs-CPR等),使機體從中樞至外周均處于一種慢性炎癥狀態[20-21]。首先,睡眠障礙可上調炎性基因的表達并激活多條與免疫相關的基因通路[如Toll樣受體信號通路、核因子-κB(NF-κB)信號傳導通路][21]。其次,睡眠障礙可影響HPA和ANS兩大效應系統,從而改變基礎基因表達譜,使其傾向于增加炎癥基因的表達,升高炎性細胞因子水平[22]。再者,睡眠障礙可抑制免疫細胞的活性及數量,降低機體免疫力,增加感染風險,引發炎性反應[21]。綜上所述,睡眠障礙會使脂聯素的分泌受抑,而脂聯素可降低IL-6、TNF-α水平,抑制肝Kupffer細胞及肝星狀細胞活性[19],故脂聯素分泌減少無疑會促進NAFLD發生發展。
2.2不良生活狀態 健康的生活狀態建立于良好的睡眠之上,而現代社會生活節奏迫使大多數人陷入一些不良生活狀態之中,如暴飲暴食、高鹽高脂飲食、久坐、熬夜、輪班等,打破了正常睡眠習慣,罹患各種類型的睡眠障礙。睡眠障礙反過來也會影響個體的生活狀態如飲食、運動等,二者互為因果,陷入惡性循環。在飲食方面,對于睡眠不足、睡眠質量差者,其飲食模式常表現出與傳統一日三餐節律相違背的進食特點——進食次數增多、進食時間點向夜間轉移、更易選擇高熱量的食物[15]。睡眠障礙所致上述飲食模式的改變可能與以下幾個方面有關:(1)睡眠不足會降低發揮抑制食欲作用的瘦素水平,升高具有增強食欲作用的胃饑餓素水平[18]。DASHTI等[23]在對受試者進行連續兩晚睡眠限制后發現,受試者循環中瘦素水平下降了18%,而胃饑餓素水平升高了28%,因此睡眠不足會增強人的食欲,激發進食行為。(2)睡眠不足可刺激中腦邊緣多巴胺能系統,行為上表現為睡眠不足者會更傾向于選擇攝取高熱量食物及更頻繁的夜間進食[24]。另外,睡眠不足會增強大腦背側前扣帶回皮質同殼核及島葉之間的神經活動,這些腦區之間的活動增加與脂肪攝入量呈正相關[25]。(3)睡眠不足、晚睡的人清醒時間延長,進食機會相應增多。在運動方面,對于睡眠時間短、睡眠質量差的NAFLD患者,體力活動量及運動量均明顯低于健康人[15]。睡眠時間過長或嗜睡的人活動消耗量也明顯下降,這可能與其臥床時間延長所致日均活動量及消耗量降低相關[26]。
睡眠障礙可明顯增加不健康飲食的攝入、減少運動量,若此時相應攝入量增多未帶來對應的消耗量增加,長此以往會增加肥胖型NAFLD的發病風險,對伴有睡眠障礙的NAFLD患者來說,其減肥失敗及減重后體重反彈的概率均遠高于無睡眠問題的NAFLD患者[27]。對存在睡眠問題的NAFLD患者來說,改善睡眠不僅可提高胰島素敏感性、減輕炎性反應,還可幫助人們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的調整正是NAFLD治療的基石。
2.3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 OSA是指睡眠過程中反復出現的低通氣及呼吸暫停。OSA屬于睡眠障礙的一種類型,以白天嗜睡、睡眠碎片化、打鼾為其主要特征。OSA的患病率在男性中為10%~17%,在女性中為3%~9%,男性、高齡、肥胖、頸短、上呼吸道軟組織功能及結構異常均是OSA發病的高危風險因素[28],而NAFLD與OSA之間存在一些相同發病高危因素,如肥胖。現研究表明,OSA與NAFLD密切相關[29-30],慢性間歇性低氧(CIH)是OSA發病的關鍵機制,故OSA可能是通過CHI介導了NAFLD的發生。CIH 可誘導IR、上調炎癥基因及相關信號通路表達、誘導包括SREBP1c及FASN在內的成脂基因表達、引發肝細胞內質網應激及脂質過氧化、促進肝內膠原蛋白交聯。因此,CIH是OSA與NAFLD相關并加速其進展的一個機制[29]。打鼾是OSA最常見的癥狀,會增加微喚醒的次數,從而導致睡眠碎片化,WANG等[30]研究發現,習慣性打鼾可作為預測NAFLD發病的一個有效指標。OAS嚴重程度與IR、炎癥水平、脂肪肝的程度呈正相關。在控制了(如肥胖、煙酒等)OSA危險因素之后,經鼻持續氣道正壓通氣(CAPA)是成人OSA患者首選治療方式,CAPA可改善OSA患者的睡眠狀況。LIU等[31]在對患NAFLD的OSA患者進行持續3個月以上的CAPA治療后發現,其肝酶學、肝脂肪變及肝纖維化情況較治療前好轉,這從側面證實了睡眠障礙和NAFLD相關性及解決睡眠問題可能有助于肝臟獲益。
2.4腸道菌群失調 腸內的營養物質被吸收后經腸系膜靜脈至門靜脈入肝,當腸道屏障被破壞,肝臟將受到腸道內微生物及其相關代謝產物的損害,因此腸道菌群失調被認為是NAFLD發病的病原學因素。正常情況下腸道菌群保持著動態平衡,而其平衡又嚴格依賴于良好的睡眠。睡眠障礙主要通過擾亂腸道菌群的晝夜節律,從而破壞菌群的組成和數量。在組成方面,睡眠限制的小鼠腸道菌群中擬桿菌、普拉梭菌等菌種減少,厚壁菌門相對增加,而后者可促進腸道吸收更多食物中的熱量,從而增加肥胖的發病風險[32]。在數量方面,睡眠障礙減少了菌群的豐富度,破壞了“菌膜”的完整性,使腸道通透性升高。此外,睡眠障礙引起的交感神經過度活動也可提高腸道通透性。腸通透性升高會使原有的定植菌及外源性病原體及其產物跨上皮移位,引發炎性反應、IR、肝脂肪變。因此,睡眠障礙可通過破壞腸道菌群穩態而促進NAFLD的發生。研究發現,補充腸道微生態制劑可改善血脂代謝、減少肝內脂質堆積、減輕肝內炎性反應,從而緩解NAFLD[33],同時微生態制劑也可有效改善睡眠質量[34],因此微生態制劑可能為治療伴有睡眠障礙的NAFLD提供新的思路。
2.5生物鐘紊亂 為適應地球自轉所帶來的24 h光線變化,絕大多數生物進化出了一種內源性計時系統-生物鐘。在分子層面上,生物鐘是由Per及Cry基因所構建的轉錄翻譯反饋環,由轉錄因子Bmal1和CLOCK激活;在解剖層面上,生物鐘由位于下丘腦視交叉上核的中央鐘和位于外周器官組織的外周鐘構成[35]。生物鐘能預見外部時間變化,從而驅動機體做出相應的應答,如生物鐘可通過預測每天的進食-禁食及睡眠-覺醒周期,調整體內合成及分解代謝過程以滿足不同時段對于能量的需求。生物鐘調控著生命體內在活動的節律性。肝臟作為人體內最大的新陳代謝場所,其內代謝反應大多受生物鐘調控。以脂質代謝為例,在肝內進行的包括脂蛋白合成、脂質吸收轉化、脂肪酸從頭合成等過程均受生物鐘調控;另外,血漿中15%的代謝物受生物鐘調控,而這些代謝物中很大一部分是脂質[15];生物鐘失調還會誘導SREBP1c等成脂基因表達。因此,生物鐘紊亂必然會破壞整體脂質代謝,進而出現高血脂、異位脂肪沉積、NAFL等。除外脂質外,生物鐘紊亂也會干擾血糖穩態調節,如純合子Clock突變小鼠及Bmal1基因缺失的小鼠均表現出了高血糖、IR、高胰島素水平、高血脂、肝脂肪變等[36]。另外,體內絕大部分激素分泌、炎性反應、腸道菌群等都受生物鐘的調控。可以看出生物鐘紊亂會引發全方位的代謝紊亂,而生物鐘的正常運作離不開規律的睡眠,睡眠紊亂可使內源性生物鐘與外部時間去同步化,引發上述代謝紊亂過程,增加NAFLD發病風險。此外,NASH發生發展的機制包括內質網應激、脂毒性、IR、線粒體功能障礙、氧化應激等同樣受生物鐘調控[37]。因此,改善睡眠有利于維護生物鐘正常運轉,以保證肝臟晝夜動態平衡,降低NAFLD發病風險。一項關于晚睡與NAFLD發病風險相關性的前瞻性研究結果顯示:晚睡(≥22:00)可明顯增加NAFLD發病風險,晚睡時間增加1 h,NAFLD發病風險增加29%[8],這與晚睡使個體暴露在更多的光線下導致松果體分泌褪黑素節律紊亂相關。褪黑素因具有調節睡眠的作用而用于治療失眠,其分泌嚴格受生物鐘調控;另外,褪黑素還具有強大的抗氧化功能;褪黑素還能改善晝夜節律基因的表達如脂質代謝相關基因SCD-1、CD36、Abcg5等,從而減輕肝臟脂肪堆積、促進胃腸道內膽固醇排泄[38]。因此,褪黑素也表現出顯著的預防NAFLD甚至肝癌的作用。這說明睡眠障礙所致生物鐘紊亂的治療方式(如褪黑素使用、生物鐘靶向治療等)將有利于NAFLD的防治。
3 小 結
睡眠可影響人的生活方式、體內糖脂代謝、腸道菌群穩態及生物鐘同步化等,因此睡眠在NAFLD的發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當前,針對NAFLD治療主要基于改善生活方式之上,但NAFLD治療效果常因患者較差的依從性及較低的健康意識水平而多不盡如人意,這提示醫務人員針對睡眠的干預可能是NAFLD治療的關鍵之一。鑒于現代快社會生活節奏不易矯正的現實性,生物鐘紊亂難以避免,因此,除外生活方式的調整,生物鐘的治療可能為NAFLD的防治提供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