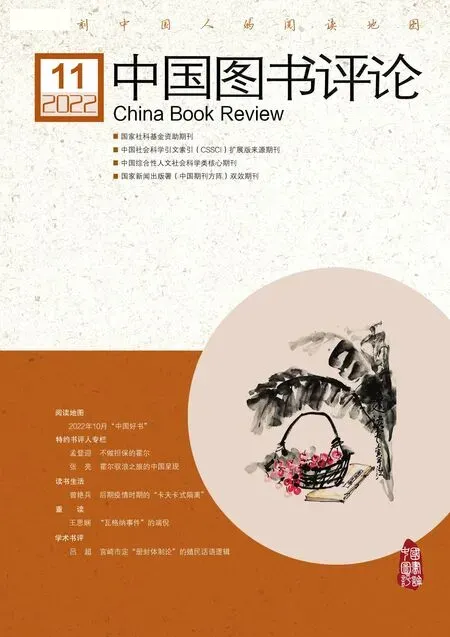“瓦格納事件”的端倪
——從《悲劇的誕生》看尼采與瓦格納的“合”與“分”
□王思嫻
【導 讀】 作為塑造德國精神的兩位偉大思想家, 尼采與瓦格納自相識以后, 二人的名字便緊緊地綁在了一起。 從尼采早期代表作《悲劇的誕生》 中, 可以看到二人思想的“合” 與“分”。 而“瓦格納事件” 則透露出, 在尼采心目中,“瓦格納” 儼然成為德國精神的象征和代名詞。 因此, 尼采與瓦格納的分道揚鑣不僅是兩個個體之間的沖突, 也是尼采與他心目中的寄托的決裂。
一位是哲學天才,一位是音樂家、戲劇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理查德·瓦格納 (Richard Wagner),作為塑造德國精神的兩位偉大思想家,自相遇、相識之后,二人的名字便緊緊地綁在了一起。身為藝術家的瓦格納試圖用他的音樂和“整體藝術”(Gesamtkunstwerk)理想重塑德國民族精神,這讓當時年輕而富有朝氣的尼采看到了復興德國乃至歐洲文化的希望。然而,瓦格納后期浮夸而庸俗的風格讓尼采深感失望,二人的友誼宣告破裂,于是有了哲學史和音樂史上的“瓦格納事件”(Der Fall Wagner)。
瓦格納對尼采的影響不可謂不大。在尼采生命最后所寫的自傳《瞧,這個人》(Ecce Homo)中,他這樣看待自己與瓦格納之間的關系:“我把瓦格納視為我生命中最大的恩人。我們有親緣關系的原因,在于我們遭受到的痛苦要比本世紀其他人所能忍受的痛苦更深,而且我們還要遭受互動干戈的痛苦,這就將我們的名字永遠連在一起。”[1]44
《悲劇的誕生》(Die Geburt der Trag?die)作為尼采首部發(fā)表的作品以及早期思想的代表作,它的誕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瓦格納。在這部書的前言“致理查德·瓦格納”中,尼采激動地寫道:“我確信有一位男子明白藝術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來的形而上活動。我要在這里把這部著作奉獻給這位男子,奉獻給走在同一條路上的我的這位高貴的先驅(qū)者。”[2]88青年尼采視瓦格納為德國復興道路上的先驅(qū),從《悲劇的誕生》中可以看到很多瓦格納思想的影子。但同樣是從《悲劇的誕生》開始,尼采的思想已經(jīng)開始與瓦格納產(chǎn)生分歧,這就為之后二人走向?qū)α⒑蜎Q裂埋下了伏筆。
一、尼、瓦二人的“意合”之處
1872年,尼采出版了他的處女作《悲劇的誕生》。在此之前,青年尼采視為先驅(qū)者的瓦格納已經(jīng)發(fā)表了眾多論述當時藝術和未來藝術的文章,如《藝術與革命》(Die Kunst und die Revolution,1849)、《未來的藝術作品》(Das Kunstwerk Der Zukunft,1850)、《歌劇與戲劇》(Oper und Drama,1851)等,逐步提出了他著名的“整體藝術”理念,其藝術思想和藝術實踐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的反響。
對比尼采的早期著作與瓦格納的理論文章,不難發(fā)現(xiàn)二人在思想和精神追求上的重合與交疊。或許我們可以大膽推測,尼采的思想除了從叔本華的唯意志論與瓦格納的戲劇音樂中吸取靈感外,還直接受到瓦格納文字的啟發(fā)。前者已有眾多學者參與討論,而后者尚未被深入開拓,這也正是本文所致力挖掘的地方。
尼采與瓦格納生活的19世紀后期,是德國由分裂走向統(tǒng)一,率先實現(xiàn)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的時代。彼時的德國在普魯士的帶領下,逐漸走出戰(zhàn)爭的泥潭,德意志帝國宣告成立。統(tǒng)一之后,德國在政治、社會穩(wěn)定的基礎上,大力發(fā)展工業(yè)經(jīng)濟,提升科學技術水平,整體呈現(xiàn)出欣欣向榮的局面。然而,尼采和瓦格納都看到了工業(yè)、科技發(fā)展所帶來的隱患。
1873年,尼采的第二篇《不合時宜的考察》(Unzeitgem??e Betrachtungen)論文創(chuàng)作完成。在這篇文章中,尼采指出現(xiàn)代科學活動的野蠻性。工業(yè)和科技的發(fā)展讓人逐步異化,“生命換上了非人體的齒輪轉動裝置和機械裝置的毛病”[1]88,同時文化也變得僵化、庸俗。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對片面崇尚科學、理性而扼殺生命本性的現(xiàn)代文化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認為科學和理性實則是一種貪婪的求知欲,它讓藝術被迫緊緊攀緣著辯證法的主干,藝術精神逐漸在邏輯公式中化為木偶。[2]141尼采所看到的科學、技術、理性對人性和藝術文化的壓制,與瓦格納在《藝術與革命》和《未來的藝術作品》中所討論的情形是一致的。
早在1850年前后,瓦格納已經(jīng)意識到了工業(yè)、科技對藝術及藝術家的危害。他認為現(xiàn)代藝術創(chuàng)作者與其說是“藝術家”,不如說是有點藝術修養(yǎng)的“手藝人”和“工匠”。藝術對于他們來說,不是享受,而是勞動; 不是快樂,而是負擔; 不是自發(fā)的,而是強迫的。他們已經(jīng)完全淪為工業(yè)的奴隸。[3]瓦格納對推動工業(yè)發(fā)展的科學以及科學背后的理性主義也進行了反思和批判。他認為真正的藝術作品應當是“直接訴諸感官的,在它最赤裸裸地現(xiàn)身的瞬間展示出來的藝術作品”[4]40。倘若科學和理性先于“赤裸裸的”藝術而存在,那么藝術自身最原始的本性和感性力量也就被遮蔽甚至不復存在了,這必然是對真正藝術和文化的巨大打擊。
那么,真正的藝術應當是什么樣子的? 對于尼、瓦二人來說,現(xiàn)實生活中是否存在或存在過他們理想中的真正藝術呢? 答案是肯定的,這種藝術就是古希臘的悲劇藝術。
在尼、瓦二人看來,悲劇是古希臘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結合的產(chǎn)物。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鮮明地提出了這一點。而在瓦格納的《藝術與革命》一文中,這一觀點已經(jīng)初見端倪。
瓦格納首先給予日神阿波羅(Apollo)極高的地位。他認為,阿波羅具有明朗嚴肅的外表、崇高的精神氣質(zhì),因此受其影響而產(chǎn)生的藝術是優(yōu)美而富有力量的。對于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us),瓦格納明確提到“悲劇詩人受酒神鼓舞”,也就是說,他將酒神視為悲劇產(chǎn)生的一大重要影響要素。緊接著,瓦格納又強調(diào),當受到酒神鼓舞的悲劇詩人看到日神阿波羅時,會自發(fā)地通過語言將所有豐富的藝術元素匯集到一個焦點上,從而產(chǎn)生出最崇高的藝術品——戲劇。[5]由此,瓦格納隱隱地將戲劇視為酒神與日神共同作用的結果。顯然,瓦格納的這一思想在尼采那里得到了繼承,并得以充分發(fā)揮。
尼采認為,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彼此結合,最終產(chǎn)生了既是酒神的又是日神的藝術作品。這種藝術作品是“酒神認識和酒神作用的日神式的感性化”[2]116的戲劇,是作為“日神和酒神這兩種彼此交織的藝術本能的表現(xiàn)”[6]66的悲劇。可以說,尼采在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的二分以及悲劇的誕生方面,與瓦格納是一脈相承的。
尼采與瓦格納都將戲劇或悲劇看作最完美的藝術品,而對于時下流行的工業(yè)文明的產(chǎn)物——現(xiàn)代歌劇,二人則持批判態(tài)度。
瓦格納認為,歌劇完全拋棄了藝術的靈魂。在希臘悲劇衰落之后,它被分解成了各個獨立的組成部分。這些組成部分逐步發(fā)展成為今天獨立的藝術門類,歌劇就是其中之一,然而這些獨立的藝術門類并沒有繼承悲劇的核心精神。瓦格納犀利地指出,現(xiàn)代劇場藝術流于表面,只是一種富有技巧性的、吸引人的表演,完全稱不上是什么真正的戲劇。現(xiàn)下流行的歌劇已經(jīng)失去了戲劇的核心和最高意圖,只是各種感官刺激的大雜燴,混亂,毫無韻律可言。[7]
尼采對瓦格納的觀點表示強烈贊同,他諷刺歌劇極其膚淺而不知虔敬,夾雜了太多非藝術的傾向。歌劇致力于迎合觀眾的理想、想象和音樂本能而全然失去自然的藝術本性,它試圖用高超的演唱技巧以掩蓋自身藝術氣質(zhì)的天然缺乏[2]156-160,但本質(zhì)上,它已經(jīng)喪失了原本存在于悲劇藝術中的對美的追求和對人類自我、自然宇宙的真實展現(xiàn)。
透過尼、瓦二人對歌劇的批判,可以看出他們實際上是在反思受工業(yè)、科學和理性影響而扭曲的現(xiàn)代藝術。瓦格納看到,以歌劇為代表的現(xiàn)代劇場藝術是工業(yè)發(fā)展中機械性的產(chǎn)物,只會喚起人們不自然的、毫無節(jié)制的需求,從而將人帶入歧途。[4]50尼采將歌劇視為科學和理性的產(chǎn)物,它所呈現(xiàn)的內(nèi)容與真正的藝術相沖動,即與感性活動相沖突[2]160-164,這就不利于德國民族精神和歐洲精神文化的復興。尼、瓦二人暗含的意思是說,現(xiàn)代工業(yè)的特點是重復進行機械性的勞動,它最大化地壓制了人們的本性和情感。因此,工業(yè)文明下產(chǎn)生的歌劇,必然不會自然地表現(xiàn)人們的感性,也就不會激起人們內(nèi)心的情感共鳴,這些恰恰是藝術的靈魂所在。而正因為這類藝術不會表現(xiàn)深層次的感性訴求,它們只能轉而訴諸膚淺的技巧,以刺激感官的方式掩蓋它自身的空虛。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因為感官刺激會產(chǎn)生即時的快感,所以一旦這類藝術泛濫,人們會迷戀它所帶來的生理刺激。而當人沉迷于聲色之時,就逐漸失去了對精神性事物的追求,這必然阻礙了個體自身的發(fā)展。同樣對國家和民族來說,這也不利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復興。
由此我們看到,尼采和瓦格納面對當時工業(yè)、科學和理性扭曲人文藝術的情況,提出了自己的藝術理想。他們視古希臘悲劇為理想藝術,并在批判現(xiàn)代藝術特別是現(xiàn)代歌劇這一點上,達成了高度一致。這些都反映出二人希望實現(xiàn)民族精神復興的共同愿望。
二、超越瓦格納與分道揚鑣
偉大的思想家往往是在吸收前人思想精華的基礎上,糾正、彌補前人的不足,并拓展尚未被開發(fā)的領域。這些,23 歲的尼采都做到了。
雖然瓦格納已經(jīng)初步提出了日神、酒神與悲劇誕生之間的密切關聯(lián),但是尼采并沒有止步于此。首先,在日神精神方面,尼采創(chuàng)造性地從德語詞源的角度將“日神”與“外觀”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引出了日神代表靜穆、素樸的造型藝術的觀點。在德語中,schein 兼有光明和外觀的含義,因此“日神”在德語“der Scheinende”中也可以翻譯為“制造外觀者”。[2]89-90尼采將“光明”和“外觀”聯(lián)系起來并指出,制造出美的外觀以美化世界,這正是日神的智慧。其次,尼采洞察到,日神精神之后還有更深層次的酒神精神。日神藝術所反映出來的古希臘世界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般美好,在美麗外觀的背后隱藏著一種對未知的恐懼和生存艱難的痛苦。而酒神精神的提出,某種程度上是對這種痛苦經(jīng)驗的揭露。尼采認為日神的“整個生存及其全部的美和適度,都建立在某種隱蔽的痛苦和知識根基之上,酒神沖動向他揭露了這種根基”[2]101。如此一來,尼采便將酒神置于日神之上,賦予了酒神前所未有的地位和高度,從而顛覆了前人(包括瓦格納)普遍以日神為大的傳統(tǒng)。
而瓦格納在行文中依舊遵循以日神為尊的希臘文化傳統(tǒng)。在希臘神話中,日神阿波羅作為主神宙斯(Zeus)所寵愛的兒子,其誕生地提洛思(Delos)被確立為希臘的中心。同時,阿波羅還被視為希臘的開國之神,其神殿位于希臘宗教的中心德爾菲(Delphi)。因此,日神阿波羅在希臘文化中處于至高無上的正統(tǒng)地位,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瓦格納多次強調(diào),阿波羅是希臘民族真正的主神,人所有的苦難和哀樂都在阿波羅身上體現(xiàn)出來。[8]相比之下,酒神雖然也是奧林匹斯(Olympus)眾神的一員,但是他入祠奧林匹斯神山是在荷馬(Homer)之后很久的事情了。[6]23與日神阿波羅比起來,他在希臘神話中的地位無足輕重。然而尼采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酒神所代表的人類對自然和生殖的崇拜,以及酒神精神所象征的對個體化痛苦的超脫——這是一條通向存在之母和萬物核心的道路。正是這一發(fā)現(xiàn)讓尼采對酒神格外青睞,并極具顛覆性地將其與日神并尊,甚至凌駕于日神之上。借助酒神,尼采也顯示出了他對“正統(tǒng)文化”的反叛和對瓦格納的超越。
正因為尼采對酒神精神格外重視,所以他對瓦格納所代表的新酒神藝術抱有極大的期望。他認為瓦格納是歐洲文化復興的領路人,他的音樂和戲劇中隱藏著古希臘文化中的酒神精神,能夠引領德國重新走向輝煌。然而,命運開了一個玩笑,尼采和瓦格納的友誼最終宣告結束。
眾多研究“瓦格納事件”的專家認為,尼、瓦二人決裂的重要原因在于,尼采向來摒棄的基督教精神竟然在瓦格納的最后一部戲劇《帕西法爾》(Parsifal)中有著濃重的體現(xiàn)[9],這令尼采十分憤怒。尼采認為自己一貫是基督教的敵手,從《悲劇的誕生》開始,他就對基督教持強烈的批判態(tài)度。在他看來,基督教既不是日神阿波羅,也不是酒神狄奧尼索斯。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講,基督教是一種虛無主義,它也否定一切美學價值,而這種美學價值恰恰是《悲劇的誕生》一書中承認的唯一價值。[1]80對基督教如此摒棄的尼采,不會允許所謂的基督教精神沾染他心目中的希臘世界與理想藝術。因此,他對瓦格納所顯露出的對基督教道德意識的臣服自然十分不滿。
值得注意的是,瓦格納早期的理論著作透露出他其實也是一個反基督教者。在《藝術與革命》中,瓦格納總體上是站在反基督教的立場上探討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復興的。瓦格納認為古希臘悲劇衰落之后,藝術就被基督教所俘虜,而基督教的本質(zhì)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偽善。這種惡劣的品質(zhì)與藝術糾纏在一起,并且越來越深,嚴重阻礙了藝術展現(xiàn)其自律性的、純潔的美。雖然瓦格納對基督教進行了強烈的譴責,但是從他在《藝術與革命》文末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他對基督教的批判并不徹底,認為其中依舊存在某些積極的因素。[10]他提道:“耶穌向我們表明,我們大家都是長相相似的人類,我們親如兄弟。……因此,讓我們在生活中和生機勃勃的藝術中建立祭壇,以此獻給并長久地紀念人類最重要的兩位導師。耶穌,他為全人類受苦;阿波羅,他把人類提高到充滿歡樂和尊嚴的地位!”[11]這里,瓦格納顯然對耶穌給予了非常正面的評價,認為耶穌具有拯救性,并將耶穌與阿波羅并舉為人類的導師。也正是因為瓦格納批判基督教的不徹底,為他晚年屈從于基督教的道德精神埋下了伏筆。
尼、瓦二人決裂的原因,或許還在于他們的藝術目標并不一致。尼采將悲劇視為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結合的完美藝術作品,他希望通過希臘悲劇和瓦格納的藝術實踐看到新的人類尊嚴的興起。但事實上,瓦格納的戲劇音樂在發(fā)展中已經(jīng)逐步脫離了尼采心中真正的悲劇形式。瓦格納在《未來的藝術作品》中明確提出,他要創(chuàng)造的是一種名叫“整體藝術”的新的藝術形式,它是音樂戲劇的新的統(tǒng)一。在這種藝術形式中,歌詞、戲劇人物與音樂似乎都融化在了一起,留給觀眾的是發(fā)展到極限的感官刺激。然而,倘若一直處在感官享受的精神狀態(tài)中,其后果必然是筋疲力盡、意志喪失。尼采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一點,他鄙棄瓦格納的言行不一——瓦格納一面批評歌劇等現(xiàn)代藝術追求感官刺激,一面卻在他的“整體藝術”實踐中將這一刺激推向極致。因此,尼采在《尼采反對瓦格納》(Nietzsche contra Wagner)中激烈地抨擊瓦格納,指責他的音樂毒害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二人的友誼走到了盡頭。
比較尼、瓦二人的理想與追求,我們可以看到瓦格納似乎對世界抱有“建設”性的樂觀態(tài)度。他提倡日神精神,提倡“整體藝術”,本質(zhì)上是想要借助這兩者構建自己理想中的社會。他期待“耶穌”的拯救,也是因為他希望耶穌能夠幫他實現(xiàn)自己的愿望。而尼采雖然也有著民族復興的理想,但他更多是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的沖突、矛盾與沒落,尤其是晚年的尼采,對世界懷著深深的絕望。因此,二人之間巨大的精神鴻溝,也許是造成他們走向分歧的深層原因。
三、抽象的瓦格納——“瓦格納事件”背后
在“瓦格納事件”發(fā)生之后,瓦格納依舊占據(jù)了尼采生命中極其重要的位置。對于尼采來說,瓦格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極為特殊,“瓦格納”這個名字儼然成為德國精神的象征和代名詞。因此,尼采與瓦格納的分道揚鑣不僅是兩個個體之間的沖突,也是尼采與他心目中的寄托的決裂。
瓦格納之所以能夠成為某種象征,是因為他具有某種代表性和典型意義。首先,瓦格納致力于德國民族復興的理想,代表了當時一批有志之士的集體愿望。這些人包括與瓦格納一起參加德累斯頓五月起義的起義者,也包括大力支持和宣傳瓦格納音樂、理想的“瓦格納派”。其次,瓦格納的音樂及其“整體藝術”的藝術實踐代表了一次德國民族復興的具體嘗試。“整體藝術”其實是以集音樂、舞蹈、戲劇等因素于一身的古希臘藝術為原型而進行的一次再創(chuàng)造。瓦格納試圖通過這種綜合性藝術創(chuàng)造一種日耳曼式的古希臘文化,把德國打造成繼古希臘、羅馬之后的又一個文化強國,從而實現(xiàn)德國的復興。而他的戲劇音樂所展現(xiàn)出來的宏大氣魄也與當時的時代精神相契合,成為德國精神的外在顯現(xiàn)。瓦格納的這種嘗試在當時獲得了熱烈的反響,尤其是在拜羅伊特(Bayreuth)演出《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Der Ring des Nibelungen)之時,當時的德國皇帝威廉一世 (William I)及多國政要和各界代表都出席了該演出,這部戲劇也在歐洲文化界引起了轟動。從這個意義上講,瓦格納從藝術領域進行德國復興的嘗試無疑是一次突破。可以說,瓦格納的名字與德國復興和德國精神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
正是因為瓦格納與德國精神聯(lián)系得如此密切,在尼采眼中,瓦格納已經(jīng)不再僅僅是一個個體、一個特別的音樂家。他褪去了個人身份,成為德國精神的符號和象征。或許可以這樣說,尼采并不迷信瓦格納,他心中牽掛的一直是瓦格納所代表的德國精神。也正是由于這一點,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尼采對瓦格納會表現(xiàn)出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早期尼采推崇瓦格納,是因為他仿佛看到了德國精神的復興,而之后他批判瓦格納,其實就是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德國精神的衰落。在《瓦格納事件》中,尼采認為瓦格納集中體現(xiàn)了一種現(xiàn)代特性,這種特性的背后實際上是日漸墮落的德國精神,而它透過瓦格納“蠻橫、做作又‘清白無辜’”的戲劇音樂顯露出來。尼采在自傳中常常寫道:“我這樣攻擊過瓦格納,確切地說,我攻擊的是我們文化的虛偽和雜種文化的本性。”“瓦格納被德國化了。”[1]14,94此時的“瓦格納”就是德國精神墮落的象征。
尼采與瓦格納之間的“合”與“分”,實則暗示了尼采對德國精神從一開始抱有希望到不斷失望甚至絕望的變化過程。尼采會對瓦格納迎合大眾和基督教的轉變感到無比憤怒,其背后是對德國精神的“怒其不爭”。
結語
作為19世紀末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尼采以其顛覆傳統(tǒng)的思想著稱。而這樣一位人物的一生中,瓦格納的名字占據(jù)了極為重要的地位。從《悲劇的誕生》中,我們看到了二人之間思想的“合”與“分”。從“瓦格納事件”中,又看到了尼采對瓦格納“言行不一”的憤怒,以及對“瓦格納”所象征的德國精神墮落的痛苦和悲哀。但不可否認的是,二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踐行著復興德國精神和歐洲文化的理想,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筆。
注釋
[1][德]尼采.瞧,這個人[M]. 黃敬甫,李柳明譯. 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14 -94.
[2][德]尼采.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M].周國平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8 -164.
[3]“The latter is the lot of the Slave of Industry.”Wagner,Richard. Translated by Ellis,William.Art and Revolution.Blackmask Online,2001,p.14.
[4][德]瓦格納.瓦格納論音樂[M].廖輔叔譯. 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40 -50.
[5]“Thus,too,inspired by Dionysus,the tragic poet saw this glorious god:when,to all the rich elements of spontaneous art,the harvest of the fairest and most human life,he joined the bond of speech,and concentrating them all into one focus,brought forth the highest conceivable form of art — the DRAMA.”Wagner,Richard. Translated by Ellis,William.Art and Revolution. Blackmask Online,2001,p.7.
[6][德]尼采.瓦格納事件:尼采美學文選[M].周國平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23 -66.
[7]“The opera is forestalled of the living heart and lofty purpose of actual drama.”“The opera becomes a chaos of sensuous impressions jostling one another without rhyme or reason.”Wagner,Richard. Translated by Ellis,William.Art and Revolution.Blackmask Online,2001,p.12.
[8]“... found its fullest expression in the god Apollo,the head and national deity of the Hellenic race”“The deeds of gods and men,their sufferings,their delights,as they,—in all solemnity and glee,as eternal rhythm,as everlasting harmony of every motion and of all creation,—lay disclosed in the nature of Apollo himself”. Wagner,Richard.Translated by Ellis,William.Art and Revolution.Blackmask Online,2001,p.7.
[9]鄒建林. 從酒神精神到強力意志——尼采音樂美學思想述評[J]. 中國音樂學,1998(4):81 - 93. 黃茂文,刁笑萌.酒神哲學和音樂靈魂的悲劇之會——瓦格納音樂對尼采思想的影響及“瓦格納事件”芻議[J]. 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12(3):24 -28.
[10]伍維曦. 古典精神與哥特傳奇——瓦格納1850年前后文論中的二元性音樂戲劇觀及其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J].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3(2):15-30,106.
[11]“Thus would Jesus have shown us that we all alike are men and brothers;...Let us therefore erect the altar of the future,in Life as in the living Art,to the two subhimest teachers of mankind:—Jesus,who suffered for all men;and Apollo,who raised them to their joyous dignity!”Wagner,Richard. Translated by Ellis,William.Art and Revolution.Blackmask Online,2001,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