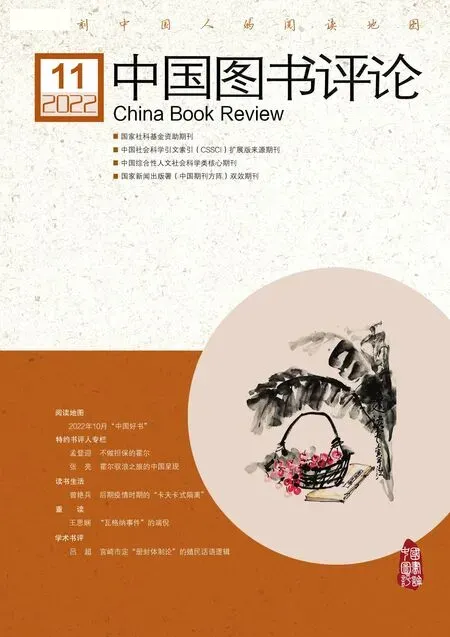出版家年譜的學術意義與編纂思路初探
□段 煜
【導 讀】 出版家年譜是出版家生平史料的整理與呈現, 可豐富中國出版史研究的史料基礎, 但目前所受到的重視度較低, 且欠學理思考。 在編纂出版家年譜時, 應當立足于問題意識和現存史料, 從生活史、思想史、心靈史的層面入手, 構建完整的理論體系。
年譜是一種中國傳統的述史方式,它在體例上結合了紀傳體與編年體兩種形式,以時間順序考訂某人(或某團體)的相關史實,并連綴成冊,形成一部關于譜主生平史料的完整匯集。年譜是人物研究成果的一種呈現方式,在涉及人物研究的學科中,均有著一定的用武之地。在編輯出版學中,編輯家、出版家、發行家等編輯活動相關人員的生平行述與思想觀念均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人物研究無論是在編輯出版實務還是編輯出版史層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史料匯集與出版家形象的塑造
對于編纂年譜的學術意義,陳思和認為:“編制年譜,功在三個方面: 一是詳細考訂譜主家世背景、個人遭際、思想著述、親友關系等史料; 二是對于譜主經歷的歷史事件的深入研究; 三是對其人其書的整體研究的推進。”[1]這一論述強調了年譜在研究資料梳理、歷史本末研究和人物整體研究三個層面的作用。結合出版史學科的特殊性,可在陳思和思路的基礎上略做延伸,將出版家年譜編纂的學術意義歸結為史料的匯集與出版家形象的塑造,具體可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出版家年譜具有史料整理與匯編的屬性,能夠為編輯出版學和編輯出版史研究提供資料基礎。
正如陳思和所言,編制年譜需要對譜主現存的生平史料進行仔細而全面的考訂。考訂的過程既是匯集整理、尋找新史料的過程,也是訂正資料中的訛誤、去偽存真的過程。可以說,一次年譜的編纂,就是一次針對譜主史料的全面更新與整理。如《張元濟年譜》對于1928年張元濟赴日訪書的資料知之甚少,《張元濟年譜長編》在原有資料的基礎上,根據在上海市檔案館發現的三卷老商務印書館檔案中的往來書信,更加清晰地勾勒出當時張元濟與日方往來談判的過程,使得相關資料得到了豐富。[2]
具體到編輯出版學領域,目前整理的編輯出版史料中,恰恰缺乏以人物為線索的史料梳理成果。如張靜廬輯注的《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之《中國現代出版史料》(共甲、乙、丙三編),收錄的內容主要包括重要刊物的發刊詞、政府關于出版的法令、一些重要出版團體的簡要介紹; 宋原放主編的《中國出版史料》收錄的資料大多是重要刊物的發刊詞、終刊詞,以及各個政府關于出版管理的法律、規定。而專門研究出版史的期刊《出版史料》與《中國出版史研究》囿于單篇文章篇幅的限制,對于人物史料的梳理多呈片段化、專題化的特點,整體性和條理性并不強。
因此,在以人物為線索的史料梳理相對薄弱的研究現狀下,年譜在編輯出版史的研究中,可以發揮綴連史料,完整地展現重要出版家生平的作用,從而彌補闕漏,完善史料體系,為出版史中的人物研究和其他相關研究提供更加翔實和完整的史料集。
第二,年譜便于對出版家進行整體和全方位研究,有利于完善編輯出版史的研究結構。
在中國出版史的研究體系中,人物研究在較長時期內一直沒有得到其應有的地位。戴文葆自1986年1月連載至1990年7月發表在《出版工作》的“歷代編輯家列傳”專欄是較早的成體系的人物研究,共42 期,涉及編輯家36 人。在張召奎的《中國出版史概要》,宋原放、李白堅的《中國出版史》,肖東發等的《中國編輯出版史》等關于出版史的早期著作中,出版家均處于出版物、出版機構、出版技術等課題的附庸地位,宋原放、李白堅著作中的第四章第四節“出版機構與出版家”是唯一單獨成節的篇章,此節也僅僅用2 頁的篇幅對毛晉進行了較為系統的介紹。
人物研究直到21世紀初才慢慢得到出版史研究者的重視,如黃鎮偉《中國編輯出版史》對孔子、司馬遷、劉向劉歆父子的編輯活動與編輯思想開辟專節加以介紹; 吳永貴主編的《中國出版史·近代卷》第五章專門設置了“民國重要出版人物”,在其后的《中國出版通史》八卷本中,各卷均開辟專章,對各個時代的出版家進行了系統的介紹。由國家出版基金資助的“中國出版家叢書”,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叢書計劃推出50 余種,截至2020年10月已出版20 種。叢書的出版目的在于“第一次規模化地為這個群體(出版家——作者注)中的杰出者系列立傳,從一個人到一群人的出版事功中,折射出近代以降出版業的俯仰變遷,同時見證著出版參與時代文化思想締構及其背后深廣的社會歷史內容”[3]。
出版家傳記的成規模出版,標志著出版史中的人物研究更加深入與系統,與傳記相比,年譜具有史料翔實、注重細節的優點,更能夠體現客觀的研究視角,避免過于感性化。與此同時,對于入譜資料的選擇也能夠表現出作者的史識及其對于譜主的態度。胡適在《章實齋先生年譜》的序言中將年譜視為“中國傳記體的一大進化”[4]。一部具有學術意義的年譜,不僅應當是一部翔實的人物史料匯編,還應通過資料的選取、詳略的安排、注釋的撰寫等手段,用史料說話,展現出作者對于譜主的認識與評價,使出版家譜主的形象更加整體化、系統化,從而進一步提升人物研究在編輯出版史研究中的地位,讓編輯出版史的研究結構更加合理與完善。
第三,編纂出版家年譜也能夠對改善編輯出版史的研究風氣有所貢獻。
由上文可知,在目前的編輯出版史研究中,人物研究在體量和深度上都遠不如對出版物、出版機構、出版政策的研究,對于“事”的重視程度要相對高于“人”。但編輯出版活動中,無論是內容的制作,還是對內容的編輯與傳播,都要立足于人的活動; 編輯出版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理應對出版活動中的“人”予以足夠的重視。年譜立足于史實的鉤沉考訂,往往需要重視大量細節,力求完整地搜集譜主一生中的點點滴滴。這種治學方式體現出很強的人本思想,有助于提升出版史研究中的人文關懷。
此外,年譜講究用資料說話,作者在編寫譜文時必須有足夠扎實的資料作為佐證,不說無根據之話。這種嚴謹的研究精神有助于使出版史的研究更加客觀、清晰與可靠。在中國的出版史尤其是近現代出版史中,出版機構具有企業的性質,不同出版機構所代表的不僅是不同的出版觀念,也代表著不同的利益群體。出版機構之間明爭暗斗,出版家之間也難免有分分合合。當事人在提供一手史料時難免會由于群體和派系的原因出現有失公允的評價,后世的研究者既有可能以訛傳訛,也有可能因為與資料提供者之間的人際往來而對資料進行有意的遮蔽。比起親歷者較多、較容易對照印證的具體事件而言,這些有失公允的資料更容易出現在對人物的評價中。年譜以史料說話,首先就能夠避免研究者出于主觀臆斷的任意評價。年譜編纂過程中對于史料的匯集與比對,也能夠最大限度地鑒別材料的真偽,從而最大限度地讓出版史研究盡可能避免隨意性,遠離有意的遮蔽與無意的誤讀,更加被人所認可。
二、成果缺位、學科意識的淡漠與理論思考的乏力
從現有成果來看,出版家年譜在成果數量、成果的學科意識方面都仍有不足,理論性的思考也較為乏力,存在著明顯的改進空間。
探討出版家年譜的研究現狀之前,需要對出版家的具體身份有所界定。以張元濟、王云五、陸費逵等為代表的一類出版家,其精力主要集中在對稿件的審查、編輯和對出版社的經營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大都體現在出版行業本身——如張元濟之于《百衲本二十四史》,王云五之于四角號碼檢字法等——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則處在一個相對次要的地位。除此之外,還有一類可以被稱為“兼職出版家”的出版者,他們多是在諸如文學、歷史、哲學等出版以外的專業領域有所專長,并出于編印作品、傳播主張的考量而參與出版行業。如魯迅曾為出版自己的作品和提攜年輕人而創辦過“三閑書屋”“野草書屋”等多個小型出版機構,近代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也均設有出版部門。這兩類出版家從事出版工作的側重點不同,年譜編纂現狀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職業出版家年譜的問題主要呈現為成果數量少、規模小,缺少與出版家的貢獻與地位相稱的著作。出版家年譜的編纂工作目前還處于初級階段。目前已經有專著規模的年譜僅有《張元濟年譜》[5]、《張元濟年譜長編》[6],《鄒韜奮年譜》[7]、《鄒韜奮年譜長編》[8],以及《陸費伯鴻先生年譜》[9]、《王云五先生年譜初稿》(未在中國大陸正式出版)[10]。在2010年啟動的“近代重要人物年譜長編”工程中,除張元濟和鄒韜奮之外,《舒新城年譜長編》也在規劃之列,但尚未出版。[11]
除上述著作外,出版家的年譜還散見于一些學術刊物和出版家的傳記、紀念集中,如王震編《陸費逵年譜》; 趙普光、方久月編《宋云彬年譜節選 (1949—1965)》; 周國偉編《趙家璧年譜》[12]; 前文提到的“中國出版家”系列叢書中,已出版的20 種也均在書末附錄了傳主的年譜。這些年譜篇幅較短,對于一些具體和細微的史實往往掛一漏萬,且存在著一定的錯漏與訛誤。如趙家璧的回憶文章《回憶魯迅與連環圖畫》在《趙家璧先生紀念集》與《中國出版家: 趙家璧》所附年譜中均將題目誤收為“魯迅與連環畫”。這些短篇年譜給初學者和普通讀者用于入門尚可,若以學術研究為目的則遠遠不夠。總體來說,職業出版家年譜成果的數量和體量不足,成功范例較少,對資料的收集、整理和訂正工作均亟待展開。
與職業出版家年譜數量稀少的現狀不同,兼職出版家年譜的成果相對較多。但是,這些成果普遍缺乏編輯出版學的意識,未能很好地體現出譜主的出版家身份,無法在年譜中反映出譜主作為出版家這一身份的全貌。
《魯迅年譜》中對魯迅編纂《北平箋譜》相關史實的記錄情況在此可作為例證。《北平箋譜》是魯迅與鄭振鐸在1933年合編的一部箋譜,魯迅在日記和與鄭的通信中,提到了很多關于箋譜出版的具體構想和方向性思路。這些內容對于研究魯迅的出版實踐、出版思想以及中國近代藝術出版史具有重要意義。魯迅在1933年2月5日致鄭振鐸的信是《北平箋譜》編輯工作的開端,《魯迅年譜》收錄了這封信,并將《北平箋譜》的總體情況進行了大致介紹。但是對于箋譜編纂過程中的內容,年譜的譜文則存在大量遺漏。如1933年10月11日,魯迅致信鄭振鐸,對箋譜的紙張、版式等提出建議。這封信在年譜中并未收錄。又如,魯迅在1934年2月24日致鄭振鐸信中提道:“日前已獲惠函并《北平箋譜》提單,已于昨日取得三十八部,重行展閱,覺得實也不惡,此番成績,頗在豫想之上也。”[13]而《魯迅年譜》在當日的譜文中,只收錄了信尾“新年新事,是查禁書籍百四十余種,書店老板,無不惶惶奔走,繼續著拜年一般之忙碌也”[14]一句,對于《北平箋譜》的編纂情況則只字未提。
《魯迅年譜》開始編纂時,魯迅的書信和日記均已公開出版,不存在資料缺失的問題。年譜在“編輯說明”中提到了對于書信和日記的收錄原則并非每則必錄,而是“有選擇地入譜”[15]。由此可見,上述關于魯迅與出版的材料是被年譜編纂者“有選擇地”略去了。而這種省略使得《魯迅年譜》在呈現作為出版者的魯迅形象時顯得缺乏總體性與立體性,未能完整地展現出魯迅作為出版家的一個側面。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完全按照出版家的視角編纂兼職出版家的年譜是既無必要也不現實的,合理的思路是讓具有出版視野的學者參與到年譜的編纂工作中來。畢竟對于魯迅、巴金、葉圣陶等多方面發展的文化學者而言,出版家雖然只是他們的兼職身份,但在他們的生活中也有著重要的地位,故而在年譜中理應有所提及。隨著年譜編纂的深入和年譜意識在編輯出版學領域的發展,編輯出版史的研究者理應參與到兼職出版家年譜的修訂工作中,為展現一個更加全面的文化學者貢獻力量。
從學理層面來看,年譜憑借其獨特的述史優勢,在近年來愈加受到多個人文學科的重視與推崇。如李道新關于電影人年譜的研究[16],李雪、李立超等對于當代文學家年譜編纂的思考[17]等。但具體到出版史研究領域,對于年譜的學術意義和理論價值,尚欠缺整體層面的思考。
出版家年譜的編輯體例、重點內容、史料搜尋和運用的方式,都是出版家年譜能夠與其他領域相區分的點。具體來說,古代出版家與近現代出版家年譜的側重點如何區分、史料搜集方式有怎樣的區別;在編輯體例上如何處理人物的日常活動與出版活動的聯動; 在譜文寫作中如何處理出版者與出版物的關系,做到既完整地展現譜主的代表性出版貢獻,又不偏離人物本身而使人物變為出版事件和出版物的附庸: 都是需要在編纂工作中加以解決的理論性問題。出版史研究對于年譜意識的缺失,不僅體現在成果較少,也表現在缺乏對于如何編纂出版家年譜而進行的理論思考。理論思考的缺失與實踐成果的稀少在一定程度上互為因果,均亟待解決。
三、展望與思考: 問題意識導向下的生活史、思想史與心靈史
對于出版家年譜編纂的思考可以轉化為另一個問題,即出版家的年譜應當怎樣編,在編纂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問題。出版家年譜的編纂涉及對于多個方面關系的處理,編纂過程中所涉及的問題也是多方位、多維度的。
第一,要堅持以學術價值和問題意識為導向。
這個問題主要體現在選題階段。對譜主的選擇是衡量一部年譜學術價值的前提。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出版工作雖然并非社會上的主流活動,但是從事過出版工作的人也如恒河沙數一般,在史書上留有姓名的出版家也是浩如煙海的。為所有的出版家都編纂翔實的大部頭年譜,在學理上并無必要,在實踐中也頗有難度。因此,需要以學術價值和問題意識為導向,從必要性和可能性兩個方面衡量是否有必要為一個出版家編纂年譜。
具體而言,值得編纂年譜的出版家應當有以下幾方面的特質。首先,譜主應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從事出版工作,并在工作中處于相對核心、具有一定參與度和自主權的地位。譜主以出版家的身份入史,年譜所要呈現的也應是譜主究竟是為何從事出版、怎樣走上出版的道路,又在出版行業中做出了怎樣的成就。其次,譜主應當在出版活動中形成了自己的工作風格、行事特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值得為后人所學習與紀念。最后,譜主應留存有足夠窺見其出版活動面貌的可靠史料,能夠為考訂史實提供足夠的依據和線索。出版家歷來被視為“為他人做嫁衣”的角色,很多關于出版家自身的史料則往往付諸闕如,這既給年譜的編纂帶來了困難,也從側面印證了為出版家編纂年譜的必要性。
第二,正確認識出版家年譜的定位與作用。
年譜是對譜主歷史的整理,也是學者對于譜主生平的研究成果。一部優秀的出版家年譜,應當處理好史料與文本的關系,除基本的史料作用外,還應當具備生活史、思想史、心靈史三個層面的特點。
生活史是當今國際學術界一種較為前沿的研究視角,范軍、歐陽敏在將生活史視角引入出版史時認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出版人物的日常物質生活,包括娛樂休閑活動在內的精神交往活動,以及與親朋好友間的人際往來。[18]其研究目的在于希望“通過研究出版人的生活史,將出版人從龐大的社會結構中凸顯出來,彰顯出版人的主體性”[19]。這里所提出的對出版人主體性的彰顯,正是出版家年譜所要進行的工作之一,而年譜立足于史料和細節的特性,不僅能夠在研究出版生活史的過程中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還可以使出版生活史的研究更加系統,從而更好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所謂思想史,即年譜中應當通過對譜主生平史料的整理,表現出譜主對于出版行業、出版業務的思索與考量。這些思考既體現在譜主的行為和著作之中,又是表層史料之外較為深層次的內容。不使年譜流于簡單的史料匯編,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史料的選取和應用中,將那些最能夠表現譜主深層次思想的內容整理并呈現出來,從而增加內容層面的厚度,為出版史研究的整體做出貢獻。
所謂心靈史,就是對譜主如何成長為一個有成就的出版家的思想變遷與心路歷程的整理與呈現。這些思想上的閃光點往往是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他自己的重要因素,而在以事件和出版物為核心的研究中又相對容易被忽視。因此,一部成功的年譜,理應捕捉住譜主在思想方面的閃光點,既是為前人樹碑立傳,又是為后人提供示范與借鑒。
總而言之,通過扎實考證、系統搜集,將出版家的生平史料匯為一編的出版家年譜,對出版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人物的研究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在現有的史料和出版家傳記研究的基礎上,將中國出版史上的重要出版家作為譜主,形成網狀的出版家年譜體系,將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和完善中國出版史的史料類型、研究體系和述史結構,使中國出版史研究向著系統化、深度化的方向不斷邁進。
注釋
[1]陳思和. 學術年譜總序[J]. 東吳學術,2014(5):134.
[2]張人鳳,柳和城. 張元濟年譜長編·后記[J].出版史料,2012(1):72.
[3]“中國出版家叢書”編輯委員會.出版說明[A]. 中國出版家:趙家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
[4]胡適,姚名達. 章實齋先生年譜[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2 -3.
[5]張樹年. 張元濟年譜[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6]張人鳳,柳和城.張元濟年譜長編[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
[7]復旦大學新聞系研究室. 鄒韜奮年譜[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2.
[8]鄒嘉驪.鄒韜奮年譜長編[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
[9]陸費伯鴻先生年譜[M].臺北:中華書局,1977.
[10]王壽南. 王云五先生年譜初稿[M].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
[11]馮勤.近代重要人物年譜長編出版工程啟動[J].近代中國,2010(2):478.
[12]上海魯迅紀念館.趙家璧先生紀念集[M].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332 -359.
[13]魯訊. 致鄭振鐸[A]. 魯迅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32.
[14]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 魯迅年譜(第四卷)[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17.
[15]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 編寫說明[A].魯迅年譜(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1 -2.
[16]李道新.影人年譜與中國電影史研究[J]. 當代電影,2019(1):92 -98;數字人文、影人年譜與電影研究新路徑[J].電影藝術,2020(5):27 -35.
[17]李雪.當代作家年譜與當代作家研究[J].文藝爭鳴,2019(12):13 -18;李立超.論中國當代作家年譜編寫的體例問題——以余華為個案[J]. 東吳學術,2018(3):89 -97.
[18]范軍,歐陽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學研究新視閾[J]. 現代出版,2017(2):62.
[19]范軍,歐陽敏. 論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的雙重特質[J]. 編輯之友,202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