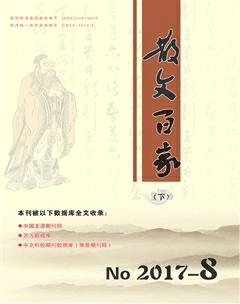一切理想從現(xiàn)實(shí)出發(fā)
丁博涵
每個(gè)人在孩提時(shí)期都有一個(gè)遠(yuǎn)大的理想,長(zhǎng)大了要做科學(xué)家、文學(xué)家、宇航員……后來,有的人實(shí)現(xiàn)了自己的理想,更多的人則是平凡地度過一生。在我看來:任何天馬行空的理想最終只不過是幻影,一切理想還需從實(shí)際出發(fā)。
理想從實(shí)際出發(fā)首先是從實(shí)際考慮,選定一個(gè)現(xiàn)實(shí)的目標(biāo)。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不可否認(rèn)的是,把科學(xué)家、宇航員作為我們的理想,的確是目標(biāo)遠(yuǎn)大。但是在樹立理想前,我們應(yīng)該認(rèn)真審視自己,從自身實(shí)際出發(fā),看看自己有沒有相關(guān)的特長(zhǎng)或興趣,從而論證樹立此理想的可行性。一旦理想立錯(cuò)了,后面再怎么努力,也很難實(shí)現(xiàn)。
理想樹立的另一個(gè)方面,是樹立細(xì)節(jié)化的理想。有人說他要當(dāng)文學(xué)家,那他到底是要研究語文還是英文?到底是要當(dāng)作家還是翻譯家?過于泛泛會(huì)使理想趨于空洞化,面對(duì)高高在上的理想,人們會(huì)失去追求它的動(dòng)力,這時(shí)理想就會(huì)變成一個(gè)一觸即破的泡沫。因此,在樹立理想時(shí)我們要注重細(xì)節(jié),規(guī)劃好自己的專業(yè),認(rèn)準(zhǔn)自己所要從事的具體領(lǐng)域。
理想從實(shí)際出發(fā)的關(guān)鍵在于一切從點(diǎn)滴小事做起。記得流沙河的《理想》一文中有這樣一句話:“理想是鬧鐘,打破你的黃金夢(mèng);理想是肥皂,洗濯你的自私心。理想既是一種獲得,理想也是一種犧牲”。理想樹立了,還要付之于行動(dòng)。那些實(shí)現(xiàn)了自己理想的人,絕對(duì)是敢于為了自己的理想而付出努力的人,他們能夠去除自己的私欲,不受誘惑侵?jǐn)_,全身心地投入到為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理想所做的努力中。越努力,越幸運(yùn)。只要肯努力,你就會(huì)離理想更進(jìn)一步。就算最后沒有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理想,只要努力了就不后悔。而那些整天對(duì)著理想說著看似完美的空話的人,終究不會(huì)實(shí)現(xiàn)理想,到頭來,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chǎng)空。
一切理想從實(shí)際出發(fā),簡(jiǎn)而言之,就是要求我們以自身實(shí)際情況制定具體化的理想,之后再?gòu)默F(xiàn)實(shí)出發(fā),去追求理想。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陽(yáng)正晴,出發(fā)吧!
指導(dǎo)老師:趙艷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