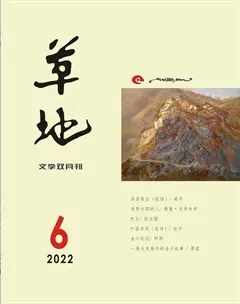一襲長發展開的金川敘事
一個作家的寫作發生質變,不亞于一場成功的整容術,甚至是換頭手術。可是,這個作家在一條足可以繼續精耕細作的道路上,不滿意了,堅持要變回那個原來的自己。
記得今年年初的一個晚上,盧一萍、巴桑、龐驚濤、韓玲和我在成都錦江邊喝茶。韓玲講到了自己正在寫作的歷史題材小說《阿扣》。阿扣在嘉絨藏語里是掌上明珠或心肝寶貝之意。那是一個被萬千目光環繞的藏族美女,大金川土司莎羅奔的掌上明珠。史料上說,莎羅奔為擴充實力和疆地,先后將她許配于丹巴革什扎土司、康定明正土司,后又嫁小金川土司澤旺為妻,為此三家火拼,引發了嘉絨藏區十八土司之間藏民族部落間的激烈紛爭與仇殺,騷亂如青藏高原起伏的石濤,乾隆帝為維護社稷安穩,卷入了這場戰爭……阿扣為了愛情,在習俗和地域文化的影響下,游弋于各權勢之間,最終被推上風口浪尖,成為箭垛式人物。這個后來被《清朝野史》稱之為“妖姬”的阿扣,最后香消玉殞。
韓玲沒有在歷史的記錄下亦步亦趨,而是根據這條歷史之線,刪繁就簡,展開了歷史情境中的想象,她用阿扣與良爾吉敢愛敢恨的冰雪一生,去穿越、去托舉、去延宕三百年前的大小金川之役,用一個女人勇往直前追尋愛情,來展示一場空前的高原戰事,這就是小說《阿扣》的旨歸。我靜靜聽著韓玲喘氣的敘述,她吐出的一道道白氣是高地上的氤氳,而成都的夜空雨絲飛舞,總有一種若隱若現的憂傷,那是一種散發著香氣的憂傷,而憂傷似乎是雨的精靈,也是大雪的精靈。
在我們談話間,一只白鷺在鋪滿漣漪的水面大叫起來,就像濯錦者用力過猛發出的裂帛之聲。靜美的錦江本來在敘事,為何在撕裂之際會發出干燥的、粗糲的嚎叫,一直是未解之謎。
韓玲轉過頭來對我說:“對于行事丑惡的人,阿扣幾乎從來不掩飾她的厭惡之情,這讓她吃了不少的虧,也有不少好心人善意地提醒她,該把自己黑白分明外露情緒收一收,但阿扣不想把自己的心思和精力浪費到不必要的人身上,連表象的維和也不屑……所以,她就像這只白鷺,用凄厲的叫聲,打破了全部假象!”
如果說振翮向外飛翔,是韓玲的散文正在進行的言路,那么向內心坍縮,在歷史的縫隙間竭力撐開一片女人的天空,則是韓玲小說的向度。所有的刀光劍戟,所有的權力與面子,所有的冠冕堂皇與蠅營狗茍,都被女人的愛憎予以清潔、予以厘定、予以試錯,并賦予了一層神山投射而來的光暈。好在三百年前的金川,那的確是一個靈光從未消逝的時代。
女人寫一個女人很難寫好。一個金川女人寫一個金川女人,顯然韓玲是在嘗試有難度的寫作。她們之間隔著三百年的風霜雨雪。但這一切,似乎伸手可及。韓玲說:“我感覺阿扣經常在給我說話!講那些寥寥幾行刻在石頭上的經文背后的愛山情海……有一天,我看見一地的雪蓮花。奇妙的是,散發著梅花的香氣。”
寫過著名的非虛構小說《騙子》的作家塞爾卡斯曾經說:“我個人也認為文學或者小說本身就應該是虛構的,但是我又覺得現代小說概念開始以后,文學最首要的任務或者文學最大的美德是講述的自由。”
在小說里實現“講述的自由”已經夠難了。比如余華承認“卡夫卡使我的寫作自由”。作家固然有生存的荒謬,但終于擁有想象的自由,這已十分不易。以此看待阿扣,這個人物最大的現實悖論在于:從屬權力就是一路鮮花,否則就一無所有。但反抗者之所以反抗,在于她敢于放棄唾手可得的,不顧一切地朝向光明與自由。阿扣最終沒有得到她渴望的,但她的容顏恰恰因為她的失敗,獲得了美麗之外的另一種不可逼視的神韻。所以,我以為在此之上,更有一種“為了自由的講述”。如果韓玲一旦確立了這個向度,那么歷史的、戰爭的、權力的、愛情的、親情的、民俗的故事等等,才可以從容地得以落地生根。
韓玲對于《阿扣》的講述是謹慎的,她最后采用的方式是:“一紙杯喝完以后,我又悄悄起身為自己添了第二杯,我想我能喝三杯的,后來是不是喝了三杯呢,我就忘記了。再后來,我獨自走出了巖洞,至今我都記得那天晚上的月亮好大好圓好亮,原諒我詞庫的匱乏吧,當我只能用這樣的詞語描繪當晚的月亮時。我當時唯一的念頭是,這樣的月光不用來談戀愛真是可惜了,又落俗套了吧,誰說白月光一定適合愛情,撞見鬼也是常有的事。比方說我,不是在三千尺的瀑布下遇見了頭發比月光還白的老奶奶,她一句,你來吶。把我的酒都嚇醒了一半,我搖搖頭,確定自己并沒有看錯,是的,瀑布下的石頭上一位老奶奶安靜地打坐,石大如席,老奶奶嘟嘟嘴示意我坐下,并讓我喝她早準備好的酒……”
故事在老奶奶的話語與三百年的跌宕戰事中從容轉身,一個又一個的懸念得以鋪開,而一個又一個的謎團又得到了解決,但老人又拋出了另外一個謎面之下的謎團……
我意識到,只有一種作家,敢于去寫他們不是了然于胸的題材,由此散發出尖銳的香。恰恰因為不知道事情的底牌而迂回,這本身就足夠迷人了。但他們在寫作過程中,與陌生的東西耳鬢廝磨,最后與這些事物達成了高度的默契與相知。在這樣的作品里,與其說作家以歷史的合理性在推演情節,不如說他們藏匿了一半的理解與表達,而付之于沉默與空缺。
在我看來,《阿扣》是一部成功的歷史非虛構小說。
作為一位較為成熟的散文家,韓玲所具有的細膩觀察與細節描述功夫,在《阿扣》里得到了極大的彰顯。她對大小金川一草一木、民俗風情非常熟悉,加上她多次的田野考察,她基本能夠復原那個三百年前的時空。而她用情事“反寫”歷史宏大敘事的方式,展示了韓玲在逸出散文畛域的遼闊想象空域。這就是說,整部作品表現出來的歷史,肯定不能拘泥傳統意義上的唯一性和客觀真實性,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明顯虛構化特點,是新歷史主義批評家眼中的“新”歷史或者阿扣文學化的大小金川史。在這樣的歷史表征中,歷史事實和虛構元素被有機地混合在一起,歷史與文學、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已經“打成一片”。
韓玲的情事“反寫”策略,目的是使歷史敘事非自然化,使自己的虛構意識得以凸顯,雖然作者使用這些策略的本意,就是強調敘事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畢竟歷史并非鐵板一塊,更多的時候它是以多元性、柔軟性呈現出來的,《阿扣》對人們心安理得地接受鐵板一塊歷史事實的現象,進行了強力顛覆。也使得阿扣這個箭垛式的人物,為我們留下了孔雀回首的容顏與身姿。
在《阿扣》的結尾,如何看待始作俑者莎羅奔?硝煙散去,阿扣已入土,但石頭在某個時候會開口說話!韓玲寫道:土壤早已成了紅褐色,鮮血凝固,天空的陰霾無法散開,不久前還充斥在這里的廝殺聲、呼喊聲、槍炮聲消失了,卻讓此時的寂靜顯得無比猙獰。
一切都消失了,一切!
撕心裂肺的痛苦如潮水般把莎羅奔緊緊包圍,他佝僂著背,衣衫不整。阿扣的臉、母親的臉、央金的臉、許多士兵的臉交替在他眼前出現,致使他完全不敢閉眼,一閉上眼,一生的罪惡,一幀一幀浮現,割破時光,跌跌撞撞地撲面而來。
莎羅奔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他跪在自家家廟前懺悔,后悔自己任憑自己的貪戀膨脹而不加約束才致今天的生靈涂炭,他覺得自己罪孽深重,連佛教最戒的貪、嗔、癡、慢、疑,他一個關也過不了。他把官寨一應事務全部交給侄子郎卡打理,他自己則形單影只地整日坐在經堂禮佛,人很快瘦骨嶙峋,凹陷的眼窩常窩著一汪濁淚,他身邊只留下一個貼身下人,終其余生,并不見任何人。
“不知原諒什么,誠覺世事盡可原諒。”(木心之語),但僅有溫情與原諒,可能還是歷史給予我們的訓誡。所以,我佩服那些不原諒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