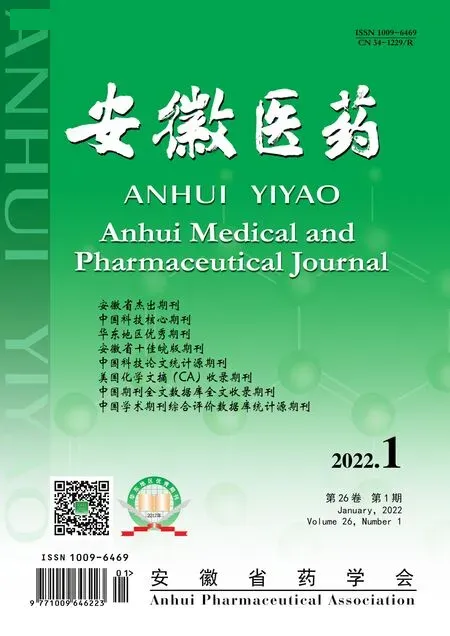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及低氧誘導因子-1α與糖尿病合并動脈狹窄病人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的關系研究
馮自波,楊文波,祝友鵬,張靜
糖尿病作為一種以胰島素分泌、胰島素作用或兩者共同存在缺陷而誘發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質、水和電解質等代謝紊亂及慢性血糖升高為主要特征的內分泌性疾病,可引起全身動脈粥樣硬化,造成動脈不同程度狹窄或閉塞而致相應器官和組織出現供血障礙[1-2]。因此重建動脈、恢復血流是其主要治療原則,而支架植入憑借其適應證廣泛、風險低和并發癥少等優勢被視為其首選方案[3-4]。但受到支架植入刺激,病人血管內膜組織會過度增生、平滑肌細胞能產生移行效應[5];再加上糖尿病病人血糖因素影響,動脈狹窄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率相對非糖尿病病人明顯升高,對植入效果及病人術后生活質量造成一定影響[6]。加強糖尿病病人動脈狹窄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機制探討和防控,利于降低再狹窄率、改善病人預后。資料顯示目前關于該方面研究主要以炎癥反應為主,指標檢測側重白細胞介素(IL)和C反應蛋白(CRP)水平探討[7];但并不能完全和徹底闡明糖尿病動脈支架植入后再狹窄發生機制,不利于再狹窄全面防控。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和低氧誘導因子-1α(HIF-1α)作為當前研究較多的熱點,主要集中于視網膜病變、腫瘤、糖尿病腎病等方面[8]。本研究旨在分析VEGF和HIF-1α水平變化與術后再狹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資料概況:選取2016年9月至2018年2月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梨園醫院糖尿病合并動脈狹窄行動脈支架植入治療病人188例,男124例,女64例,年齡范圍51~72歲,中位年齡62歲,年齡(56.4±7.1)歲,糖尿病病程范圍11~34年,中位病程19年,病程(18.2±5.2)年,病變血管中股動脈、肱動脈等主干動脈76例,脛后動脈、腓腸動脈等分支動脈112例,其中152例植入1個支架,36例植入2個或以上支架,植入支架管徑范圍3~16 mm,管徑(4.2±1.1)mm。其中合并高血壓136例。所有病人或其近親屬知情同意,且本研究符合《世界醫學協會赫爾辛基宣言》相關要求。
納入標準:(1)符合2型糖尿病診斷標準[9]和動脈狹窄支架植入適應證[10];(2)預計生存期>6個月且能堅持隨訪半年;(3)植入支架均為強生Cordis自膨式支架;(4)術后規律進行抗凝、抗血小板及降脂治療。排除標準:(1)嚴重肝腎功能不全;(2)合并甲狀腺功能異常、糖尿病酮癥酸中毒等其他內分泌疾病;(3)惡性腫瘤及全身免疫性疾病。研究分組:病人入選后規律隨訪,按是否發生動脈再狹窄[10],分為再狹窄組(n=98);未再狹窄組(n=90),兩組病人均為同一手術組實施手術,術后隨訪期間均規律降糖、降脂、抗血小板等治療。治療干預措施等基線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指標檢測方法標本來源及采集:病人治療前抽取空腹抽取病人外周靜脈血液6 mL,置于含有肝素的抗凝采血管內,作為相應標本。其中2 mL送檢行血脂、CRP及血糖、HbA1c檢查,4 mL標本采用上海安亭公司提供的飛鴿TDL-5A臺式離心機,以3 000 r∕min速度離心15 min,取得上清液,即刻送檢。
VEGF、HIF-1α水平檢測:采用雙抗體夾心-酶聯免疫吸附法(ELISA法)測定,試劑盒分別由武漢欣博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西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CRP水平檢測:采用i-CHROMA Reader免疫熒光分析儀測定,Bodi Tech Med IncorooratedC反應蛋白檢測試劑盒由北京凱諾春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3 相關資料調查記錄病人一般資料、病情及治療情況,包括性別、年齡、吸氧史、糖尿病病程等病人基本資料、動脈病變程度、類型、支架植入情況,血糖、血脂及VEGF、HIF-1α等指標檢測情況。
相關資料情況:188例病人空腹血糖(FPG)范圍為5.2~11.6 mmol∕L,FPG(6.7±1.4)mmol∕L,糖化血紅蛋 白(HbA1c)范 圍 為5.4%~9.6%,HbA1c(7.2±1.3)%,總膽固醇(TC)范圍為3.1~8.4 mmol∕L,TC(5.7±1.3)mmol∕L,三酰甘油(TG)范圍為3.9~10.2 mmol∕L,TG(6.7±1.6)mmol∕L,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sLDLc)范 圍 為2.1~7.2 mmol∕L,sLDLc(3.4±0.7)mmol∕L,CRP范圍為2.9~42.6 mg∕L,CRP(11.6±4.2)mmol∕L,VEGF范 圍 為57.4~204.2 pg∕mL,VEGF(106.4±21.4)pg∕mL,HIF-1α范圍為142~326 ng∕mL,HIF-1α(217.4±26.9)ng∕mL。
1.4 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24.0軟件。計數資料用例(%)表示,單因素分析采用χ2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VEGF、HIF-1α、CRP對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的評估效能分析采用ROC曲線分析法,指標間相關性分析采用Pearson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動脈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動脈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相關因素分析∕例
再狹窄組和未再狹窄組相比:血清HbA1c、TC、VEGF、HIF-1α、sLDLc、CRP、病變血管類型,支架植入長度、支架數目及支架直徑構成情況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動脈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結果將支架植入后血管再狹窄作為因變量,HbA1c、TC、VEGF、HIF-1α、sLDLc、CRP、病變血管類型,支架植入長度等相關因素作為自變量,建立非條件logistic回歸模型。各變量賦值:HbA1c<7.2%=0,≥7.2%=1;TC<5.7 mmol∕L=0,≥5.7 mmol∕L=1;VEGF<106.4 pg∕mL=0,≥106.4 pg∕mL=1;HIF-1α<217.4 ng∕mL=0,≥217.4 ng∕mL=1;sLDLc<3.4 mmol∕L=0,≥3.4 mmol∕L=1;CRP<11.6 mg∕L=0,≥11.6 mg∕L=1;血管病變類型,主干動脈=0,分支動脈=1;支架長度,<3.4 cm=0,≥3.4 cm=1支架植入數目,1個=0,2個及以上=1;支架直徑≥4.2 mm=0,<4.2 mm=1。回歸過程采用逐步后退法。分析結果顯示,VEGF、HIF-1α、HbAH1c、CRP水平是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的風險因素,支架直徑是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的保護性因素(P<0.05)。見表2。

表2 動脈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的獨立危險因素分析結果
2.3 VEGF、HIF-1α和CRP對糖尿病合并動脈狹窄病人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評估效能的ROC分析結果以再狹窄組(n=98)為陽性樣本,以未再狹窄組(n=90)為陰性樣本,建立ROC曲線評估模型。各指標均參考臨床實踐劃分成若干個組段,再以軟件擬合ROC曲線讀取約登指數最大值點,對應計算理論閾值和各項參數。并按實測樣本計算敏感度、特異度、準確度。結果:VEGF、HIF-1α、CRP評定糖尿病合并動脈狹窄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的ROC-AUC(95%CI)分別為0.665(0.412~0.916)、0.761(0.552~0.971)、0.636(0.323~0.944)。見圖1及表3。

表3 VEGF、HIF-1α和CRP評定糖尿病合并動脈狹窄病人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ROC分析結果

圖1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低氧誘導因子-1α(HIF-1α)和C反應蛋白(CRP)評定糖尿病合并動脈狹窄病人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ROC分析曲線
2.4 VEGF、HIF-1α與CRP水平相關性分析經Pearson相關分析,VEGF、HIF-1α分別與CRP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r=0.295,P=0.022;r=0.885,P<0.001)。
3 討論
研究顯示糖尿病已被視為動脈狹窄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發生的獨立性危險因素[11],與血糖水平升高有密切關聯。在本次研究中,對糖尿病合并動脈狹窄行支架植入治療的病人追蹤觀察發現,病人的血清HbA1c、TC、VEGF、HIF-1α、sLDLc、CRP、病變血管類型,支架植入長度及支架直徑等均與動脈支架植入后再狹窄有關。在進一步的多因素分析中發現,VEGF、HIF-1α、HbA1c、CRP水平是發生再狹窄的危險因素,而支架直徑是保護性因素。
HbA1c能夠反應病人血糖的長期控制狀況,HbA1c過高反應病人長期的血糖控制不良,其能夠通過多種機制引起血管內皮的增生,誘發氧化應激及炎癥反應等,導致血管的再狹窄。
TC和sLDLc也是發生再狹窄的相關因素,TC和sLDLc能夠引起血管內皮的損傷和脂質沉積,導致內膜的氧化損傷和粥樣斑塊形成,尤其是sdLDL-C更容易被氧化修飾[12],而且不能夠被低密度脂蛋白受體識別,不容被清除,對血管的危害更為顯著。
此外,血管病變的類型、支架的長度及管徑等均與支架植入后的再狹窄有關,其可能與原發血管病變的嚴重程度以及支架長度及管徑不同所造成的血流動力學差異有關,其中較小管徑的支架更容易為增生的組織所填塞導致血管閉塞。糖尿病病人高血糖狀態能夠引起耗氧量增加20%~25%[13-14];且血糖升高通過引起血管內皮細胞鈣平衡功能紊亂,能夠激活蛋白激酶C系統活性,致一氧化氮含量下降、超氧陰離子增加,最終引起血小板功能異常,造成血液日益呈現高凝態勢[15];隨著時間推移而誘發局部組織缺血缺氧。
HIF-1α是一種能感受缺氧環境且能對其實施調控反應而具有特殊生物學活性的核轉錄因子[16],該指標水平的升高往往提示機體處于缺氧狀態;且可以通過啟動VEGF基因表達而促進新血管的形成及內皮細胞增殖以增加血管數量及密度,從而提升缺血組織血流灌注、供氧量等,實現減輕缺血缺氧對組織的損傷作用[17];在分析中發現,HIF-1α及VEGF是動脈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的獨立危險因素,也提示機體的缺氧及血管增生活躍是引起動脈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的機制之一。二者水平升高,說明病人局部細胞代謝處于低氧狀態;而長期的低氧狀態能激活和促進泡沫細胞形成,從而誘發血管內皮細胞功能和結構異常、加重炎癥反應和氧化應激反應等病理性機制變化,進而引起動脈粥樣硬化發生或加重,甚至導致動脈再次狹窄或閉塞[18-19]。
CRP是預測硬化動脈血管粥樣斑塊穩定性的公認指標,在CRP水平增高的病人,病變血管發生閉塞及斑塊破裂的風險均較高。本組資料的分析中發現,冠脈支架植入術后的病人,HIF-1α及VEGF的水平與CRP的水平具有正相關關系,說明其在動脈狹窄的病人中表達具有一致性。進一步的ROC分析結果顯示:VEGF、HIF-1α和CRP評定曲線下面積(AUC)均超過0.50,提示三者均具有評定價值,并以VEGF、HIF-1α為優,其評定靈敏度、特異性均高于CRP,說明VEGF、HIF-1α界定糖尿病合并動脈狹窄病人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可能性的價值較高。
綜上所述,VEGF、HIF-1α水平異常變化可能參與了糖尿病動脈支架植入術后再狹窄發生,所以通過檢測二者水平狀況,能夠預測病人血管支架植入后再狹窄發生的風險程度。但本研究僅以本院糖尿病動脈支架植入術病人為主,造成不同程度選擇性偏倚,削弱了研究結論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