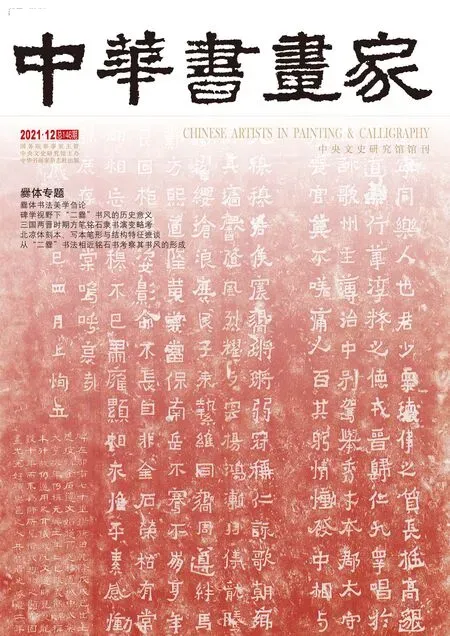碑學視野下“二爨”書風的歷史意義
□ 王吉凱
清代碑學書風在中國書法史上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其首先打破了千百年來學書取法帖學的固有慣式,改變了傳統文人書法的審美范式,使得大量南北朝殘碑斷碣登入文人士大夫的大雅之堂,學書取法途徑進一步多元化。碑學的興起除卻帖學自身的輾轉翻摹面目全非之外,金石考據之學的興盛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條件,故馬宗霍《書林藻鑒》稱:“嘉道以還,帖學始盛極而衰,碑學乃得以乘之。先是雍正、乾隆間,文字之獄甚嚴,通人學士,含毫結舌,無所攄其志意,因究必于考古。小學既昌,談者群籍金石以為證經訂史之具。金石之出土日多,摹搨之流傳亦日廣,初所資以考古者,后遂資以學書。故碑學之興,又金石學有以成之也。”①在金石學興盛的學術氛圍帶動下,文人學者訪碑風氣成為一時之尚,《爨龍顏碑》即是在這種訪碑風氣中為阮元所發現。
“二爨”碑刻在出土伊始并未引起書家足夠的重視,一般制作成拓本在友朋之間贈送傳閱,其史料價值遠過于其書法審美價值,這與當時碑刻作為金石學證經補史的學術風尚是分不開的。但隨著金石碑志的出土日多,也逐漸吸引了一批書家學者的注意,其書法審美價值亦隨之被重視。正如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一文中提到:“從前的人,本來并沒有所謂‘碑學’,嘉道以后,漢魏碑志出土漸多,一方面固然給幾位經小學家去做考證經史的資料,又一方面便在書學界開個光明燦爛的新紀元。”②徐利明《中國書法風格史》在談及這一現象時亦稱:“自明末清初以降,金石書跡的發現日益增多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客觀條件,書家的審美視野因此而日益開闊,從而使得書風的發展在帖學大盛的形勢下產生了一股潛在的暗流,由細小在逐步擴大,審美趣尚在悄悄地轉移,對古碑、志書跡的價值取向正發生著變化。”③真正使“二爨”在書法審美上為書家所重的是康有為,其在《廣藝舟雙楫》中對“二爨”碑刻的書法價值有著極高的評價。“二爨”碑刻的價值之所以能在清代碑學風潮中大放異彩,絕不單是其作為“南碑絕少”的獨特風格存在,而是全面地體現在學術、審美及書學取法之中。

[東晉]爨寶子碑(局部)拓本
一、質疑《蘭亭》:傳統權威的動搖
隨著晚清金石書跡的出土日多,書家的審美志趣隨之轉移,對南北朝碑志的關注也更為空前,在此基礎上,也逐漸演變出了書法藝術上的碑、帖之爭。阮元作《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欲揚碑而抑帖,阮氏之論出,一時響應者翕然,自此,關于書法碑、帖孰優孰劣的高下之分一直爭論不休,從而造就了清代書壇獨特的學術爭鳴。在這場關于碑、帖高下的學術紛爭中,最為顯著的就是作為傳統經典權威法帖地位的動搖。千百年來學書以傳統法帖為范本幾成慣式,尤其“二王”父子為代表的刻帖更是被歷代書家奉為圭臬,但這一慣例在清代碑學的大背景下逐漸被沖破。袁昶《毗邪臺散人日記》稱:“茍以二王書札結體施之石刻,如野服處士驟登臺閣,究嫌寒乞相,何能赤舄兒而有舂容之度哉。”④在袁昶看來,縱使如“二王”父子書札之俱美,若強施之以碑版,其亦不乏有寒乞之相,此雖是碑、帖二途各自因其不同的審美形態所致,但在碑學尚未興起之前的文人書家眼中,“二王”父子書札顯然是不容批判的。從側面也可以看出,在清代碑學書風的大背景下,被歷代書家奉為圭臬的“二王”書風地位也隨之動搖。而被奉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在這種風尚下也漸引起書家的懷疑。阮元就曾以當時新出土晉磚銘文來公開質疑王羲之《蘭亭序》的真實性,其《晉永和泰元磚字拓本跋》稱:“此磚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蘭亭》前后數十年。此種字體,乃東晉時民間通用之體。墓人為壙,匠人寫坯,尚皆如此。可見爾時民間尚有篆、隸遺意,何嘗似羲、獻之體?”⑤又《毗陵呂氏古磚文字拓本跋》稱:“王著所摹晉帖,余舊守‘無征不從’之例,而心折于晉宋之磚,為其下真跡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試審此冊內永和三、六、八、九、十各磚隸體,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寫,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隸字尤為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當是羲之之族,何與《蘭亭》決不相類耶?”⑥阮元以東晉磚文來質疑挑戰《蘭亭序》的權威性,這在當時可謂是驚世駭俗之言,若細究之,其質疑《蘭亭序》真實性的背后實則是鞏固其“南北書派論”的合理性,故美國學者艾爾曼稱:“阮元撰寫了兩篇在中國書法史上有著開拓性貢獻的論文,他認為,‘二王’創立的書體并不代表兩漢以后的書法風格,擔此重任的是磚石文字。”⑦

[北魏]欽文姬辰墓表(局部)拓本

[南朝宋]爨龍顏碑(局部)拓本

[北魏]司馬金龍墓表(局部)拓本
如果說阮元依據東晉磚文只是對《蘭亭序》的真實性提出質疑的話,那么碑學書家李文田則十分肯定地認為《蘭亭序》為偽作,并且指出王羲之書的真實面貌則與“二爨”相近。其稱:“梁以前之《蘭亭》與唐以后之《蘭亭》,文尚難信,何有于字?且古稱右軍善書,曰‘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曰‘銀鉤鐵畫’,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茍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爨龍顏》相近而后可。以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后體也。”⑧李文田依據《蘭亭序》文本及后世書家對王羲之書法風格的評述來否定《蘭亭序》的真實性,在其看來,王羲之《蘭亭序》不傳則已,若有則必與“二爨”書風相近,這也是“二爨”碑刻第一次在書法學術方面擔任如此角色。李文田之所以認為王羲之《蘭亭序》書風與“二爨”碑刻相近,原因有二:其一,李文田認為東晉以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而“二爨”書風所保留的隸書意趣正屬于此類;其二,在時間上“二爨”碑刻更接近于王羲之《蘭亭序》的所書時間。無獨有偶,在近代書法史上由《王興之夫婦墓志》和《謝鯤墓志》而引發的“蘭亭論辯”與李文田以“二爨”來質疑《蘭亭序》的觀點可謂如出一轍,不同的是李文田所依據的“二爨”換成了郭沫若所依據的王、謝墓志。無論是李文田以“二爨”否定《蘭亭》亦或是“蘭亭論辯”中的王、謝墓志,其所討論的無外乎銘石書與手寫體墨跡二者審美和功用目的之本質差別所在。正如章士釗所謂:“晉人公用爨,私用王;碑用爨,帖用王;文書用爨,書札用王;刀筆用爨,毛筆用王。以一人論,可能先爨后王,抑先王后爨,亦可能一時王爨皆工。”⑨以今日之眼光來較《蘭亭》則已成定論,但“二爨”碑刻在書法史上曾起到的學術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二、派別之爭:南北不能分派
阮元作《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專以法帖屬南而碑榜屬北。其《南北書派論》稱:“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蓋由隸字變為正書、行書,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正書、行草之分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也……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尺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⑩阮元以地域為界將書法分為南北兩派,其依據南朝帖系筆法之傳承關系亦將北碑溯源分流,南北兩派同宗鍾繇、衛瓘,南派由羲、獻父子傳至王僧虔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則由索靖、崔悅、盧諶、高遵等傳至歐陽詢、褚遂良。在阮元看來,南北兩派因士族不相通習,故兩派書風判若江河。阮元的南北書派之說也引起了一批書家的推崇,錢泳更是在其《書學》中專辟《書法分南北宗》一篇以響應阮氏之說,此外如伊秉綬、梁章鉅、何紹基等人亦對阮氏之說無不推崇備至。但隨著書家對南北朝碑版的熱情高漲及碑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亦有相當書家對阮元所提出的南北書派觀點提出質疑,對阮元南北書派持反對態度的書家所依據的觀點也正是“二爨”與北碑書風的相似之處。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關于“二爨”碑刻的論述甚夥,并常將“二爨”與北魏碑刻進行風格對比以辨其源流,其稱:“晉碑如《郛休》《爨寶子》二碑,樸厚古茂,奇姿百出,與魏碑之《靈廟》《鞠彥云》,皆在隸、楷之間,可以考見變體源流。”又:“南碑奇古之《寶子》,則有《靈廟碑》似之;高美之《爨龍顏》,峻整之《始興王碑》,則有《靈廟碑陰》《張猛龍》《溫泉頌》當之。”“《爨龍顏》與《靈廟碑陰》同體,渾金璞玉,皆師元常,實承中郎之正統。”康有為在列舉了種種南北碑版對比之后,詳盡歸納總結了南北碑版書風的相似之處,其得出了書可分派而南北不能分派的結論,故其稱:“阮文達《南北書派》,專以帖法屬南……以余考之,北碑中若《鄭文公》之神韻,《靈廟碑陰》《暉福寺》之高簡,《石門銘》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劉懿》《敬德騕》《龍藏寺》之虛和婉麗,何嘗與南碑有異?南碑所傳絕少,然《始興王碑》戈戟森然,出鋒布勢,為率更所出,何嘗與《張猛龍》《楊大眼》筆法有異哉!故書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達之為是論,蓋見南碑猶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為界,強分南北也。”在康有為看來,阮元之所以以碑帖二途劃分南北是因其見南碑絕少,不能詳盡辨其源流,故以碑帖為界強分南北。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將《爨寶子碑》《爨龍顏碑》對比最多的就是北碑《嵩高靈廟碑》。從整體風格上看,《爨寶子碑》(東晉安帝乙巳年,405)與《嵩高靈廟碑》(北魏太延二年,436)尤為相似,二者線條厚重且筆畫多平直,隸法之波磔鮮明,同屬隸楷之過渡體。除此之外,北魏平城時期的《欽文姬辰墓志銘》(北魏延興四年,474)也與《爨寶子碑》極為相似,尤其在一個字中的多個隸法波磔的處理上可謂絕肖。

[清]沈曾植 臨《爨寶子碑》 紙本款識:《爨寶子碑》。鈐印:馀黎(朱)

[清]沈曾植 臨《爨龍顏碑》 紙本款識:《爨龍顏碑》。
康有為還將《爨龍顏碑》(孝武帝大明二年,458)與《靈廟碑陰》進行對比,《靈廟碑陰》今已漫漶不可識。但在其他北朝碑刻中依然可以發現與《爨龍顏碑》風格相近的作品,如北魏平城時期的《司馬金龍墓表》(北魏太和八年,484)和《皇帝南巡之頌碑》(北魏和平二年,461),相較于《爨寶子碑》的筆畫厚重和較多隸法波磔的處理方式,《爨龍顏碑》的筆畫則較為瘦勁,且隸法波磔的處理相對較少,往往只保留在末筆的捺畫之中,這表明經過50余年的書體演變,《爨龍顏碑》相較于《爨寶子碑》已漸至脫去隸法而向更成熟的楷書方向發展。從近世不斷出土的南北朝時期諸多碑版來看,南碑與北碑的書法風格并非阮元所謂之兩派判若江河。沙孟海在《中國書法史圖錄上冊分期概說》中將北碑結體分為“斜畫緊結”和“平畫寬結”兩大類型,就“二爨”碑刻所表現出的結體特征來看,其與北碑之“平畫寬結”類型的碑刻并無二致,唯隸法之波磔處或隱或顯。總的來說,無論南碑抑或是北碑,其皆是當時出于隸楷過渡階段所保留的時代特征。曾熙《跋清道人節臨六朝碑四種》云:“南北碑志‘二爨’與《中岳靈廟碑》同體,以剛勝。”而所謂書分南北兩派之說在“二爨”與北碑書風的對照下也顯然是有違史實的,正如沙孟海所謂:“南碑數量不多,但不是絕無……而《爨龍顏碑》在云南,《大代華岳廟碑》在陜西,《嵩高靈廟碑》在河南,書體近似,地隔南北。以上都說明南北書體是不能分派的。”可以看出,隨著碑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和體系化,不少書家也漸至糾正了阮元所提出的“書分南北兩派”相對偏頗的碑學觀點,而“二爨”毫無疑問是他們最直接而有力的證據。
三、楷隸共參:造就碑學新境
“二爨”書風除了在碑學書法的學術紛爭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之外,其在碑派書風的實踐創作方面同樣有著不同尋常的作用。在清代晚期,碑派書法經阮元、包世臣、康有為等人的極力推崇而大行于世,在康有為之前,“二爨”碑刻的作用多體現在經史考訂層面,“二爨”書風之所以能在晚清書壇聲名大噪,與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的極力推崇不無關系。其更是將《爨龍顏碑》視為“正書第一”。康有為在《論書絕句》中稱贊《爨龍顏碑》:“鐵石縱橫體勢奇,相斯筆法孰傳之?漢經以后音塵絕,惟有《龍顏》第一碑。”后又跋曰:“宋《爨龍顏碑》渾厚生動,兼茂密雄強之勝,為正書第一。”康有為雖然在《廣藝舟雙楫》中極力推崇“二爨”,但其碑學思想尤青睞北碑,在書法實踐中也并未涉及“二爨”。在康有為之前,雖有碑學書家楊峴曾對《爨寶子碑》取法臨習,但其多以漢隸法來改造爨碑,筆法上易方為圓,頗具個性特色。
首先在“二爨”書風取得突破并卓有建樹的書家是沈曾植。沈曾植也是碑派書風的代表書家,不同于阮元、康有為等碑學書家偏激的尊碑主張,沈曾植在書法上崇尚碑帖共治、南北會通。沈曾植的弟子王蘧常曾題其師絕筆楹聯有詩云:“昔年書法傳坤艮,置我三王二爨間。”沈曾植一生臨習“二爨”頗多,據戴家妙統計:“沈寐叟傳世作品中,就有十來件臨《二爨》。”除了臨摹,沈曾植的楷書創作受“二爨”書風的影響也十分明顯,這與其所主張隸楷共參的書學思想是一致的。沈曾植《論行楷隸篆通變》稱:“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二爨”作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由隸向楷的過渡書體,也最能體現沈曾植所謂“隸參楷勢而姿生”的書法美學特質。曾熙評價沈曾植書法時:“工處在拙,妙處在生。”以沈曾植的楷書來看,曾熙之論誠不虛也。沈曾植楷書之獨特處正在于“拙”與“生”二字,而“二爨”作為由隸向楷的過渡性書體,未脫漢法之“拙”與未定型楷法之“生”是其顯著特征,此也正是與沈曾植楷書的暗合之處。
除了沈曾植,碑派書法的代表書家鄭孝胥、李瑞清等人亦對“二爨”碑刻青睞有加。鄭孝胥曾在日記中有多處其觀摩收購“二爨”拓本和臨寫“二爨”的記錄,而且在書學思想上與沈曾植同樣主張“楷隸相參”,如其《題清道人臨魏碑》云:“蔡君謨謂《瘞鶴銘》乃六朝人楷隸相參之作,觀六朝人書無不楷隸相參者,此蓋唐以前法,似奇而實正也。”雖然不見鄭孝胥對“二爨”碑刻的細致論述,但從其推崇六朝碑版中“楷隸相參”美學特質的態度來看,“二爨”碑刻的書法風格顯然是符合其書法美學思想的。李瑞清尤愛《爨龍顏碑》,嘗評此碑:“納險絕入平正,南中第一碑也。”由臨《爨龍顏碑》稱:“用筆得之《乙瑛》,布白出于《鄭固》,化橫為縱,拿空筆實,若但以形貌求之,愈近則愈遠,納險絕入平正,大難大難。”

[清]沈曾植 節臨《爨寶子碑》 紙本鈐印:寐叟(朱)沈(朱)

[清]王世鏜 自在有才八言聯 紙本 1928年釋文:自在本自由之所始;有才非有德莫能良。戊辰孟夏,積鐵試墨。鈐印:云津王世鏜之印(白)魯生長壽年(朱)
晚清書壇在碑學運動的影響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風貌,但多數書家在阮元、包世臣、康有為等碑學理論的宣揚下對北碑書風推崇備至。在此種情形下,沈曾植、鄭孝胥、李瑞清等書家能從“二爨”書風中探尋“楷隸共參”的生拙之趣,無疑開辟了碑學書風之新境。在民國以來的后碑學時期,仍有相當書家受“二爨”書風的影響而形成獨特的書法風格,如經亨頤、弘一法師、沈尹默、高二適等書家,皆在一定程度上浸染“二爨”書風,這也是“二爨”書風在近代書法風格中的新拓展。
結語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稱:“南碑數十種,只字片石,皆稀世罕有;既流傳絕少,又書皆神妙,較之魏碑,尚覺高逸過之。”相較于魏碑的繁星浩瀚,南碑確實如孔子之履稀世罕有,故論書者也往往更加看重其書法美學價值。然若將“二爨”碑刻放置整個清代碑學運動中考察,會發現“二爨”碑刻的價值及作用絕非僅存在于書法審美層面,自碑學運動的發生伊始至其落幕,“二爨”碑刻是貫穿其始終的。無論是李文田以“二爨”否定《蘭亭》、抑或是康有為以“二爨”來否定阮元的南北分派之說,直至晚清沈曾植等人以“二爨”來開辟碑學新境,“二爨”在整個碑學運動中自始至終都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而我們今天再重新審視清代的碑學運動,“二爨”在其中的歷史意義是不容忽視的。■
注釋:
①馬宗霍《書林藻鑒》卷十二,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92頁。
②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論書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第37頁。
③徐利明《中國書法風格史》,河南美術出版社,1997年,第457頁。
④袁昶《毗邪臺山散人日記》,張小莊《清代筆記、日記中的書法史料整理與研究》(上),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2年,第122頁。
⑤[清]阮元《揅經室集》三集卷一,中華書局,2016年,第602頁。
⑥[清]阮元《揅經室續集》卷三,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影印本,第136頁。
⑦[美]本杰明·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2頁。
⑧梁達濤《廣東歷代書家研究叢書·李文田卷》,嶺南美術出版社,2017年,第40頁。
⑨章士釗《柳子厚之于蘭亭》,《蘭亭論辨·下編》,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頁。
⑩[清]阮元《南北書派論》,《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年,第629-6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