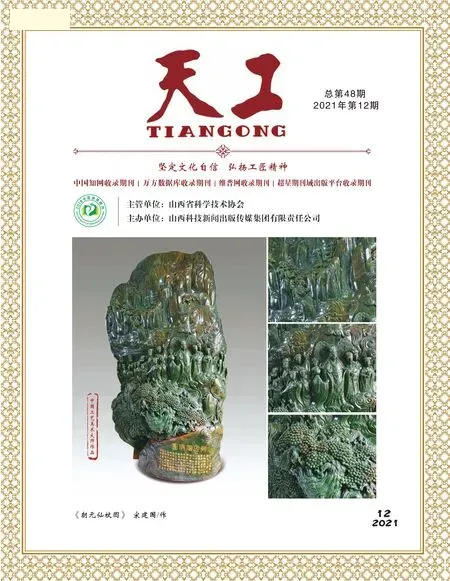大冶刺繡圖像的視覺建構
吳秀麗 湖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一、歷史溯源
任何一種有深厚歷史根基的文化現象都反映著民族文化精神,是文化整體結構中的重要環節。大冶刺繡作為荊楚刺繡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鄂東南民俗文化的土壤中逐漸形成的具有獨特藝術精神與獨特藝術語言的區域民俗文化載體。
大冶是民間繡活(大冶刺繡)的發源地,坐落于湖北省東南部,長江中下游南岸的湖北“冶金走廊”腹地。根據17世紀的清·康熙《大冶縣志》中記載的“女紅度日”與19世紀清·同治《大冶縣志》中記載的“針黹晨夕”可以窺見當地刺繡工藝的歷史性。另外,在大冶的明清古建筑群里,大箕鋪鎮水南灣古村落,靈鄉鎮的胡家大院等庭院建筑中至今仍保留著大戶小姐習女紅以評才德優劣的繡樓。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大冶市城區、大箕鋪鎮、劉仁八鎮、陳貴鎮、姜橋石任村、茗山鄉等地又出現以繡花鞋為業的碼頭批零售賣點,這是大冶民間刺繡從傳統的品鑒性轉為商品性的歷史見證,體現了這一民間繡活的觀念轉化,也印證了當年大冶刺繡盛況。時至今日,在大冶城鄉仍活躍著許多繡花女,農閑時她們攜一圓繃,聚桌而圍,一邊唱著千年流傳的《十繡歌》《勸女歌》等民間刺繡歌謠,一邊剪紙繡花,構建了大冶刺繡剪紙繡花與方言唱和相互融合的傳統刺繡文化,展現著大冶刺繡文化靜態與動態相結合而產生的視覺文化結構模式。隨著文化與經濟的不斷發展,繡活女紅從單一的女性才德的表征逐漸轉化為補貼家用生活所需之技能。這種技能的傳承以家族、師徒關系為紐帶,通過傳統的家傳模式得以世代傳承。時至今日,大冶刺繡已經傳承了六代人,有史可依的傳承譜系:
第一代傳承人石氏太婆(1851年生),張接弟(光緒年生);
第二代傳承人馮蓮氏(1884年生);
第三代傳承人阮轉(1920年生)、盧金繡(1933年生)、胡定蓮(1938年生)、鄧桂芬(1939年生);
第四代傳承人段辛紅(1941年生)、劉蘭田(1944年生)、熊翠英(1947年生)、陳芬(1952年生);
第五代傳承人李秋英(1957年生)、劉小紅(1968年生)、鄭文莉(1969年生);
第六代傳承人彭肖肖(1991年生)、譚春英(1983年生)、張秀容(1955年生)等。
從以上第一代傳承人石氏太婆、張接弟到第五代傳承人劉小紅再到第六代傳承人彭肖肖、譚春英等,大冶刺繡傳承文脈已達百年之久,展現了大冶刺繡文化的系統性與歷史性。近幾十年來,在國家大力倡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背景下,第五代傳承人劉小紅在當地政府的幫助與扶持下以工作室為基點進行開放式授徒,以培訓班、公益公開課等多種形式推動了大冶刺繡文化的廣泛傳播,促進了本地區經濟和文化的共同發展。
特定的地理位置與豐富的礦產資源,推動了大冶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物質生活比較富足的狀態下人們渴望更高層次的精神文化追求。而作為民間繡活的大冶刺繡符合了當地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至今,大冶刺繡已成為特定的民俗文化符號,鑲嵌在鄂東南區域文化之中。
二、大冶刺繡圖像的視覺建構
早在1912年,德國阿比·瓦爾堡就提出圖像是“文化記憶”的均等載體。大冶刺繡作為湖北刺繡文化的一部分,其圖像紋樣的構成與鄂東民俗文化緊密相連,也是鄂東區域性民俗文化的記憶載體。
(一)主題與觀念
當特定的觀念作為表現主題進入造型活動時,它便會與審美主體對現實事物的感受相聯系,使現實事物中與觀念表現要求相關的形象特征為審美主體所關注和選擇。①呂品田:《中國民間美術觀念》,江蘇美術出版社,1992,第334頁。求生、趨利、避害作為一種集體性、歷史性的民間文化觀念千百年來牽引人們用各種民俗文化形式表達智慧、傳達文化。大冶刺繡一直秉承先剪紙再刺繡的傳統工藝,在表達主題上多以祈福納祥、趨利避害等觀念進行傳達并應用于服飾、鞋、帽、枕頭、帳簾及錢包、香包等生活物件上。
在我國“吉祥”二字有福瑞喜慶、諸事順利的意思。《說文》中講:“吉,善也,從士口;祥,福氣,從示羊聲,一云善。”在民俗文化中象征如此觀念的圖案紋樣較為普遍。在我國最早關于“吉祥圖案”的記載是甘肅成縣魚竅峽的摩崖的《五瑞圖》巖畫,據說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隨著文化的不斷發展,人們對吉祥幸福的渴求越來越強烈,并在唐朝得到了更為廣闊的發展且一直延續至今。大冶刺繡在創作主題觀念上始終圍繞傳統的吉祥納福、趨利避害等觀念進行主題創作。
1. 驅邪接福
獅子是文殊菩薩的坐騎,有驅邪之象征,常用在傳統婚禮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上,有吉祥喜慶、好事連連的寓意。據《漢書·禮樂志》記載,漢代民間流行獅舞,兩人合扮一獅,一人持彩球逗之,上下翻騰跳躍,有祛除災難、好事降臨之意,由此獅子滾繡球圖案便在民俗文化之中廣泛推廣開來。
在大冶刺繡圖像中沿襲傳統吉祥圖案獅子滾繡球進行主題創作的典型代表作有兒童包被、披風等(如圖1)。另外,在兒童的肚兜、口水兜等物品中經常出現五毒辟邪的吉祥圖案,創作者通過繡制蜈蚣、毒蛇、蝎子、壁虎和蟾蜍這五種有毒動物的圖案來驅逐災禍、祈求孩童平安健康成長,并把它作為禮品贈送親友,表示吉祥、和善、友愛、辟邪、保平安。在民俗言語中有“九個石榴一個手,小鬼不敢見,閻王領不走”,所以在娃娃肚兜上繡石榴和佛手,寓意孩童長命百歲。在婚嫁用品上繡有“蛇盤兔”圖案則寓意男女婚配的和睦與富足。

圖1 《兒童披風·獅子滾繡球》 劉小紅/作 彭濤/攝
以上種種驅邪接福的刺繡圖案基本都有驅邪惡、除百病、保平安、得福貴的美好寓意,無論是孩童的獅子滾繡球披風還是五毒辟邪的圍兜、獅子形涼帽,都要圖個吉祥好彩頭。
2.喜慶祝壽
寓意夫妻恩愛、永不分離的題材比較多地表現在婚嫁服飾以及婚配用品上。舊時上至皇家下至平民百姓,婚嫁繡品不管多與少、簡與繁都必備。“鴛鴦采蓮”“鯉魚鬧蓮”“鷺鷥戲荷”“富貴白頭”“花開見子”等圖樣刺繡在婚嫁禮品之中寓意“同偕到老,永不分離”的美德。如繡花衣、繡花枕、繡花蓋頭、繡花轎簾、繡花被面、繡花鞋、帳沿、床上用品、荷包、香囊等都繡有各種吉祥圖案,寓意“早生貴子、白頭到老”(如圖2)。

圖2 《婚嫁系列》 劉小紅/作 彭濤/攝
(二)制作程序
大冶刺繡分為底稿制作與刺繡兩大步。
第一步:根據主題選擇合適的圖案紋樣并把選好的圖案紋樣畫在紙上,再用剪刀剪下后,用膠水貼在繡布上,然后根據主題需要進行選色配色。一般一幅作品以三色系、五色系為主。三色為“天地人和”,即紅、黃、藍三原色,代表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一般用于兒童服飾上。五色為“金、木、水、火、土”,代表五行,即青、黃、赤、黑、白,寓意“萬物生長,五行不可缺”,一般用于戲服、女士服飾上。
第二步:用不同的針法刺繡選好的底稿,繡面注意齊、平、整、密,方向不能繡反。刺繡花草時一般都要順時針繡制,針腳一般在1厘米以內,不能太長,花瓣由外向內繡制,外圈要保持針腳整齊,繡線平行。對于動物與人物而言,刺繡針法也各有不同,在這里不做贅述。如圖3的老物件《口水兜》在制作過程中就是嚴格按照以上的傳統流程進行制作的。但是對于現當代來說,由于刺繡工藝的不斷提升,有些民間刺繡高手會根據主題與觀念不繪制底稿,用意象造型觀念直接繡制而成,如圖4的《星云之夢》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圖4 《星云之夢》 劉小紅/作 彭濤/攝
另外,在整個制作過程中繡娘之間還通過唱念《十繡歌》《勸女歌》來助興和表達心中的愉悅之情。《十繡歌》如下:
一繡廣東城,城城鬧盈盈,想起那曹操調雄軍
二繡花世界,街中好買賣,想起那仙女下凡來
三繡赤壁巖,齊齊露出來,想起那三娘把磨挨
四繡荷花放,蓮蓬在中間,想起那藕斷絲不斷
五繡舞龍雞,身穿五色衣,想起那觀音度眾生
六繡楊六郎,打開白虎堂,想起那佛祖救凡民
七繡七月七,鵲橋來相會,你在河東,我在河西
八繡百褶裙,層層起彩云,想起那百褶掃灰塵
九繡九月九,荷包繡到手,想起那荷包兩朋友
十繡小陽春,荷包繡起身,想起那荷包兩老根
(三)藝術特征
任何民間美術的造型都會受到實用性與審美性的雙重制約,而實用性在民間美術造型中占主導地位。民間美術作品的特殊之處在于內容、藝術形式、制作技術,這些因素跟物品實際用途是有機聯系的。
1.造型特征
大冶刺繡紋樣的造型在實用性基礎上仍保持著審美的獨特性,這尤其表現在底稿制作上。首先,在制作過程中創作主體會根據實際用途,采用適形造型法,具體表現為不依賴原始物象的具象形態而是根據主題需要依據記憶進行適形性的底稿制作。通常情況下,創作者會根據需要在保留原圖案的完整性的基礎上進行內部結構的調整或大小的縮減,以便放置在合適的位置完成主題表達。整體造型體現出稚拙而不失童趣、簡潔而不失繁復、夸張而不失樸實、詼諧而不失莊重的意象性。例如,《婚嫁系列》(圖2)中有表達喜慶的如意雙喜拖鞋、如意雙喜紅蓋頭、如意雙全改口紅包、雙喜枕頭、百子被等都是根據主題需要選取不同的圖案進行制作;另外,表達祈福納祥之意的刺繡圖案紋樣有兒童口水兜(圖3)中的十指生花,同樣采用適形造型法。這些刺繡紋樣的造型無不體現出圖像的古拙、質樸的意象之美。在各種民俗生活中,常見的獅子滾繡球披風、蓮生貴子包裙、暗八仙百家衣、五毒鞋、口水兜、兒童帽等分別展示出稚拙、夸張、簡潔的造型特征,并賦予吉祥、安康的寓意,展現出人們對日常生活中吉祥、幸福的渴求以及對信仰的無限崇拜。

圖3 《口水兜·十指生花》 劉蘭田/作 彭濤/攝
2.色彩特征
色彩搭配的典型性:色彩簡練,注重對比,感染力強,如常喜用“三色系”和“五色系”配色法。三色為“天、地、人”三界,而五色即為“五行”。整體色彩嬌艷而不失雅致、強烈而不失恬淡,形成了獨特的視覺藝術特征。
在傳統的創作觀念中,求生、趨利、避害、納福、祈祥等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主題,并成為一種符號表現在刺繡藝術作品之中。現當代大冶刺繡在主題創作與觀念上一直延續和深化這種傳統觀念,并在當代刺繡作品中進行延續和拓展。
3.傳承與發展
任何藝術的發生和發展都會受歷史、自然地理條件以及民俗文化的影響,把握、體認傳統民俗文化的智慧,并把符合自身的意愿、希望和立意融入現實生活中,創作具有時代特色的藝術作品是當下藝術創作者的使命。大冶刺繡在沿襲傳統刺繡工藝的基礎上結合時代要求在造型特色與針法上進行了突破。例如,作品《星云之夢》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作者劉小紅以紀念我國航空航天60周年為主題,采用無底稿而繡的造型方法配合盤旋針、柳針、摻針等針法繡制而成,在色彩配置上采用藍與紅作為主色,代表陰與陽、水與火,背景中采用星星作為點綴表示宇宙,寓意永恒。整幅作品是以旋轉七彩星云組成的“60”字樣,歌頌了祖國對太空探索事業的永無止境,有“天宮一繡”與“天上第一繡”的稱號。
大冶刺繡幾代傳承人在參照、繼承傳統老花樣的同時以能動的唯我態度把握客觀對象,從傳統的圖案紋樣到現當代的圖案刺繡紋樣無不真實地記錄了不同歷史時期的民俗習慣、風土人情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反映了當地人民對物質、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建構了具有傳統特色與新時代精神訴求的新花樣。
三、結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工作,強調“讓文物說話”,講述中國,溝通世界。文化遺產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同時也是對外交流的文化紐帶。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冶刺繡與當地民間口頭文學以及民間歌調相互融合,形成了獨特的動態結構模式,蘊含著本地區的民俗風情與民俗文化,彰顯了刺繡文化的藝術特色與地域民俗文化特色。美的本質在于人們改造現實的能動的生活、實踐之中,主張從主體實踐對客體現實的能動活動中去探求美的本質,美的本質是真與善的統一,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①李澤厚:《美學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第197頁。大冶刺繡圖案紋樣在合乎主題表達的基礎上始終圍繞真與善的審美意蘊通過簡約與繁密、質樸與柔媚、夸張與寫實的處理法則,表達了自身的審美價值。大冶刺繡文化的百年傳承真實地記錄和印證了當地人們對物質與精神文化生活的雙重需要,并滲透到人們的生辰、婚嫁、壽誕、祭祀、宗教及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這個地區的人們共同享有的文化產品。
在現當代通信技術發達、傳播渠道多樣化的背景下,大冶刺繡文化漸漸受到相應的影響,使得人們在本土刺繡文化特色和外界文化的不斷交流碰撞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尋找一種表達的平衡來達到文化的自身認同;同時這種刺繡圖像的變遷又是復雜的,它受到本地區的視覺建構者和消費者與外界的視覺建構者和消費者的認知水平以及文化認同、傳播媒介等多方面的影響。近些年,傳承人劉小紅所創企業和培訓學校也培養了眾多專業和兼職繡娘,并為當地待業婦女、貧困人員、殘疾人、下崗人員、應屆畢業生等提供了手工技能培訓和就業機會。另外,這種具有地域性、文化性、保護性、周期性文化產業的不斷發展對建構區域文化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