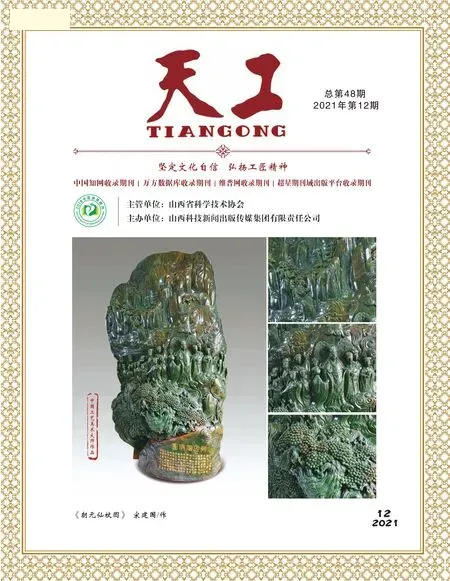關于現代漆畫創作中語言運用的思考
盧鐵柱 天津美術學院
中國現代漆畫的發展根植于8000年以上的大漆藝術,常用材料多種多樣,除天然大漆之外,還有各種金屬以及貝類、石類、木質材料等,因此它的工藝技法非常豐富,在色彩、造型、肌理、畫面構圖、制作等方面的表現形式極具特色,并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人們的生活中表現出璀璨奪目的一面。
漆畫作為一個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逐漸發展起來的獨立畫種,在創作語言運用上有著自己的辯證邏輯和美學追求,這既是漆畫藝術家感悟自然與社會、彰顯他們藝術個性的結果,又是藝術家深刻內省、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在漆畫創作中融匯現代藝術精華和相關理念、手段進行大膽實踐的成果[1]。
一、漆畫創作中語言運用背后的辯證邏輯
漆畫語言運用要遵循中國傳統美學中倡導的“陰陽相濟之道”。“陰陽相濟”是萬物運行的基本規律,也是各種語言技法運用背后所隱含的辯證思維。
“陰陽”是一對包含著樸素的辯證法的概念,源于中華民族文化對世界的傳統認知,是萬事萬物抽象出的一般規律,體現在藝術與美學等具體領域中。《周易·說卦》稱:“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交。”意思是說,宇宙間萬物皆有陰陽兩面,因而創立陰陽兩類卦象;通常陽為剛性一面,陰為柔性一面。一般來說,陰陽還涉及藏與露、巧與拙、曲與直、隱與顯、虛與實、正與反等范疇。
陰陽相輔相成,互為其用,是我們在創作時應該奉行的根本原則。陰陽體現著自然和社會有效運轉的規律,同時也是萬物生成、變化與發展的重要法則。漆畫以漆為媒材,以各種工藝技法為手段,調和漆色冷暖、明暗、主次、藏露等陰陽兩面對立統一的矛盾,從而創造出絢爛多彩的畫面[2]。
二、漆畫創作中語言運用在美學上的追求
(一)大巧若拙,拙處見工
漆畫語言在藝術表現上體現了辯證的要素,在創造美的過程中反映著藝術家的情懷與性靈。大巧若拙體現出藝術創造上“巧”與“拙”的辯證關系,是漆畫藝術創造所追求的美學表征。這既是一種美好的藝術境界,又是人類崇高價值觀的重要體現。精巧與細膩、古樸與拙雅等辯證藝術的方式,可不斷為漆畫藝術表現語言創造新的可能。
清代文藝理論家和語言學家劉熙載說:“古樸而近華,古拙而近巧。”這種語言技巧的境界就是漆畫藝術所追求的,它使漆畫表現與藝術上的油膩或華而不實劃清了界限,更加貼近宇宙間的生命本質。
北魏司馬金龍墓中出土的漆屏風,繪制題材多取自《列女傳》《孝子經》中的故事。在這一時期呈現的傳世精品中,人物裝飾技藝高超,手法純熟,線條自然流暢,如行云流水,造型生動質樸,極為傳神且富于特色,充分體現了漆畫藝術語言“大巧若拙,拙處見工”的藝術追求(如圖1)。

圖1 北魏漆畫屏風《列女傳》(局部)
(二)力避炫技
現代漆畫工藝不能脫離創作主體而獨立存在。無論哪一種藝術形式,其最終目標都是滿足人的審美等需求,脫離了創作者以及其對生活的體驗,藝術也就失去了賴以存在的肌體和魂魄。袁運甫先生認為:“空間中的藝術創作必須要考慮到在適應大多數民眾對待藝術的基本態度和理想追求的基礎上最大范圍地去實現創作者的藝術自由和美學理想,藝術作品的創作不能單純為了炫技而降低文化品格,違背根本宗旨。”
可見,在現代漆畫創作過程中不能片面地追求炫技,追求在技法上的感官刺激,絢麗浮華,空洞無物。它應是在中國傳統“重己役物”思想的統領下滿足主體的審美訴求。“重己役物”最早是由荀子提出,主張利用積極的態度來處理人與自然萬物的關系,調和在實踐中產生的矛盾。“重己”意指物為人所用,所以人是物的主人;“役物”就是自覺地駕馭和主宰物質。
中華傳統文化思想中這種始終把人放在主體位置的思想在哲學發展上具有進步意義,也與現代科技發展的要求相符合。
“重己役物”思想根植于傳統文化的豐厚土壤之中,現代漆畫需要以此為基礎進行藝術創作的探索活動。漆畫表現不管是采用哪種工藝技法或風格語言,在創作中都不能背離這種思想。
漆畫工藝以及其所表現的“物”要為人所用,要有利于人的生活,有利于實現人文價值。也就是說,在漆畫創作中,人是運用工藝的主體,不能為工藝所累,要讓漆工藝去適應人的創作需要,以此實現自我美學價值,最終達到更高的藝術境界。
在漆畫創作中,基礎的東西不掌握而空談藝術性,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但片面追求“技法至上”或忽視畫面的靈魂,“為了工藝而工藝”也是不可取的。不追求更高一層的藝術之魂,不飽含藝術家思維靈性的作品就是沒有情感與思想的作品,這樣的作品畫面空泛無物,陷入基礎技法的堆砌中,從而失去生命力,更不可能感動觀者。
如何避免炫技?
首先,明確創作主題。好的思想觀念是作品成功的必備要素,思想情感與審美標準在漆畫創作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不論是越南漆畫的成功經驗還是我國漆畫的發展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其次,重視“磨顯”但不迷戀。我們從許多現代漆畫佳作不難看出,漆畫制作過程與其他畫種不同,是間接通過“磨顯”表現藝術家的創作意圖,其風格顯現在“磨”的階段。有句話說得好,“磨即是畫”。研磨過程既有主觀性又有客觀性,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漆畫家要隨時注意改變和取舍,不能迷戀于“磨顯”材料,否則便是舍本求末,以偏概全。最后,我們要專注于畫面整體,明確材料和語言的意義。對于漆畫來說,習作也好,創作也好,都是如此。把眾多的漆畫語言組織在一起,通過層層“磨顯”,把材料美和語言美與藝術家的感受相結合,傳遞出漆畫家的情感與思想,表達其觀念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人性的認識。
總之,漆畫語言多種多樣,千變萬化,既有自身獨特的材料特性又有諸多繪畫所具有的共同特點,了解漆性,學習漆畫藝術語言是漆畫學習不可逾越的基礎階段,但更重要的是明確運用材料、語言的價值和意義。漆畫的畫面不能成為技法的展示臺,要努力擺脫單純的技法堆砌,在畫面中表現生活,在此基礎上表現對美的認識,借此展現作品的魅力。
(三)幻中有真
漆畫藝術創造的既是一種真實的世界,也是一種虛幻的世界,其是藝術家對客觀世界的主觀反映。一件藝術作品能否最大限度地構成藝術的感性時空,是驗證其感染力和創造力的標準。
吳可人幾十年如一日,探索漆畫語言的表現,成為中國現代漆畫的重要開拓者,創造了《馬蹄蓮》《雞冠花》《畢加索陶瓶里的黃色》等一系列代表作品。他的作品造型內蘊豐富,將漆畫語言表現得似真似幻,將幻中有真的表征升華到文化性的高度,為當代中國漆畫藝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漆畫作品《百合花》充分發揮了漆畫語言的優勢,使畫面意境純美,亦真亦幻,取得了其他畫種不能取代的效果。那美妙的“磨顯”肌理和令人神迷的色彩造成的虛幻空間中包裹著一個藝術家的真摯靈魂(如圖2)。作品幻中見真,將夢幻般的空間效果與觀者心靈融為一體,使觀者駐足在作品之前,生成一種難以用語言形容的藝術感受[3]。

圖2 漆畫《百合花》 吳可人/作
(四)有限中見無限
漆畫創作中的語言運用有著自己的獨特之處,但是與其他藝術創作一樣,要最大限度地拓展畫面張力,使造型和形象具有更深刻的內涵;同時將具體的“形”寓于聯想之中,于有限中見無限,創造永恒的瞬間,讓人們的記憶永遠定格在藝術家創造的靜止的畫面中,從而構成回味無窮、意蘊蕩漾的藝術情境[4]。
1984年第六屆全國美術作品展中,鄭力為的銀獎作品漆畫《拉網》(注:此屆沒有金獎作品)以黑紅色的對比和富于動感的畫面營造出了一種飽含生活氣息的場景,表現了惠安女辛勤勞作的情節,格調優雅,意境唯美,讓人產生無盡想象,成為一幅永恒的經典畫面(如圖3)。李永清的漆畫作品《永恒的記憶》榮獲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金獎,表現了一片籠罩在黃色調下的茫茫草原,雪山佇立,殘碑臥地,一支插在草地前方的樹枝直破蒼穹,鮮亮的黃色與肅穆的意境讓人過目不忘。雪山、草地、墓碑,不著一字卻形成無限永恒,它銘記著棲息于這片土地之下為革命而永生的靈魂。有形的畫面創造出無形的精神與品格,有限的場景讓人聯想起革命者前仆后繼、艱苦卓絕的斗爭畫面(如圖4)。在第十三屆全國美術作品展中,張玉惠的金獎作品漆畫《盛世花開》的畫面中央是枝繁葉茂、花開朵朵的參天大樹,大樹之下重點表現了新時代少先隊隊員,他們聚攏在樹前,與盛開的花朵相映生輝,有限的場景顯現著無限的生機,寓意少先隊員是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

圖3 漆畫《拉網》 鄭力為/作

圖4 漆畫《永恒的記憶》 李永清/作
三、結語
在民族文化復興的當下,我們要不斷思考漆畫創作中語言運用方面的諸多問題,借此總結經驗,不斷提高。我們需要在堅守漆畫自我語言體系的基礎上繼承其創作的美學追求和思維方式,使蘊含豐富的漆工藝技法的語言體系在實踐中能夠與人文精神充分結合,體現融合、創新的中國精神,呈現鮮明的特色。這對現代漆畫的發展來說,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