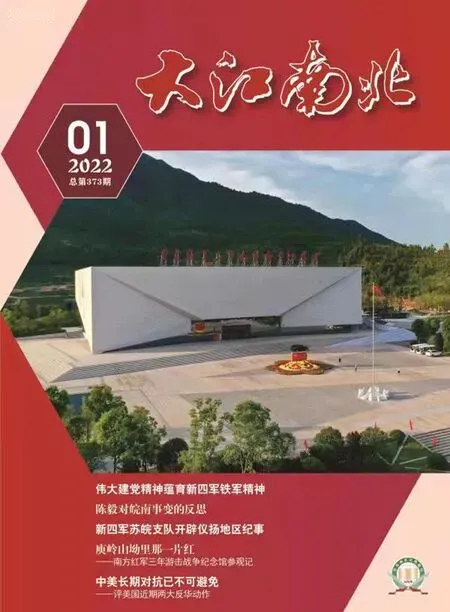新老洲:外表灰色的抗日根據地
奚兆堅 朱家躍
新老洲(即江鎮地區)地處隔江相望的江都(揚州)與鎮江兩地交接的邊緣地帶,位于長江主航道以北,霍橋、杭集一線以南,淮河入江水道以西,古運河以東。其主體范圍為橫亙在大江中的新洲與南、北老洲,也包括散布于江心的一系列小塊綠洲,是溝通蘇南、蘇北、淮南的重要水上交通樞紐。抗日戰爭時期,這里的黨政軍民為服務于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創建,承擔了保障共產黨與新四軍在人員、物資、情報信息等方面水上交通的特殊使命。并且,其獨特之處還在于這里既具有抗日根據地的一般特征,還根據抗日斗爭形勢的變化,適時地創建了以灰色面貌出現的抗日根據地,從而把這里建設成為新四軍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安全地往來于大江南北的“江中橋梁”。
1、新老洲灰色模式抗日根據地建設的必要性
1938年10月,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帝國主義把作戰重點轉向了共產黨控制的敵后根據地,國民黨蔣介石也加緊了對八路軍、新四軍的限制。在新形勢下,中共中央及時作出“開辟蘇北,發展華中”的戰略部署。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陳毅、粟裕等領導同志積極貫徹中央指示,及時籌劃并組織實施江南的新四軍北渡長江,開啟了建立蘇中抗日根據地的歷史進程,也賦予了新老洲作為重要渡江點的歷史使命。
當時,為慎重選擇新四軍北渡的渡江點,陳毅在管文蔚陪同下,于1938年10月中旬專程由鎮江大港渡江視察新老洲。經考察調研,陳毅認為,這里距離日偽重要據點揚州太近,且江面太寬,危險性較大,江對面又是游擊區,大部隊行動難以保密,故提出將揚中作為第一渡江點,新老洲作為第二渡江點,但新老洲“工作也不能放松”。出于政治家和軍事家的高度敏感性,陳毅首先將新老洲作為渡江點的安全問題放在了人們面前。而他指示的“工作也不能放松”則是要求新四軍指戰員和地方黨政組織要著重解決安全問題,努力把新老洲打造成安全高效的“江中橋梁”。
事實上,新四軍北上首先是從江南北渡至新老洲,此后在江都三橋兩蕩地區建立橋頭陣地。此時,新老洲的抗日武裝得到發展,民主政權得以建立,抗日團體紛紛涌現,各種抗日活動十分踴躍,根據地各項建設搞得紅紅火火,為新四軍北上東進提供了良好的服務。新老洲抗戰活動的蓬勃發展也引起了日偽軍的高度關注。1940年7月,新四軍主力東進后,日偽軍抓住新老洲抗日武裝大部隨主力東進、原地堅持力量比較薄弱的時機,發起大規模“掃蕩”,數路進犯,扣留船只,封鎖交通,抓捕留守堅持的黨政干部,并在頭橋、黑橋、高橋、八方橋、荷花池等處構筑據點,奴化人民。“掃蕩”以后,新老洲黨政組織遭到極大破壞,多名抗日干部遭到逮捕和殺害,黨領導的抗日斗爭全面轉入地下,而作為新四軍南北交通的重要渡江點深受影響,其保障南北水上交通的功能幾近喪失。
這段時間,遠離黃橋大根據地,地處日、偽、頑控制范圍內的新老洲,如何繼續發揮“江中橋梁”的作用,成為蘇中和蘇南乃至淮南的共產黨、新四軍急需解決的問題。1941年夏末秋初,日偽軍在蘇南實施“清鄉”,很快擴展到丹北地區。為使新老洲這條水上交通線在困難情況下不致中斷,10月,蘇中區黨委根據華中局的決定,將新老洲劃歸江南第四行政區管轄,由中共京滬路北特委領導。當月,建立中共長江工作委員會,負責發展黨的單線組織和建設長江中心秘密交通線工作。1942年1月,中共京滬路北特委決定建立江鎮工委(縣級),并明確指示工委的任務是:在保持該地區外表“灰色”的同時,積極進行根據地的各項建設,確保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新四軍部隊和黨的領導干部都能從此往來于大江南北,由此開啟了新老洲黨政軍民發揮聰明才智,在灰色面貌掩蓋下建設安全鞏固的“江中橋梁”、創建獨特的抗日根據地的歷史進程。
2、在新老洲建立灰色模式的抗日根據地的可能性。
首先,從新老洲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看,新老洲由長江中的一系列島嶼和沙洲組成,其面積不大,無論是日偽頑還是新四軍都不可能有大部隊在此區域常駐。新老洲距鎮江、揚州和仙女廟都不遠,處于這幾個重要據點的邊緣地帶,是日偽頑“三不管”的地帶。并且,樹木成林,修竹成蔭,隱蔽條件較好,適合建設灰色模式的抗日根據地。
其次,從新老洲當地住民的階級成分看,居于上層的主要是地主兼工商業者,這部分人占據當地大量土地,掌握著全洲的經濟命脈,不少人在幫會中還有著一定的地位。按照幫規,幫會成員要講江湖義氣,遇事抱團,一致對外。蘇北淪陷后,不少在幫會中任職的幫會成員成為當地偽鄉、保長。但是,幫會中也不乏一些具有民族氣節的愛國人士和開明士紳,他們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政策,是共產黨新四軍重要的統戰對象。在新老洲居民中,絕大多數是農民、漁民和船工。他們身居底層,長期飽受剝削、壓迫,有改變現狀的強烈愿望。這些貧苦群眾,一經宣傳、動員,階級覺悟和民族意識得到提升,就會成為保障共產黨新四軍水上交通暢通的主要依靠力量。
再次,從外部條件看,新老洲處于蘇南、蘇中、淮南三大抗日根據地的結合部,隨著三大根據地的不斷建設與鞏固,日偽軍既惱恨交加又疲于應付,其注意力也受到了極大的牽制。我方悄悄進行“江中橋梁”建設,就可避免引起日偽軍的關注,客觀上成為采用灰色模式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有利條件。
從1942年2月初起,至抗日戰爭進入全面反攻,江鎮地區歷任黨政軍領導班子經過不懈努力,多措并舉,探索并總結出一整套在灰色面貌下創建抗日根據地的經驗:
1、加強黨的建設,恢復和發展各級黨組織。江鎮工委領導成員分頭與江都縣委移交的秘密黨支部接頭,將分散在各地的黨員聯系起來。創建之初,江鎮地區的黨政領導干部全部分散群眾家中。他們通過深入基層將群眾中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培養為建黨對象,秘密發展了一批年輕黨員。至10月,黨支部發展到10多個,有黨員100多人。1942年2月底,日偽軍對丹北地區進行大“掃蕩”,中共京滬路北特委的黨政干部陸續轉移到江鎮地區。丹北黨政軍機關及大批干部進入新老洲,黨的組織得到快速發展,秘密工作延伸到這一地區的各個層面。1943年秋末,江鎮工委在天吉鄉舉辦了第一期黨員培訓班,歷時1個多月,培訓了一批黨的基層骨干。不久,新洲、南洲、北洲等區級黨組織得到建立和健全,此時,江鎮地區黨員人數已達250多人,黨支部發展到30個。1944年11月下旬,中共蘇中第五地委在新洲成立,下轄鎮江、丹陽、武進、澄西、揚中、江鎮6個縣。黨的組織加強了,各項工作便順利開展。
2、以統戰工作入手,加強對幫會的改造和利用。早在1938年新四軍武裝開辟新老洲時,新四軍就十分重視統戰工作,組織了各種抗敵協會,團結各界人士,爭取幫會勢力共同抗日。轉入創建灰色模式抗日根據地以后,如何在秘密狀態下爭取和利用幫會勢力是一個新的課題。從1941年下半年起,中共京滬路北特委即要求各級黨組織指定專人負責這項工作。特委成立“新生社”,幫助幫會改造幫規幫法,加入抗日內容,將青幫的“大通悟覺士”五個輩分改為“一心救中國”五輩。同時,派出黨的干部進入幫會開展工作。韋永義等領導干部作為黨在幫會中工作的代表,輩分很高,敵工人員就以他們的名義收徒弟,通過各種渠道動員偽軍、偽鄉保長、地主資本家地方實力派以及幫會的大小頭目送帖子、拜先生。這些人一經送了帖子,按幫會規矩就與改造后的幫會建立了聯系,共產黨就可以根據實際斗爭的需要,分別不同對象安排不同的任務,以達到保障抗日活動、掩護打入日偽內部中共秘密黨員安全的目的。
3、對頑偽人員爭取與打擊并重。江鎮工委還運用“打拉”結合的策略,開展對頑偽人員的工作,對新老洲在保持灰色面貌的情況下,爭取頑偽人員為我所用,保證新四軍南北交通的暢通發揮了較好作用。1942年四五月間,江鎮工委敵工站長宦明龍通過關系做通了黑橋據點偽軍副隊長和機槍班長的工作,使其成為抗日軍民的內應。當年冬,特區工委書記陳西光派濟福鄉兩面派鄉長耿詔與黑橋耿家花園的偽連長潘克持談判,在陳述利害得失后,要求其支持抗日,不得妨礙新四軍的活動,并保證抗日干部的安全。
對于死心塌地做漢奸和堅決與新四軍為敵的頑偽勢力,江鎮工委則果斷組織短槍隊將其消滅,不留后患。對于人數多、規模大的對象,工委就采取借請外部軍事力量的辦法組織實施。
4、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使其成為建設新老洲灰色模式抗日根據地的基本力量。江鎮工委和江鎮辦事處特別注重維護群眾權益,適時通過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爭奪灘田、筑堤圍田、借種補種、滅蝗救災、禁毒戒賭等項斗爭,解決群眾困難,改善群眾生活。針對地主豪紳將江水沖擊形成的沙灘占為己有,1943年春,江鎮工委發動了奪灘斗爭,由黨員和積極分子帶領群眾到鄉保長那里說理訴苦,同時工委積極爭取上層人物的同情和支持,江鎮辦事處也出面督促鄉保長和地主豪紳將灘田交給群眾。此后,新洲濟福鄉筑岸委員會又帶領群眾筑堤20余里,圍灘造田1700余畝,全部分給無田、少田的農民,使200余戶貧苦農民的生活有了著落。在對漁民、船工的工作中,工委派出多名秘密黨員深入他們之中,在灌輸革命思想的同時,與他們建立感情,很快就將漁民、船工組織起來。
5、掌控運輸載體線路,確保南北水上交通安全暢通。全洲實現了長江運輸載體的各種組織形式:一是全部掌控大橋、嘶馬到頭橋夾江邊的漁船和渡船,這是比較固定的運輸載體;二是對江中行駛的運輸民船的臨時征用,這是不固定的運輸載體,主要在新四軍大規模部隊過江時采用;三是擁有自己的交通運輸船,這些船數量不多,主要是隨時解決少數新四軍干部和部隊的過江問題。與運輸載體組織形式相適應,新老洲除建有多個水上交通站,還開辟各種形式的水上交通線,這些交通站、線,為共產黨和新四軍部隊在大江南北交通的安全暢通發揮著各自的重要作用。
新老洲抗日根據地歷史作用的發揮,從貫通大江南北交通的角度,按時間、內容和創建模式劃分,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38年7月至1940年底,主要是江南的新四軍主力渡江北上,開辟蘇北、發展華中。采用的模式,由表及里,都是紅色根據地。第二階段從1941年初到抗日戰爭全面反攻,主要是江北的新四軍南下東南各省發展敵后斗爭,這個階段基本采用的是灰色模式。而這兩個階段的銜接與轉換,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由弱轉強,抗日根據地從少到多、由小到大的歷史進程。
(編輯 李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