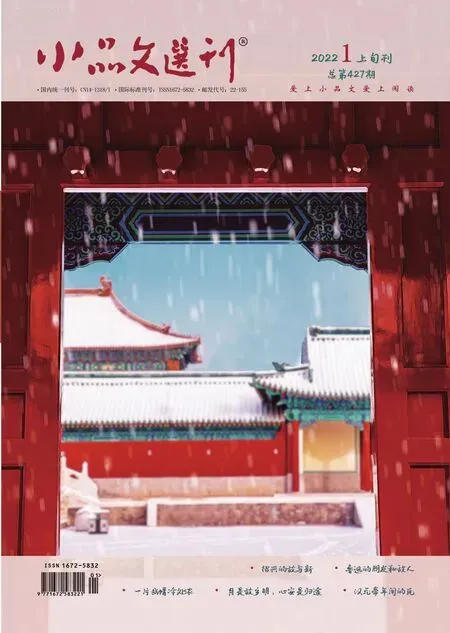一條河的時間書
李少巖
那個艷陽高照的秋日,我在呂家坪鎮(zhèn),遇見沈從文《長河》中的錦江河。
換作平時,與一條河的相遇,我起初的印象,總是停留在淺顯層面。很多時候,我的匆匆來去,有點浮光掠影的意味。細(xì)想,人這一生,會與許多江河劈面相逢,印象深刻能有幾許?與錦江河的會晤,我的解讀是多維的,寬泛的。此刻,在呂家坪鎮(zhèn)臨河碼頭,我持久地佇立,眼前這條名不見經(jīng)傳的河,因為沈從文《長河》的細(xì)膩文字,注定不再是一條簡單意義的河流。
一波,一波,清澈的河水輕柔地拍打碼頭,零零碎碎,濺起一串串俏皮的水花。一波未盡,又一波浪花來襲。頃刻間,原本洇濕的水印,被下一波浪花所涵蓋。水能洗去一切,歲月,塵埃,乃至世間物事。河流是大地的經(jīng)絡(luò),縱橫交錯,默默無聞地供養(yǎng)萬物。想象每一條河,從它誕生那一刻起,都在向往自己的遠(yuǎn)方,如同一個志存高遠(yuǎn)的人,遠(yuǎn)方總是他執(zhí)著不變的精神指向。
時光回溯。上世紀(jì)30年代,風(fēng)華正茂的沈從文,從故鄉(xiāng)鳳凰縣一路跋山涉水,行至水汽漫漶的呂家坪鎮(zhèn),這里的山,這里的水,以及淳樸善良的苗家人,一度讓沈從文疲憊的心得以安頓。在呂家坪鎮(zhèn)短暫居住,從喧鬧的碼頭出發(fā),搭乘聲名遠(yuǎn)播的麻陽船,由沅江匯入長江,一路北上,開啟他漫長的從軍模式。
一艘老船泊在錦江河岸,如一位垂暮、低沉的老人。在河之上,老船的表情呆滯,目光深邃,一派寂寥的神態(tài)。世間萬象,繁華落盡,終歸于沉寂。我想,老船一定在靜謐地反芻,那些曾經(jīng)有過的激情歲月。船與河,河與船,互為交集,兩者有著不可分割的語境。試想,讓一艘船遠(yuǎn)離河流,還有存在的意義?一條大河,如果沒有船的點綴,哪有自然、靈動的氣象?經(jīng)歷太多風(fēng)雨,老船的帆布已經(jīng)千瘡百孔,神色黯然,那架勢,再也經(jīng)不起風(fēng)雨摧折。一桿銹跡斑斑的鐵錨,頹然臥在船頭,與老船渾然一體,相依相守。唯有那根飽經(jīng)滄桑的桅桿,直插云霄,接近歲月的天空。
時間似一條奔流向前的河,每道人生碼頭演繹不同的劇情。多年以后,也就是1937年,在京任職的沈從文回到家鄉(xiāng)鳳凰,回首往事,當(dāng)他再一次來到呂家坪鎮(zhèn),故地重游,彌望浩蕩而來的錦江河,禁不住思緒萬千,文思泉涌。先生在呂家坪鎮(zhèn)一棟吊腳樓棲居一年時間,以這里的人物、物產(chǎn)、村寨、風(fēng)俗人情,創(chuàng)作了一部膾炙人口的名著《長河》。后來他在《長河·題記》里說,《長河》其實是“用長河流域一個小小碼頭呂家坪鎮(zhèn)作背景”來創(chuàng)作的。《長河》其中一個章節(jié)標(biāo)題就是《呂家坪的人和事》,足見呂家坪鎮(zhèn)在沈從文心中的位置,舉足輕重。
重讀經(jīng)典,很大程度說,就是穿越時間的長河,重溫大師筆下的往昔歲月,煥發(fā)我們更為廣闊的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閱讀沈從文的湘西散記系列,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先生曾在書中多次寫過麻陽船,以及漾在錦江河上空的行船號子。
立時,在我腦海浮現(xiàn)一幀清晰的歷史畫面:一艘滿載貨物的麻陽船,似一片巨大的樹葉,漂在錦江河上,兩岸青山,蔥郁如蓋,一位船工手持竹篙立在船頭,他裸露的脊背,黑里透紅,在炎炎烈日下呈現(xiàn)古銅的基色。船工敏銳地觀察遠(yuǎn)處的江面,在他寬闊的胸襟里,不僅掩藏給予遠(yuǎn)方的期許,也蓄滿對于家里妻兒老小的眷戀。自古人生有三苦:行船,打鐵,磨豆腐。行在水上的江湖漢子,走南闖北,不僅咽得了日常的苦辣酸甜,還能容得下命途的萬水千山。
一腔嘹亮的號子奔涌而出,粗獷,高亢,蕩在湍流江面上,揮之不去。
曉風(fēng)清新,天高云淡,我們一行人坐在老船上聊著長河。我向老船工劉本勤探問長河號子,為了滿足我的獵奇,年近古稀的老船工欣然應(yīng)允,他沉思片刻,即興吼起一曲長河號子,那氣勢,恢宏,激昂,抑揚頓挫,千回百轉(zhuǎn),聆聽完一曲,令人蕩氣回腸。劉本勤解釋道,長河號子主要分布于沅江、長江流域,它有約定俗成的基調(diào),卻沒有固定內(nèi)容,通常是船工在行船中看見什么,想到什么,就無所顧忌吼出來,形式不拘一格,語言通俗易懂。村莊,河床,青山,田地,村姑,險灘,都是船工們臨場發(fā)揮的題材,具有鮮活的生活氣息和濃郁的民族色彩。
秋陽下的呂家坪鎮(zhèn),祥和而寧靜。走進(jìn)逶迤的巷道,我想象的青石板、兩旁木質(zhì)吊腳樓已不復(fù)存在。我的心海泛起一波巨大的落差。很顯然,我到呂家坪鎮(zhèn),是來尋找沈從文的足跡。兩側(cè)參差不齊的鋼筋叢林,不時在我心里投下暗淡的影子。同行的劉本勤是本鎮(zhèn)居民,在巷子里開了一家工藝美術(shù)裝潢店,他不無惋惜地告訴我,明清以來,這里原本清一色的木質(zhì)吊腳樓,屋連屋,檐接檐,即便多雨季節(jié),你從鎮(zhèn)上走過,也不會濕腳。上世紀(jì)90年代,一場滔天洪水將鎮(zhèn)上的木樓席卷一空,遍地狼藉,慘不忍睹。令人稱奇的是,在古鎮(zhèn)一隅,當(dāng)年沈從文棲居的那棟木樓,經(jīng)歷那場洪流的肆虐,安然無恙地留存于此。命理天象,誰解其意,世間諸多物事,有多少能夠揣摩明白?
循著一條崎嶇小徑,我們來到一棟陳舊的木樓前。舉目仰視,門楣上懸掛一塊字跡斑駁的牌匾:沈從文舊居。年長日久,木樓已經(jīng)頹敗,清寂,寥落,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夾在兩側(cè)高樓間,顯得有些格格不入。我不禁臆想,這是先生創(chuàng)作《長河》的棲居地?這么低矮狹小的空間,青燈黃卷,墨香氤氳,有多少愛恨情仇的故事在此醞釀、躍然紙上?
我欲進(jìn)屋拜謁,門扣掛著的銹鎖,將我拒之門外。我恍然醒悟,先生仙游去了。我縱然進(jìn)屋搜尋,再也找不到先生的一腔文脈。而我記住了這棟木樓,這個偏遠(yuǎn)的湘西小鎮(zhèn)。
呂家坪鎮(zhèn)在湖南麻陽縣,沈從文與呂家坪之間的趣聞軼事,寫進(jìn)泛黃的時間書。每一次打開,文氣繚繞,一幅淡雅雋永的湘西人文畫卷,撲面而來。
選自《湖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