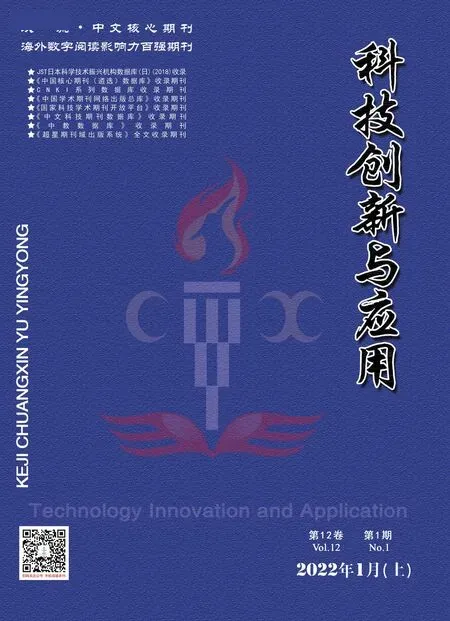廣州市增城區(qū)洪澇成因及防治對策
胡永輝
(廣州市增城區(qū)河湖庫管理所,廣東 廣州 511300)
在全球氣候變化與城鎮(zhèn)化快速發(fā)展背景下,中國城市洪澇災害日益嚴重[1-2]。2020 年廣州市“5·22”暴雨期間,廣州市黃埔區(qū)、增城區(qū)遭遇特大暴雨,多地出現(xiàn)嚴重“水浸街”現(xiàn)象,增城區(qū)新塘鎮(zhèn)受近兩年城市開發(fā)強度大、城市更新建設快的影響,鎮(zhèn)內官湖河、溫涌、雅瑤河流域受災最為嚴重(圖1),其中廣園路與開創(chuàng)大道交叉口最大淹沒水深達3.24m,最大持續(xù)時間達24h。

圖1 增城區(qū)溫涌、官湖河、雅瑤河流域
近年來關于城市暴雨洪澇災害已有大量研究,張建云[2]等分析了城鎮(zhèn)化發(fā)展對暴雨洪水頻發(fā)的影響;伍志方[3]等對2017 年廣州市“5·7”特大暴雨的天氣尺度系統(tǒng)和可預報性進行研究;王偉武[4]等從城市氣候、城市規(guī)劃、城市管理等多個角度提出城市內澇成因及防治對策;張欣[5]等通過設計暴雨推求2020 年廣州市“5·22”洪水等級。廣州季風氣候突出,出現(xiàn)強降水機制復雜[6],城市洪澇災害制約了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產生威脅,各區(qū)域地理環(huán)境、氣象條件及土地利用方式等存在差異,需要相關部門提出因地制宜的防洪減災措施。各城市洪澇災害的成因有共性也有特性,對廣州增城區(qū)“5·22”特大暴雨的研究較少。本文以2020年廣州“5·22”特大暴雨災害為例,分析廣州市增城區(qū)暴雨洪澇災害產生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防洪減災對策。
1 廣州市增城區(qū)洪澇災害成因分析
1.1 自然因素
1.1.1 流域洪水超標
廣州市屬于海洋性亞熱帶季風氣候,受海陸氣溫差異影響,降水主要集中在4-9 月。通過查算《廣東省暴雨徑流查算圖表》使用手冊和《廣東省水文圖集》(2003 年版)求得各時段流域中心點暴雨均值和Cv 值,計算雅瑤河流域設計點雨量,計算成果見表1。“5·22”暴雨1h 降雨量為20 年一遇,3h 降雨量超100 年一遇,6h 降雨量約為100 年一遇,24h 降雨量約為50 年一遇,增城區(qū)雅瑤河流域周圍實測降雨如表2 所示,綜合評判本次降雨超100 年一遇標準。此次降雨具有超標準、雨強大、歷時短、總量大等特點,降雨所產生的徑流超過現(xiàn)狀防洪排澇標準,是造成各片區(qū)發(fā)生嚴重洪澇災害的主要原因。

表1 設計點暴雨成果
1.1.2 地勢低洼易澇
增城區(qū)暴雨受災最嚴重區(qū)域為增城區(qū)埔安河流域、永和河流域及雅瑤河流域,淹沒區(qū)地勢低洼易澇。此次雅瑤河淹沒區(qū)域主要位于荔新公路以南、廣深鐵路以北的地勢低洼區(qū)域,排水能力差;永和河及埔安河流域上游西北方向多為山地,地勢較高,水流隨著地勢降低往平原區(qū)匯集,最終匯入東江北干流。永和河沿岸部分村落地勢低洼逢暴雨必淹,平均高程3~4m,2017 年“5·7”暴雨淹沒水深約0.5~0.7m;“5·22”暴雨永和河洪水位4.56m,淹沒水深達到1.3~3.0m,下游洼地多無法快速排出暴雨積水;埔安河流域內淹沒區(qū)域位于北部環(huán)形山區(qū)匯流必經出口,部分區(qū)域為局部地勢低洼區(qū)域。增城區(qū)雅瑤河淹沒片區(qū)態(tài)勢如圖2 所示。

圖2 增城區(qū)雅瑤河淹沒片區(qū)態(tài)勢
1.2 人為因素
1.2.1 下墊面硬化加劇
城市化建設進程中改變了下墊面的特性,地表徑流系數(shù)降低,使降雨強度加大,雨量分布更為集中,加劇了洪澇災害的危害。根據(jù)近年來的遙感影像圖顯示,流域中上游的大量農林草地建設為城鎮(zhèn)并仍在不斷開發(fā)建設中,中上游土地的蓄水保水能力大幅下降,而流域下游的淹沒區(qū)周邊也在不斷建設,城鎮(zhèn)建設密集,地面硬化,流域內天然蓄滯洪區(qū)蓄水功能消失,徑流系數(shù)增大。增城區(qū)永和河流域2000-2020 年遙感影像如圖3 所示。

圖3 增城區(qū)永和河流域2000-2020 年遙感影像圖

表2“5·22”實測降雨統(tǒng)計表
1.2.2 排澇體系不完善
增城區(qū)各流域防洪排澇標準低,排水系統(tǒng)維護不到位,水系復雜、橋梁阻水、流路不暢等問題較多。雅瑤河上游河道整治而下游河道未整治,上游河道拓寬使洪水歸槽效應明顯,加大了洪水下泄的流量以及下泄速度,導致下游強降雨與超標準洪水流量疊加,加重災害。兩岸堤防體系未閉合,部分堤防現(xiàn)狀并未達標,河道上下游、左右岸堤防差異較大,堤防缺口明顯。永和河未經系統(tǒng)治理,水系紊亂、流路不順,現(xiàn)有未設防,未形成封閉的防洪圈,有堤河段多為土堤,堤身低矮,防洪標準低。兩岸地勢低洼,自排條件差,現(xiàn)有排澇站排澇能力不足,水閘年久失修,無法及時開啟排洪。埔安河上游水庫大壩安全等級較低,未能發(fā)揮洪水調蓄作用。洪水發(fā)生時,為了保證大壩的安全穩(wěn)定運行,必須打開泄水涵管同步放水,不能對壩址以上天然來水進行有效調蓄以減輕下游河道的行洪壓力。
1.2.3 城市化建設加快
城市開發(fā)建設影響河道行洪,河道內存在行洪障礙物,河槽內橋墩等違章建筑物阻礙泄洪。區(qū)域內存在多處行洪卡口縮窄河道斷面,影響河道行洪。“5·22”暴雨洪水期間,由于橋梁底低阻水,水位迅速壅高,部分河道內布置有橋墩,洪水期間阻水更為嚴重。上游河涌水系被堵塞或填埋,局部河道淤積嚴重,導致暴雨洪水向下游匯集。河道主汊淤積和萎縮,行洪斷面被侵占,泄洪嚴重不暢,壅水嚴重,應對超標準洪水防御能力有限。增城區(qū)雅瑤河水系現(xiàn)狀如圖4、圖5 所示。

圖4 增城區(qū)雅瑤河行洪卡口點

圖5 增城區(qū)雅瑤河上游建設導致水系連通被破壞
2 城市暴雨洪澇災害綜合防治對策
防洪排澇必須流域統(tǒng)籌、系統(tǒng)治理,防外洪、排內澇一體化考慮。當流域內發(fā)生暴雨洪水時,應加快工程措施建設,完善暴雨洪水預警預報體系,加強海綿城市建設,多部門聯(lián)合協(xié)作提升特大暴雨洪水應急、避險、處置等能力。
2.1 加快水利工程建設,提高設計標準
目前防洪排澇的基礎設施標準低,水系紊亂,需加快推進河道清淤疏浚,拓寬河道過水斷面,恢復河網水系連通,盡快完成支流河涌達標整治。加強河道維護和水利工程管養(yǎng),對阻水構筑物及時清除,定期對水閘及箱涵維護,增設擋墻、堤防補缺加高以加快洪水快速下泄、減少洪水漫堤,提高河道防洪排澇標準。結合調度運行規(guī)則的要求,實現(xiàn)水庫、水閘和泵站等的防洪工程(設施)的聯(lián)合調度,在暴雨洪水到來之前進行水庫和河道的“預騰空”。對流域內水庫、水閘、泵站做好管養(yǎng),出現(xiàn)問題及時維修加固,保障水利工程防洪功能。不斷推進泵站、箱涵等基礎排澇設施的管養(yǎng)和擴建工作。建立健全各項管理制度,加強防洪工程的規(guī)范化管理。
2.2 加強監(jiān)測設備現(xiàn)代化,強化災害預案體系
洪澇災害可通過現(xiàn)代化設備提前監(jiān)測預警,為防洪排澇爭取寶貴的時間進行技術指導。可通過加強流域上中下游水位、流量及路面積水監(jiān)測等工作,在地鐵站等重點易淹區(qū)域布置監(jiān)測點,構建監(jiān)測預警系統(tǒng)。加強洪水風險圖的編制和應用及超標準洪水防御方案研究,全面實現(xiàn)“從注重災后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減少災害損失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為洪澇災害風險管理提供基礎依據(jù),據(jù)此對工程調度、搶險排險等進行指導,為人員和財產轉移贏得時間和主動權。
2.3 加強海綿城市建設,提高調蓄能力
城市化進程加快,下墊面急劇變化導致匯流過程發(fā)生顯著變化。在新型城鎮(zhèn)建設過程中應高度重視城市化對地區(qū)水文特征的影響,采用低影響開發(fā)建設模式,督促建設區(qū)嚴格按照國家海綿城市的要求對已建廠區(qū)地面進行改造,對擬建和未建廠區(qū)進行嚴格審批和監(jiān)督。加大城市徑流雨水源頭減排的剛性約束,優(yōu)先利用自然排水系統(tǒng),建設生態(tài)排水設施,充分發(fā)揮城市綠地、道路、水系等對雨水的吸納、蓄滲和緩釋作用,使城市開發(fā)建設后的水文特征接近開發(fā)前,有效降低城市的洪澇風險。
2.4 建立應急工作領導組,多部門聯(lián)合協(xié)作
設置應急管理小組,明確人員組成和責任劃分是促進各管理部門統(tǒng)籌協(xié)作、保障強化應急工作展開、保證洪澇災害防御和應對工作有序、高效開展的關鍵。各部門根據(jù)監(jiān)測預報分析結果,設置洪澇災害實時報告制度,部門間應加強溝通,相關應急部門做好防汛措施,加強巡邏,做好緊急管理調度工作。各行各業(yè)應增強防汛意識,加強暴雨洪水防御方案、應急預案編制和應急演練,建立水利專家顧問制,統(tǒng)籌各行各業(yè)汛前檢查和工程日常管理。同時建立信息溝通與共享機制,加強多部門、多層面的協(xié)作聯(lián)動。
3 結束語
通過對增城區(qū)三個流域片區(qū)“5·22”暴雨洪水的調查發(fā)現(xiàn),受災片區(qū)自身地勢低,流域遭受超標準洪水,下墊面硬化導致蓄滯能力不足是引發(fā)洪澇災害的主要原因,繼而導致流域內河道嚴重卡口造成洪水漫堤,最終造成了嚴重經濟財產損失;另外,水利設施防洪排澇標準低、設施陳舊,水系格局改變、水流不暢是導致洪澇災情加劇的重要原因。結合受災區(qū)特點提出洪澇災害防治對策:提高防澇設施標準、利用現(xiàn)代化設備預警、改善城市下墊面條件等,同時推動社會公眾積極參與來減少災害損失,提升應對特大暴雨的能力,以保障區(qū)域洪澇安全最大化降低超標準暴雨造成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