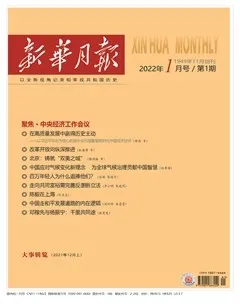司法反家暴的兩個困難需引起重視
陳敏
2021年11月25日,是國際消除針對婦女的暴力16日行動開始的第一天。北京市某律師事務所公眾號發布《“看不見、聽不到”的家庭暴力——2017—2020年千份涉家庭暴力離婚判決書分析》一文。其數據來源是Alpha-法律智能操作系統數據庫。標題中“看不見”的意思是,在離婚案件審理中,原告提供了受家暴證據,法院“看不到”證據的證明力。“聽不到”的意思是,原告寄希望于通過離婚來擺脫家暴,但法院即使認定家暴,也不一定判離,是“聽不到”家暴受害人迫切的訴求。文中提到,在全部1073起涉家暴離婚判決書樣本中,只有66份認定了家暴,認定率僅為6%,但即使是在被認定存在家暴的案件中,也有24%的案件被判不離。在未被認定家暴的余下94%的判決書中,有的家暴證據被認定為“家庭糾紛”,有的被認定為“證據不足”,還有的是“互毆”,多數情況下則未予回應。報告分析認為,法官在審判這類案件時存在理念和技術方面的不同認識。
該公眾號2021年4月還發了《179起人身安全保護令:看見家暴受害者的困境》一文,討論了法院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其編者按中寫道: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統計數據,2016年3月至2020年12月底,全國法院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7918份。其正文聚焦于上海法院五年來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情況。報告分析認為,主要原因也是法官在理念和技術方面存在不同認識。我國約有3000家基層法院,假設每個法院一年簽發一份人身安全保護令,在反家庭暴力法實施五周年之際,至少也能簽出1.5萬份。從數據看,這個簽發數確實不高。
上述兩篇文章作為民間法律機構對我國反家庭暴力法實施五周年狀況的監測的一部分,確實看到了家暴受害人的困境和法院反家暴工作存在的困難。
其實,法院也一直在關注自己在這方面的工作進展。比如,2021年全國法院第三十三屆學術討論會專門將“涉家庭暴力家事案件審判相關法律問題研究”作為選題之一。據了解,共有三十余篇論文就這個選題進行了討論。論文呈現的情況比上述兩篇監測報告呈現的情況稍微好一些(比如,數據顯示,不同法院在離婚案件審理中對家暴的認定率沒有超出12%),但沒有特別大的出入。
反家暴,特別是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源于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通過編寫《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審理指南》而開展的試點工作。參加試點的法院本著司法為民的初心,在還沒有反家庭暴力法的情況下,努力尋找間接法律依據,發揮司法的能動作用,開展反家暴試點工作,并堅持了8年。試點法院的數量從開始時被指定的5家到后來主動參加的200余家,充分顯示了各地法院明確的反家暴立場、堅定的決心和行動。目前的不盡如人意,確實是因反家暴理念和技能培訓不夠所致,需要進一步加強,但還有兩大困難,是法院自身無法克服的,筆者認為也需要被看見。
反家暴理論和實踐告訴我們,家庭暴力的驅動力是權力和控制。離婚案件中家暴實施者絕大多數是男性。他們用家暴控制妻子,認為這是家務事,外人沒有權利管。如果妻子被打得受不了,去起訴離婚,法院應當調解和好。調和不成的,就應該判決不許離婚。如果被判離,就遷怒于承辦法官,這是施暴一方典型的思維和行為模式。由于家事法官在審理涉家暴案件過程中缺乏特別保護,施暴人威脅、辱罵、糾纏、反復信訪、甚至暴力報復承辦法官的現象屢見不鮮。如果施暴方采用上述手段依然不能實現控制判決的目的,法官就會成為其精神暴力和軀體暴力的實際承受者。有一件事讓筆者至今印象深刻。一位法官判決了一起涉家暴離婚案當事人離婚后,女方立刻逃離當地,隱藏行蹤,男方找不到前妻的蹤跡,隔一段時間就在網上辱罵承辦法官,半夜用不同的手機號給承辦法官打電話和發短信,騷擾、威脅說自己知道法官的女兒在哪里上學。這種行為連續幾年不消停。其間,法官報警,警察表示無能為力,因為對方還沒有把威脅付諸行動,警察無法阻止未發生的行為。法官陷入困境,工作和心情都受到嚴重影響。更嚴重的是,2020年11月,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雙城區人民法院周家人民法庭庭長郝劍被他3個月前判決離婚的一起案件的當事人殺害;2016年2月,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法官馬彩云被她2年前判決離婚的一起案件的當事人殺害;2017年2月,廣西壯族自治區陸川縣人民法院退休法官傅明生被他22年前判決離婚的一起案件的當事人殺害。這些是其中被報道的典型例子。這實際上,是施暴人的暴力控制已經從婚姻關系延伸到訴訟關系,承辦法官及其家人也成為其施暴對象。當承辦法官意識到認定家暴就要判離婚,判離,等于將自己和孩子等家人置于施暴人的暴力威脅中,在法院自身無力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法官人身安全時,法官不敢貿然判決離婚。家暴受害人數次起訴離婚被判不離的現象,現實中就很難避免了。
國際社會早已達成的共識是,一線反家暴工作是高危職業,而涉家暴案件審判工作,屬于高危中的高危。許多國家早就有專門的適用于法官的民事保護令制度。在我國,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更未被列入解決的議事日程。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護令后,應當送達申請人、被申請人、公安機關以及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等有關組織。人身安全保護令由人民法院執行,公安機關以及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等應當協助執行。但是,在法院既無法律授權,也無人力配備、無法快速反應、更無配套機制的情況下,讓法院自行執行人身安全保護令的規定,本身是很困難的。
首先,我國民事訴訟法僅授權人民法院執行涉及財產支付性質的裁定,但從未授權人民法院執行涉及公民人身權利的裁定。人身安全保護令是一項涉及公民人身權利的裁定,讓法院自行執行,勉為其難。其次,現行法律對司法警察的定位,是審判輔助力量,其履職行為被嚴格限定在審判和執行秩序維護范疇。而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的行為,則是發生在法院以外的社會生活區域,司法警察無法到法院之外的地方去執法,更因為司法警察與24小時備勤的公安警察不同,無法快速反應、及時制止正在發生的家暴行為。另外,人民法院本身不設關押場所。拘留了施暴人,就需要送往當地看守所,如果當天看守所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接收,人又不能放,法院就會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當法官意識到自己簽發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很可能被違反,而懲罰難度過大時,結果是可預期的。如果施暴人還威脅法官及其家人的生命安全時,結果更是不言而喻。當年反家庭暴力法把執行人身安全保護令的職責賦予法院時,就相當于把法院、法官和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框到一起,結果必然大大削弱了該法所能發揮的實際效果。
國際社會通行的做法是,法院只管簽發民事保護令,不管民事保護令的執行。我國臺灣地區的法院也只負責執行涉及金錢給付、子女探視和加害人處遇計劃,“其他保護令之執行,由警察機關為之”。
綜上,法官需要接受理念培訓以提升反家暴技能,同時,法院自身無法克服的困難也需要被關注反家暴的社會各界看見。在未來的日子里,只有社會各界一起努力,推動反家庭暴立法第三十二條的修改,將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執行主體改為有法律授權、有人員配備、有快速反應能力、有配套機制的公安機關,并且建立法官人身安全保障機制,法院才會更有能力保護家暴受害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摘自2021年12月7日《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