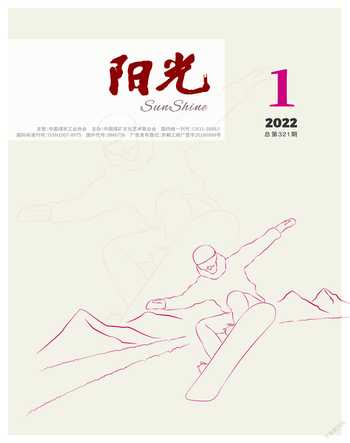詩歌的有限責任(創(chuàng)作談)
王夫剛
詩歌似乎已經(jīng)不足以在時代的快餐店單列一章了,它遇到的并非瓶頸,而是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只有那些守住底線的詩人還能稱之為詩神的知音、詩歌的布道者,但淺嘗輒止的好奇心認為,自我證明屬于無效的出庭辯護——微信勢不可擋,欲望浩浩蕩蕩,沒有來由的驕傲剛好配得上百花齊放的自戀,為了取悅一臺不斷降價的智能手機,對提升詩意指數(shù)幾無作用的龐大的寫作群體,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投誠,嘻嘻哈哈地構成娛樂的一部分。那位搖搖晃晃爆紅的詩歌愛好者就把范仲淹和柳永、海子和汪國真混為一談,情不自禁或者別有用心地宣稱,她救詩歌于寂寞。
當然,為娛樂提供服務沒什么,跟娛樂沆瀣一氣也沒什么,古往今來,滄桑有道,詩歌居草堂而令殿宇思緒萬千,處江湖而得寸心風輕云淡,從來不憚于跟一部分人講品質(zhì),講血統(tǒng),講道理和被誤解的道理,講閉門造車的野心在土崩瓦解之前所產(chǎn)生的一意孤行的優(yōu)越感,一如法國人波德里亞所言:“寫作是一項不人道和難以理喻的活動,在這項活動中,必須始終帶著某種蔑視。”詩歌的有限責任,此為一種。
詩人寫作,能否獲得李杜蘇軾等前輩同行的間接稱許,勤奮不可缺失,孤芳自賞不可缺失,天賦格局首先不可缺失——這么說吧,偉大的詩篇向來跟固執(zhí)(波德里亞使用的是“蔑視”一詞)有關,而固執(zhí)向來沒有討價還價這個選項——那些試圖用開會乃至開大會的手段強行介入詩歌、使用詩歌、臧否詩歌的做法,屬于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傲慢一廂情愿地夸大了權力的“春藥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詩歌的固執(zhí)和權力的傲慢是兩回事,前者的褒義含量高于貶義含量,而后者正好相反。花草溫柔,裁紙刀咄咄逼人,獨木橋的孤單和陽關道的熙攘各得其所,我們在現(xiàn)實中經(jīng)歷人性的美好和丑陋,詩歌在現(xiàn)實的隱形理想中記錄人性的美好和丑陋,情況就是這樣,“歷史”已經(jīng)安全著陸,未來還在靜待“后歷史”的審查通過。在人類的已知命運中,物質(zhì)因為物質(zhì)的屬性而門庭若市,靈魂起義因為靈魂的天馬行空而被普遍視為喪失了與物質(zhì)對峙的直接功能,盡管如此,詩歌仍然需要像哲學那樣,立字為據(jù)地回答“是”和“不是”的專項提問,阻止詞語的空轉,把無病呻吟的抒情和心懷鬼胎的非詩歌訴求逐出有薩福和博爾赫斯出席的人間詩會,否則,將是詩人的失職未被處罰,是波德里亞的提醒遭遇粗暴對待,他告訴我們,“如果一切都是完美的,語言就沒有用處。”
很顯然,生活距離完美還很遙遠,語言距離沒有用處還很遙遠,人類距離生命的頂格抵達還很遙遠——在貌似風起云涌的時代,談論詩歌的有限責任,其意義遠勝于談論詩歌的無限責任,如果我們是有坐標的詩人,就不會沾沾自喜地消費寫作經(jīng)驗,而是致力于“帶著某種蔑視”創(chuàng)造寫作經(jīng)驗,在“我的暴力”和“我們的民主”之間建設緩沖區(qū),像接納稀釋的贊美和不設門檻的狂歡那樣拒絕稀釋的贊美和不設門檻的狂歡:總有一些苛刻被指責,總有一些寬容需要在垃圾處理廠安身立命,生活才能津津有味,生命才能新舊有別。
王夫剛: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首都師范大學駐校詩人,詩刊社中國詩歌網(wǎng)編輯。著有詩文集多部,曾獲齊魯文學獎、華文青年詩人獎、柔剛詩歌獎和《十月》詩歌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