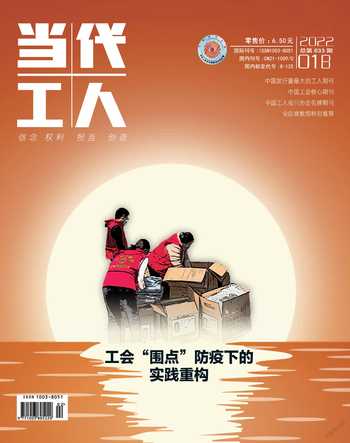用三天治愈童年
汪磊

用叔本華的悲觀主義論調,我們可以對人生發出這樣的感慨:孤獨是肯定的、絕對的、永恒的,而相伴是否定的、相對的、短暫的。
《小媽媽》是一部關于孤獨的電影。小女孩奈莉的外婆去世,她隨父母回外婆家收拾舊物。第二天,奈莉的媽媽不辭而別,留下奈莉和爸爸。
這是電影開始部分的內容,也是整個故事的背景。觸發故事的核心事件是媽媽的離開。媽媽為什么離開,影片沒有直接說明,爸爸只是說:“她今天早上離開了,我們覺得這樣比較好。”爸爸是理解原因的,卻沒有告訴奈莉。
影片敘事采用兒童視角,大量近景鏡頭聚焦在奈莉身上。電影的場面調度,使觀眾在狹小的房間場景中時時感到無力,這正是兒童身處成人世界中的感受——他們仰視著高大的父母,而父母腦中的思想高高在上,秘不可宣。
奈莉的表現,并不像一個兒童:失去外婆之后,媽媽陷入悲慟不能自拔;奈莉失去了外婆,又“失去”了媽媽,情緒看起來卻十分穩定。她似乎對至親離開后的真空產生了免疫。
影片大部分情景沒有背景音樂,劇情被緊緊限制在一種平靜、內斂的氛圍中。即使媽媽離開之前,餐桌上也氣氛冷清,一家三口的日常對話十分平淡,沒有一般家庭電影里溫馨歡樂的感覺。其中一幕,奈莉對爸爸直言:“你從不說自己小時候的故事。”爸爸則小聲告訴奈莉,他以前很怕自己的爸爸。而媽媽無聲的離開,也表明奈莉和父母的關系并不親密。她早已適應親情的疏離,也適應了作為兒童,被忽視在成人生活間隙的孤獨。
直到奈莉從房子出來,進了樹林,遇到年紀相仿的小女孩瑪麗安,敘述視角才開闊起來。瑪麗安是奈莉媽媽的小時候,即“小媽媽”,兩個小演員實為雙胞胎,電影用紅藍兩色衣服和不同的發型區分二人(紅色較藍色強勢,代表媽媽瑪麗安)。瑪麗安帶奈莉去她搭建的小樹屋,印證了媽媽曾和奈莉說過的話,也為奈莉認出“小媽媽”提供了線索。
孤獨使人早熟。和父母相處時,奈莉儼然一副大人的思考方式;而在瑪麗安面前,她找回了一顆童心。她們一起玩耍時的歡笑聲,才讓人發覺這是兩個孩子。這一點,身為母親的觀眾一定能更敏銳地察覺。
家庭教育是一個人成長中最重要的教育,然而許多父母并不懂得如何與自己的孩子相處。成年人的傲慢阻止了我們用兒童的思維方式去思考,進而和他們平等交流,深入他們的內心。但人是社會性動物,難以忍受孤獨,他們渴望融入群體,特別是家庭,這一點在自我邊界狹小的兒童身上表現尤為明顯。片中此前一系列細節表現了奈莉對媽媽的依戀:在去往外婆家的路上,奈莉親昵地從后座將零食塞進媽媽的嘴里;媽媽翻看小時候的字畫,奈莉主動贊賞;半夜起床喝水,見媽媽睡在沙發上,奈莉鉆進媽媽的懷里……而媽媽對奈莉的關注仍然不夠,她雖然愛女兒,卻不多傾訴。在奈莉看來,媽媽的心里藏了太多秘密。
沉浸在失去親人痛苦之中的人,通常會經歷一段強烈的自我關注期,這抑制了其對他人的付出,甚至對自己的子女。奈莉不懂心理學,她只能從兒童的視角去嘗試認知媽媽的感受和自己的處境。為了進入媽媽的內心,理解媽媽對外婆的情感和媽媽離開的原因,影片為奈莉設置了時空交錯的情景,這也讓身為父母的觀眾,能夠親身體驗一個被我們忽視的身邊世界。
奈莉和瑪麗安共處了三天。第一天,奈莉遇到正在搭建樹屋的瑪麗安,下雨了,她跟隨瑪麗安來到一幢酷似外婆家的房子——兩人的房子分別位于林間小路的兩頭,實則是處于不同時間的同一所房子。瑪麗安告訴奈莉,她的媽媽和奈莉有著一樣的名字,這說明瑪麗安非常愛自己的媽媽和女兒。
在“過去時”的房子里,年輕的外婆和瑪麗安的溝通同樣寡淡。我們可以看出,奈莉父母的童年都不被關注,二人組成的家庭也繼承了這一傳統,所有家庭成員對此處之泰然。但習慣不代表喜歡,當瑪麗安提出想去奈莉家時,被奈莉拒絕,理由是那里氛圍不佳,“我媽媽離開了。”
樹屋建成后,奈莉將自己身份的秘密告訴了瑪麗安,她還帶瑪麗安去了“現在時”的房子。談論起奈莉已過世的外婆,兩人共同引用了她的一句話:“好像自己明天就會死,這也許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這正是從前的瑪麗安、現在的奈莉媽媽對生活缺少信心、隔離自己的源頭——媽媽受外婆影響,始終活在無常的陰影下,長大后也難以對最親密的人敞開自己。
影片中,奈莉對瑪麗安說:“秘密不是我們想拼命隱瞞的事情,而是我們沒有任何人可以訴說的事情。”
這便是孤獨的感受。
兩個女孩共處的最后一晚,奈莉陪瑪麗安過生日。瑪麗安讓奈莉和外婆唱了兩遍《生日快樂》歌,其中一首獻給另一個時空的自己,因為這一天也是現實中媽媽的生日。第二天,女孩們劃船穿過一座金字塔般的水上建筑,這時,振奮的背景音樂響起,象征母女齊心突破了時空和內心隔閡,達成情感上的統一。
片末,現實中的奈莉與長大的媽媽互相呼喚姓名,母女也達成了情感上的統一。影片巧妙地用“互文”手法,圓滿收尾。
《小媽媽》的導演瑟琳·席安瑪,善于從女性視角解讀女性心中細膩、柔軟、兇猛的愛情,這部影片也可以從女性主義角度做出一番解讀。但兒童是無性的,因此它更是一部關于離別、孤獨和回歸的電影。近年來,網上對于原生家庭的分析熱度高居不下,電影用獨特的敘述語言,打通了一條通往童年的小徑,讓身為成人的我們直面兒童時代的孤獨,并試圖治愈自我。
【超鏈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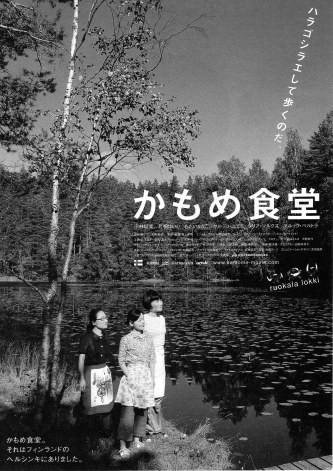
《海鷗食堂》(2006)
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某個街角,日本女子幸惠逃避現實遁居于此,開了一間食堂。在這里,她陸續遇到一些不那么典型的人與事,并建立了新的羈絆。《小媽媽》是家庭中的孤獨,《海鷗食堂》則是離家的孤獨,此域彼域,看似平和的生活之下,悲傷處處一樣。但質樸生活,友善待人,或能找到心靈棲息之地。

《你好,李煥英》(2021)
和《小媽媽》劇情有相似之處。剛考上大學的賈曉玲遭遇意外,深陷悲痛,穿越回1981年,與年輕時的母親李煥英相遇。賈曉玲想利用自己的時空優勢讓母親有所成就,但命運卻自有它的意志……中國式母女感情模式更容易引起觀眾共鳴,合格的喜劇電影不僅使人歡笑,還能啟發觀眾關注身邊的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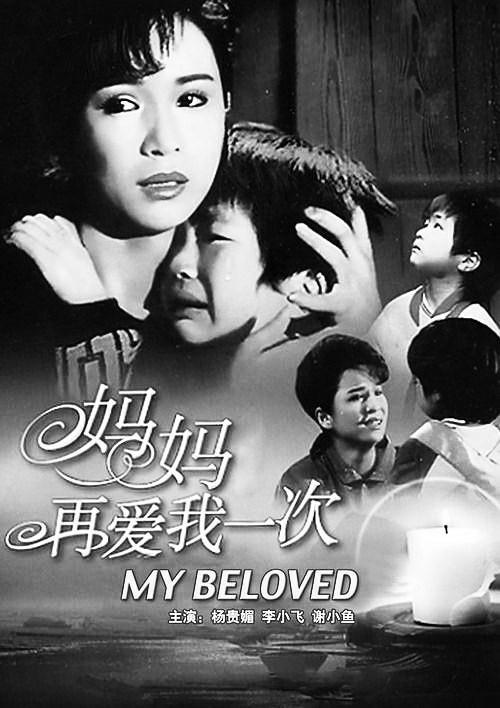
《媽媽再愛我一次》(1988)
一部影響了一代人的母愛題材電影。多少孩子在電影院哭腫了眼睛。影片主題曲《世上只有媽媽好》傳播更廣,二者結合,成就了歌頌母愛的經典。30多年過去觀眾的審美水平提高,再看此片,難免覺得劇情俗套。然而所有的俗套都源自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