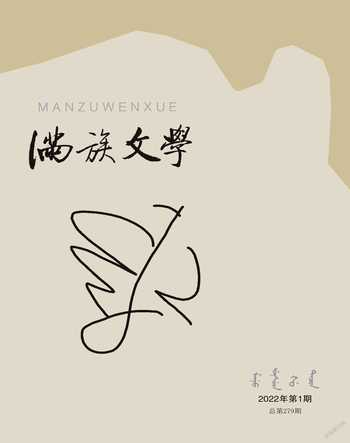主持人語:于曉威
張濤曾任《滿族文學》雜志的老主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與遼寧省內的鄧剛、馬秋芬、謝友鄞等人一起,蜚聲文壇。在本期里,我們特約張濤奉獻出他的一組短篇小說新作《他們》。這是一篇無論在結構、主題、人物、情節、氣氛還是語言等方面,讓人讀起來感覺久違和溫暖的佳作。說是久違,是它通篇彌漫著穿越了歲月之感的強大的現實主義底色和亮色,雖為短制,但因了小說的敘述語言追求儉省,極盡白描,具有獨出機杼的匠心與感染力,這樣嚴肅和認真的寫作風格于今似乎已不多見;說是溫暖,是作品里攜帶的歲月氣氛、環境烘托是那么的令人踏實,絲毫不覺違和,而里面描摹出的人物,又是那么力透紙背,栩栩如生。尤其是,作品里所寫到的,都是普通人,但是由著“他們”所代表的個體化的群雕,以及共同昭示出的古道之心,人性之魂,令人慰藉不已。
比張濤年齡稍小一些,洪兆惠也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和著名評論家。在他的短篇小說新作《雨棍》中,我們看到了作家在基于現實主義敘述的文本中,做出的具有現代性策略的可貴探索。作品中的人物與故事,似乎具有著“走廊鏡像”般的纏繞,亦真亦幻。“雨棍”是一個隱喻,它無形但有力,不可擺脫,與其說作品是探究兩個人的情感謎團,不如說是探究兩個人各自的情感謎團,或者說,是關于更多人物心靈“此岸”與“彼岸”的情感謎團。
黃海兮的中篇小說《龍泉寺》,將少年們的某一特定生活狀態縮微于單線條的故事之間,初讀之下,并無出奇之處,但就是在作者的看似無力、隨意和鎮靜的娓娓敘述之中,我們讀到了一種潛伏著深刻力量的現實或讖語。它是龍泉寺的,也是更廣闊的蕓蕓眾生的。它刻下了一個時代的無聲印記。
在本期里,我們還欣喜地讀到了青年作家趙卡和鬼金的現代派小說佳作。在趙卡的《叉牙鯛戒毒所》里,作者以一種類似“元小說”的敘述方式,饒有興味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集哲學、讀書、名著、人物、科技、歷史與現實于一體的小說文本,在看似荒誕不經的敘述策略之下,作者以強烈的互文手法,導引出歷史與現實的某些晦暗不明的生存狀態。鬼金的《白馬》也是一篇充滿著智性敘述的作品,是關于生命與思考的寓言之作。在古代哲學中,“白馬非馬”絕不是僅僅作為一種詭辯術而提出,它更代表著一種詰問事物的更真實狀態的哲學處境與能力。
總而言之,在本期小說里,我們既讀到了功力深厚的寶刀不老的現實主義佳作,也讀到了其形如流、其聲如磬的現代派作品,這也正是本欄目發表小說一貫的宗旨:不拘流派,不囿風格,海納百川,唯求優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