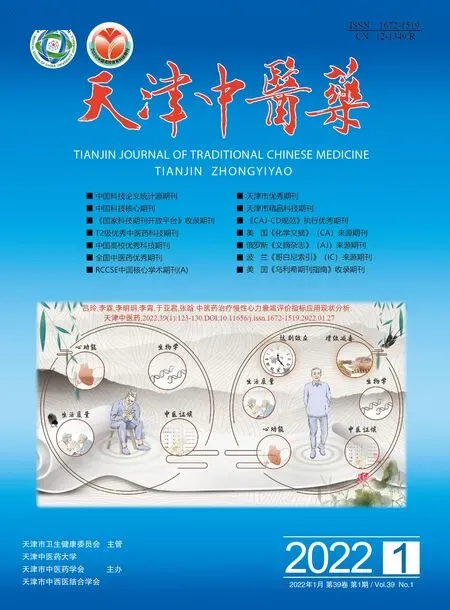活性多糖通過腸道對膽汁酸的調節作用*
邸晶蕊,尚非,楊麗,楊妙婕,趙鑫,張鵬
(天津中醫藥大學中醫藥研究院,組分中藥國家重點實驗室,天津 301617)
多糖類物質在自然界中分布廣泛,是人類膳食(如水果、蔬菜及谷物等)的重要組成成分,具有豐富的生物活性,如降血糖、抑制肥胖、保肝、增強免疫、抗炎、抗氧化、抗腫瘤、抗菌等,應用前景廣泛[1]。膽汁酸是膽汁的重要成分,可在腸道促進食物中脂類及脂溶性維生素的消化吸收,也是人體重要的代謝調控信號因子,廣泛參與糖脂及能量的代謝[2]。膽汁酸經腸道進行重吸收、代謝與排泄,多糖發揮生物活性也與腸道密切相關,研究表明多糖在腸道中可以通過激活多種核受體調控膽汁酸合成酶、代謝酶及轉運蛋白的表達,調控腸道菌群結構變化影響各級膽汁酸的代謝,直接結合膽汁酸抑制其重吸收、增加其排泄等多個途徑對膽汁酸進行調節,發揮降血糖、降血脂、保肝等生物活性。文章主要詳述了多糖通過腸道作用調節膽汁酸合成、重吸收、代謝與排泄的研究進展,以期為多糖調節膽汁酸的作用機制研究提供文獻依據。
1 多糖主要通過腸道發揮生物活性
多糖是一類由醛糖或酮糖在糖苷鍵的連接作用下形成的多聚物,由10個以上的單糖組成,成鏈狀和分支狀,其單糖組成和結構復雜多樣[3-4]。,而主要在腸道內發揮生物活性:1)多糖可以促進有益菌增殖,抑制致病菌的生長,并且影響腸道菌群對藥物及食物的代謝,發揮多種生物活性[5]。2)多糖可以通過物理或者化學結合作用抑制腸道中脂肪、膽固醇、膽汁酸的吸收,增加脂肪、膽固醇、膽汁酸排出,進而調節血脂含量,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發生風險。3)多糖可以增強腸道屏障功能,發揮調節機體免疫、抗炎等生物活性。4)多糖可以通過影響腸道消化酶的活性,調節食物的消化吸收,治療便秘等疾病。
1.1 多糖對腸道菌群的調節作用 腸道菌群可編碼多種碳水化合物活性酶催化多糖類成分的降解[6],將多糖類物質代謝為短鏈脂肪酸,如乙酸、丙酸、丁酸等,為腸道菌群提供必要的能量[7]。多糖作為腸道菌群的重要能量來源,對于腸道菌群的組成及功能具有調節作用。Zhang等[8]研究了牛蒡子多糖對腹腔注射脂多糖誘導全身炎癥模型小鼠的作用,發現其可明顯增加乳桿菌屬、Alistipes、Odoribacter和考拉桿菌屬豐度,減少擬桿菌屬豐度,顯著增加腸道內的短鏈脂肪酸的含量,減輕炎癥。Yang等[9]研究了亞麻仁多糖對高脂飲食致代謝綜合征小鼠的作用,發現其可增加阿克曼氏菌和雙歧桿菌的比例,減少Oscillospira和Odoribacteraceae的豐度,減少脂肪積累,減緩代謝綜合征的發生發展[10]。
1.2 多糖對脂肪、膽固醇、膽汁酸的結合作用 Fu等[10]在體外腸道模擬實驗中,發現枇杷葉多糖的脂肪和膽固醇結合率明顯高于羧甲基纖維素組,膽汁酸結合率明顯高于膽甾胺組。Qin等[11]在體外腸道模擬實驗中,發現秋葵多糖對脂肪、膽固醇結合能力顯著高于纖維素組,對膽汁酸結合能力高于膽甾胺組,明顯增加脂肪、膽固醇、膽汁酸的排出。Li等[12]研究了灰樹花多糖對高脂血癥模型大鼠的作用,發現其可促進糞便中膽汁酸的排泄,降低血清總三酰甘油、總膽固醇和游離脂肪酸水平,減輕血脂異常,抑制肝臟脂肪堆積和脂肪變性。
1.3 多糖對腸道屏障功能的影響 細胞間的緊密連接可通過調節細胞旁轉運,維持腸道屏障結構和功能的完整性。細胞間緊密連接相關蛋白主要包括ZO 家族蛋白(ZOs)、咬合蛋白(occludin)和閉合蛋白(claudins)、免疫球蛋白超家族蛋白等[13]。Liang等[14]研究了鐵皮石斛多糖對結腸炎模型大鼠的作用,發現其可增強腸道ZO-1和ocludin表達,有效的保護腸道屏障功能,減輕實驗性結腸炎。Bai等[15]研究了龍眼肉多糖對環磷酰胺處理小鼠的腸黏膜作用,發現其可增加黏液蛋白2、ZO-1、claudin-1、claudin-4和黏附連接蛋白E-cadherin的表達,預防腸黏膜損傷。
1.4 多糖對腸道消化酶活性的調節 多糖可以通過調節腸道消化酶活性影響機體對食物的消化吸收,優化腸道環境,改善腸道疾病。程宇嬌等[16]研究了螺旋藻多糖對便秘小鼠的治療效果,發現其可使腸道木聚糖酶、蛋白酶活性恢復正常水平,緩解小鼠便秘病癥。龍承星等[17]研究了鐵皮石斛多糖對脾虛便秘小鼠腸道微生態的影響,發現其使腸道木聚糖酶和蛋白酶活性恢復正常,淀粉酶活性顯著增加,纖維素酶活性明顯減少,優化腸道環境,改善脾虛便秘癥狀。
2 多糖通過腸道對膽汁酸的作用
2.1 膽汁酸在腸道中的重吸收、代謝與排泄 膽汁酸是一種含有24個碳原子膽烷酸衍生物[18],是膽汁的主要成分,膽汁酸隨膽汁分泌進入腸道,促進腸道對膳食脂肪和脂溶性維生素的吸收,是機體代謝穩態的關鍵調節劑[19]。膽汁酸根據來源分為初級、次級和三級膽汁酸。初級膽汁酸在肝臟中由膽固醇合成,包括膽酸、鵝去氧膽酸等[20];初級膽汁酸隨膽汁排入腸道后,一部分經腸道上皮細胞重吸收,由門靜脈返回肝臟,另一部分通過腸道菌群代謝轉化為次級膽汁酸(包括石膽酸、脫氧膽酸等)[21];三級膽汁酸一部分為次級膽汁酸的腸道菌群代謝產物,另一部分為次級膽汁酸重吸收后在肝臟中的代謝產物,包括磺基石膽酸和熊去氧膽酸[18]。未被腸道重吸收的膽汁酸經糞便排出體外[18]。腸道是膽汁酸發揮生理功能、重吸收、代謝與排泄的重要場所。
2.1.1 膽汁酸重吸收相關轉運體 大部分膽汁酸在回腸末端被重吸收進入門靜脈返回肝臟,形成肝腸循環[22],其重吸收受膽汁酸轉運體的調節。在腸道中分布的膽汁酸轉運體主要有鈉依賴型膽汁酸轉運體(ASBT)、膽汁酸結合蛋白(IBABP);有些膽汁酸轉運體在肝臟和腸道均有分布,包括異源二聚體有機溶質轉運蛋白 α/β(OSTα/β)、有機陰離子轉運多肽(OATP)、多重耐藥相關蛋白 2(MRP2)等[23-24]。法尼酯衍生物X受體(FXR)通過調節膽汁酸轉運體表達,影響膽汁酸的轉運[25]。
2.1.2 腸道菌群對膽汁酸的代謝 腸道菌群對膽汁酸的代謝主要包括早期解離、脫羥基、脫氫、脫硫4種途徑。1)來源于宿主的初級膽汁酸由膽鹽水解酶(BSH)進行早期解離,BSH主要存在于乳酸菌、梭狀芽胞桿菌、雙歧桿菌、腸球菌、李斯特菌屬、梭菌屬中[26]。2)梭狀芽胞桿菌參與膽汁酸7α-去羥基化,使初級膽汁酸轉變為次級膽汁酸[25]。3)由腸道菌群表達的 3種羥基類固醇脫氫酶 3α-HSDH、7α-HSDH和12α-HSDH參與膽汁酸羥基氧化和特定的差向異構化[27],將脂溶性的有毒膽汁酸轉化為無毒的水溶性熊去氧膽酸[26]。3α-HSDH存在于產氣莢膜梭菌、消化鏈球菌、和遲緩埃格特菌以及假單胞菌等中,7α-HSDH廣泛存在于擬桿菌、梭菌、大腸桿菌和瘤胃球菌中,12α-HSDH主要在梭狀芽胞桿菌屬中發現[28]。4)一些腸道菌群如梭狀芽孢桿菌S2產生硫酸鹽酶,能夠增加對膽汁酸的脫硫,促進膽汁酸的重吸收[27]。
2.2 多糖通過腸道對膽汁酸的調節作用 多糖通過腸道對膽汁酸的調節主要通過3個途徑:1)多糖可以調控腸道轉運體的表達影響膽汁酸的重吸收與排泄。2)多糖可以調控腸道菌群組成與結構,影響膽汁酸的合成、重吸收、代謝與排泄。3)多糖可以直接結合膽汁酸,抑制膽汁酸重吸收,增加膽汁酸的排泄。
2.2.1 多糖通過腸道轉運體調節膽汁酸 多糖可以通過調控膽汁酸腸道轉運體的表達影響膽汁酸的重吸收與排泄。Fang等[29]研究了果膠對仔豬膽汁酸轉運的影響,發現其可增加膽汁酸轉運總量及糞便中膽汁酸的排泄,降低血清膽固醇水平,對其作用機制的研究表明,果膠增加了回腸中FXR及膽汁酸轉運體 ASBT、MRP2 與盲腸中 FXR、OSTα/β、MRP3的表達。Zhu等[30]研究了山楂果膠對高膽固醇血癥模型小鼠回腸膽汁酸重吸收的影響,發現其可顯著降低小鼠腸道FXR受體的表達,使FXRFGF15軸失活,增加ASBT的表達,抑制膽汁酸重吸收,增加糞便中膽汁酸的排泄量,降低膽固醇積累,改善膽固醇代謝。陸紅佳等[31]研究了納米甘薯渣纖維素對糖尿病模型大鼠的作用,發現其可顯著下調回腸中ASBT、IBABP表達,增加大鼠糞便中總膽汁酸含量,發揮降血糖、降血脂作用。
2.2.2 多糖通過腸道菌群調節膽汁酸 Guo等[32]研究了灰樹花多糖對糖尿病模型小鼠的作用,發現其可能通過調節腸道菌群影響膽汁酸合成酶CYP7A1和膽鹽輸出泵(BSEP)表達,調控膽汁酸合成與重吸收,發揮降血糖、降血脂作用;其分析表明小鼠腸道中 Roseburia、Lachnoclostridium、Lachnospiraceae_NK4AB6_group、Rikenella、擬桿菌和 Alistipes 與CYP7A1、BSEP表達呈正相關,而鏈球菌、葡萄球菌、腸球菌和Aerococcus與BSEP表達呈負相關。張振龍等[33]研究了果膠和木聚糖對黃顙魚體內膽汁酸水平與腸道菌群的影響,發現果膠和木聚糖可能通過調控腸道菌群抑制膽汁酸的重吸收,降低血清總膽汁酸、膽固醇水平;果膠上調變形菌門豐度、下調梭桿菌門和鯨桿菌屬豐度;木聚糖上調梭桿菌門和鯨桿菌屬比例,下調變形菌門和柄桿菌屬豐度。
Huang等[34]研究了龍須菜多糖對脂質代謝異常小鼠的作用,發現龍須菜多糖通過調控腸道菌群的相對豐度影響膽汁酸代謝,減輕血脂異常;其中鵝去氧膽酸、脫氧膽酸與Alistipes、Prevotellaceae UCG-001、Corprococcus1相對豐度呈負相關,熊去氧膽酸、牛磺熊去氧膽酸與Lachnospiraceae NK4A136 group、Roseburia相對豐度呈正相關。Wang等[35]研究了小球藻多糖對高脂血癥模型大鼠的作用,發現小球藻多糖能通過調控腸道菌群促進盲腸總膽汁酸代謝,起到降血脂作用;研究顯示大鼠盲腸總膽汁酸與Ruminococcus_1、Coprococcus_1、Peptococcus 和 Acetatifactor呈正相關。Catry等[36]研究了菊粉對血管功能障礙的小鼠的影響,發現小鼠血液和盲腸中膽酸和鵝脫氧膽酸(初級膽汁酸)含量增加,石膽酸、脫氧膽酸(次級膽汁酸)含量降低,內皮功能障礙明顯改善;石膽酸、脫氧膽酸與瘤胃球菌科和Lachnospiraceae的豐度呈正相關。
Nakahara等[37]研究了杏鮑菇多糖對肥胖小鼠的作用,發現其可增加小鼠腸道中Parabacteroides、Anaerostipes和Clostridium豐度,促進糞便中脂質和總膽汁酸的排泄,抑制肥胖。Kristina等[38]研究了菊粉對動脈粥樣硬化小鼠的作用,發現其可使小鼠腸道菌群多樣性增加,腸桿菌科、Akkermansia和Bacteroides Fragilis的豐度減少,增加糞便中膽汁酸的排泄,調節膽固醇代謝。Lyu等[39]研究了靈芝多糖肽對高脂血癥模型大鼠的作用,發現其可能通過調節腸道菌群促進大鼠糞便中總膽汁酸的排泄,改善脂質代謝紊亂;靈芝多糖肽上調Alloprevotella、Parabacteroides、Bacteroides、Barnesiella、Alistipes 和Bacteroidales S24-7 豐度,下調 Blautia、Enterorhabdus、Roseburia相對豐度。尚紅梅等[40]研究發現小刺猴頭菌發酵浸膏多糖顯著提高肉雞回腸和盲腸中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的數量,促使腸道中膽汁酸和膽固醇轉化為膽酸和糞固醇,增加肉雞糞便中膽汁酸、膽固醇的排泄,改善肉雞脂肪沉積。
2.2.3 多糖通過腸道直接結合膽汁酸 多糖可以在腸道直接結合膽汁酸,抑制膽汁酸重吸收,增加膽汁酸的排出。Long等[41]評估了長莖葡萄蕨藻多糖(WCLP-70)對膽汁酸的結合能力,發現WCLP-70對膽酸、脫氧膽酸、甘膽酸和牛磺膽酸的結合能力分別為膽甾胺(100%)相應值的68.1%、36.1%、74.9%和72.3%。Gao等[42]研究發現酸輔助提取法得到的海帶粗多糖(LP-A8)對膽酸、甘膽酸和牛磺膽酸的結合能力較強,分別為膽甾胺(100%)相應值的68.29%、81.99%和161.72%。Yan等[43]研究發現紅外輻射干燥得到的苦瓜多糖,能有效結合膽酸和鵝脫氧膽酸。Deng等[44]研究了玉米須多糖對膽汁酸的結合能力,發現玉米須多糖能有效結合牛磺膽酸鈉和甘氨脫氧膽酸鈉。胡婕倫等[45]評估車前子多糖對膽汁酸的結合能力,以辛伐他汀作為陽性對照,發現車前子多糖相比于辛伐他汀能結合更多的膽汁酸。
文章將近年來研究中通過腸道調節膽汁酸的多糖種類、單糖組成、調控過程與調控方式進行了總結,見表1。

表1 活性多糖通過腸道對膽汁酸的調節Tab.1 Active polysaccharides regulating bile acids through intestinal tract
3 展望
文章對多糖通過腸道調節膽汁酸合成、重吸收、代謝與排泄研究進行綜述,可為后續治療高脂血癥、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等膽汁酸異常導致疾病的多糖類藥物開發與作用機制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制定新的靶向治療策略。由于單糖組成、糖苷鍵、聚合度等的差異使得多糖結構復雜,菌群結構受外因或內因的影響極易發生變化,碳水化合物活性酶降解多糖后得到物質種類的多樣化,腸道-膽汁酸-宿主軸的動態變化錯綜復雜,人們對于多糖的降解機制、細菌代謝終產物、對菌群結構的調控及代謝產物對機體的影響等方面的認識尚淺,多糖對膽汁酸調控的作用機制亟待大量研究工作深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