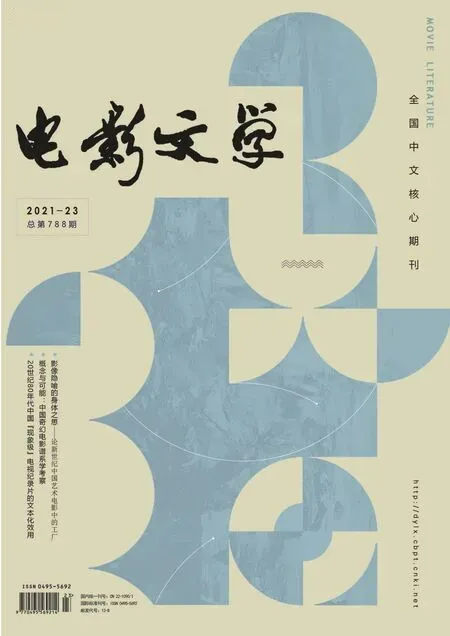從記憶重現到凝聚結構:“百年黨史”題材紀錄片建構黨史記憶研究
徐丹丹 楊鄭一
(1.揚州大學黨委宣傳部,江蘇 揚州 225000;2.揚州廣播電視傳媒集團,江蘇 揚州 225000)
記憶的概念在人類歷史上由來已久,一般指人們對所經歷事情的認識和回憶。法國學者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將涂爾干的社會分析理論引入記憶研究后,創造性地提出了“集體記憶”的概念,將其視為每一個“具有一定時空邊界的群體”所擁有的記憶。在與一定的社會情境連接后,集體記憶就超越日常性的社會交往范疇,可以長時段地參與到媒介敘事和文化實踐中,成為揚·阿斯曼所說的文化記憶。掌握和運用文化記憶傳遞機制對國家或政黨而言意義非凡,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和政黨都面臨無形的以說服和信仰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建設、傳播和認同。事實上,任何歷史話語和歷史敘事只有修辭性地融入當代族群的文化記憶之后,才能成為滋養理想信念和價值觀念的深厚土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各級媒體單位集中推出了一批百年黨史題材的紀錄片作品,如《重生》《百煉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共產黨人》《復興之路》《山河歲月》等,它們通過各種介質媒體的傳播展示,形成了極其豐富的紅色文化景觀,呼應并續寫了百年黨史記憶,成為傳承黨史文化的重要途徑。在黨和國家大力傳播宣揚黨史文化的當下,我們有必要落腳于符號表征和媒介敘事的視角,深入探尋通過紀錄影像實現百年黨史記憶修辭與轉義的作用路徑,并借此管窺強化當代政治文化傳播的方法與經驗等問題。
一、百年黨史記憶重現的視覺修辭模式
百年黨史記憶是中華民族文化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貫穿現代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歷程中,成為中華民族“家-國”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載體。當前中國正處在劇烈的社會變革期,文化記憶被賦予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多重功能,已經成為闡釋“當下”意義的重要路徑。形成文化記憶的核心是符號,是表征。由于時間與空間的無限性,人類越來越難以依靠具身經驗將復雜的歷史現實轉化為敘事性的歷史書寫,而是需要借助社會交往和媒介傳播來獲取記憶傳承,并在社會文化框架馴導下形成對文化記憶的話語表達,這個過程被稱為記憶重現。作為一種文化記憶機制,百年黨史的記憶重現是借助符碼表征和傳播活動,將百年黨史所承載的文化、情感和精神信念進行“物化”和“言說”的過程,相較于傳統的語言或文字,視覺表達能夠通過將圖像、文字、音樂等多模態語言融為一體的方式,影響和推動文化記憶的建構實踐,因而成為視覺文化時代傳承黨史記憶的重要途徑。
正因為文化記憶鮮明的“當下性”特征,百年黨史記憶的影像書寫必然蘊含著一個通過修辭手段組織符號話語實現“勸服”功能的過程,體現為通過視覺圖像在記憶文本、受眾文本和社會文化文本間建立修辭結構,傳達特定文化意義和意識觀念,從而實現記憶重建的實踐過程,其作用機制如圖1所示:

圖1 百年黨史記憶重現的視覺修辭模式
百年黨史記憶重現的視覺修辭模式包含三層內涵:第一是對記憶文本的符號生產,這是一個記憶符號存儲和加工的過程,通過紀錄影像的視覺加工將黨史記憶形象化、具體化,建構起可以被感知和言說的形式,形成人們對百年黨史記憶的基礎性認知。第二是受眾文本的二次加工,即受眾在進行“觀看”百年黨史題材紀錄片行為的過程中,將接收到的記憶符碼與自身經驗世界進行融合和重寫,借助文化記憶選擇、強化、遺忘等機制的作用,將個體記憶“集體化”“社會化”“文化化”的實踐活動。第三是社會文化情境中的記憶再生產,由于記憶書寫存在集體性、建構性、不確定性的特點,相同的記憶元素在不同個體或族群中會呈現千差萬別的理解,因此必須借助社會文化文本提供一種先驗性的認知,建構記憶體驗的“形式”和“框架”,為記憶書寫提供超越維度的他者書寫。上述三種內涵分別從視覺符碼、受眾感知與文化實踐的維度發生作用,通過其中修辭結構的建立,將百年黨史記憶以視覺影像的形式進行生產和傳播,并對現實的社會文化產生影響。
二、紀錄影像中百年黨史記憶的意象建構與修辭實現
作為一種文化實踐,黨史記憶不是靜態的、孤立的存在物,而是在社會交流中不斷更新的對話性語言。基于語義不確定的客觀存在,記憶交流活動中決定記憶內涵的就不僅是“我們說了什么”,還取決于“人們記住了什么”,其中必然包含了認知維度的修辭實踐。以百年黨史題材紀錄片為載體推動黨史記憶的記憶重現,可以理解為運用意象選擇和符號修辭的方法讓黨史記憶在當下“鮮活”起來的文化實踐,其意象建構與視覺修辭邏輯可以從文本分析、話語實踐與社會實踐三個層面展開分析。
(一)記憶重建:以視覺意象組織記憶文本
從本質上講,記憶重現是對記憶文本的符號化處理,是約定視覺符號形象和意義的意識生產活動,基礎性的產品是視覺意象。既有的研究認為:視覺意象包含原型意象、概念意象、符碼意象三種樣態,分別回應了視覺修辭實踐中語境生成、議題建構、符碼表征三個層次。利用百年黨史題材紀錄片開展黨史記憶的建構實踐,就需要分別在視覺意象的三個層次中修辭操演,實現對人們視知覺經驗的組織化和文本化,最終達到形成對話和勸服的效果。
第一,紀錄片利用原型意象建構了底層記憶語言。原型是一種穩定、典型可以被反復使用的形象,是經由歷史、文化、社會心理等反復構造所沉淀形成的普遍共享認識。人們在觀看活動中獲得的直接經驗是浮動的、零散的、未經雕琢的,并不能在修辭實踐中形成普遍意義上的記憶敘事,因此需要借助原型意象提供記憶重現的解讀語境,以此回答“圖像是什么”這個基本問題。百年黨史題材的紀錄片脫胎于黨的建設和發展的歷史進程,其中借用并顯現了大量表征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原型意象,如黨徽、黨旗、黨員身份標志、黨的政治儀式等,這些視覺意象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反復接觸并已經形成共享認知的符號形式,是普遍性社會文化經驗在人們認知系統中的投射。在觀看黨史紀錄片的過程中,原型意象能夠源源不斷地鋪設文本釋義的文化語境,激活人們在潛意識中存在的認知經驗和情感體驗,從而將社會文化系統中的“元語言系統”借用到影像釋義的活動中,為人們實現記憶重現提供定位基點。
第二,紀錄片利用概念意象形成隱喻關系。在意象形式確立之后,概念就成為修辭的關鍵。在黨史題材紀錄片的記憶書寫過程中,需要引導人們在形式認知與概念認知之間建立橋梁,激發從圖像形式到圖像概念的認知轉換行為,即開展“圖像像什么”的論證活動。在黨史記憶的圖像敘事中,同樣的形象在不同的時間和事件背景下可以表現不同意義,如南湖紅船既象征著黨的創立,也象征著紅船精神,還可以指向堅持黨的領導的意義內涵,甚至對畫面本身的不同視覺處理也可以展現出特定的意義內涵,因此有必要借助符號修辭活動提供一種外部規定性,給人們提供一種把握現實的方法指導。在黨史紀錄片社會傳播過程中,伴隨著意象敘事的是一系列概念隱喻的出場,它們之間的相互勾連在圖像表征與概念意指間建立了映射結構,展開了積極的議題設置活動,激發了受眾在潛意識中不自覺地調動概念意象解釋現實問題,從而使視覺畫面超脫了視覺獲取物的范疇而成為共享意義的攜帶者。
第三,紀錄片利用符碼意象形成意義系統。作為觀看行為的深層次活動,圖像形式與意義的接合能夠產生抽象意識,引導人們建立關于黨史記憶的知識體系,產生對圖像內涵的認識論指導。在這個階段,人們在觀看黨史題材紀錄片中獲得的形式與象征認知經過意識想象的加工被不斷雕琢、整理并系統化,形成一種相對固定的思維方式,如用開國大典、東方紅的配樂以及黨的第一代領袖的形象表征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黨的歷史,用鄧小平等領導人畫面、《春天的故事》等配樂表征改革開放初期的黨的歷史等,在圖像能指與所指間建立牢固的指涉結構,從而牢牢掌握了記憶文本的意義生產權,讓人們進行觀看行為時能夠被引導到共同的意義系統中,實現對黨史記憶的表征確立。
(二)記憶操演:以視覺框架規范受眾文本
在視覺修辭活動中,框架總是伴隨話語實踐“出場”的,重在解決合法性的問題。框架理論的創始人歐文·戈夫曼認為:框架意味著一種“闡釋圖示”,它能夠幫助人們“辨別、感知、確認和命名無窮多的事實”。在百年黨史主題紀錄片的影像敘事中,視覺框架實際上鋪設了一套邏輯推演系統,以先驗存在的形式定義了人們對紀錄影像的理解方式。第一,框架提供了解釋和重復。框架是一套組織信息的方式,其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穩固性并能夠規范人們對事物的理解。在人們觀看紀錄片的過程中,百年黨史的記憶敘事框架被重復征用,為各種形式的影像話語鋪設意義說明,以此將黨的政治意志和機制觀念灌注到人們深層次的邏輯認知中,實現說服和認同的目的。
第二,框架激活了知識體系。美國學者喬治·萊考夫和馬克·約翰遜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中指出:人類的概念系統是以隱喻的形式存在的,同樣是以隱喻的形式構成和發生作用的。在黨史紀錄片的話語敘事中,框架積極地在歷史記憶與現實概念間以隱喻的方式建立意義置換結構,形成把握理解影像內涵的知識框架,并通過對知識框架的權力操演為黨史記憶提供社會認知層面的合法性說明。例如,黨史中的革命精神資源能夠被隱喻映射進入現實的奮斗實踐,鮮活闡釋鐵人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黃大年精神等在人們現實生活中的展演,從而將來自黨史記憶中的概念體系轉譯進入“當下”的文化語境中。
第三,框架提供了間接編碼的流通。人們對黨史紀錄片的觀看行為存在多種可能,有人看過很多甚至大多數的作品,有人僅僅看過一部分或者一些片段,還有人可能看過極少數作品或者完全沒有看過,但是不論哪種情況,人們的認知世界中都存在對百年黨史的記憶認知,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就是社會記憶框架的存在。黨史紀錄片的傳播過程,實際上也是黨史記憶框架的社會傳播實踐,人們可以借助社會交往以“間接編碼”的形式開展框架敘事,形成超脫直接觀看經驗之外的認知體驗,形成與黨史記憶更加緊密的情感和文化聯系。
(三)記憶規訓:以文化關系勾連社會文化文本
既有研究已經指出:記憶建構是一個動態的社會過程,由不同的參與者、社群、媒介和文本共同塑造。從這個角度理解,黨史記憶的影像傳播不僅起到了傳遞信息的作用,同時也通過社會關系的統合勾連了記憶文本和受眾文本,實現對社會深層次文化心理結構的生產和調試,這是百年黨史記憶的再生產實踐。第一,社會文化文本形成了多模態語言的空間組合體。在黨史題材紀錄片的傳播過程中,建構人們觀看經驗的既包含紀錄影像的畫面、聲音、字幕等視聽文本,也包含彈幕、評論等伴隨文本,還包含進行觀看的場所環境、社會語境、文化風俗等環境空間,它們共同建構了黨史記憶生產的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在百年黨史記憶的社會文本書寫中,內部記憶世界與外部記憶世界不是孤立地發生作用的,而是以一種“復調式”的記憶書寫形成多元化的記憶流通通道,從而再造“觀看關系”,形成“記憶空間”,打通記憶傳播的“視覺之維”。
第二,社會文化文本重構了社會認同關系。黨史紀錄影像的傳播過程,既包含創作者與受眾的傳播和交流關系,也包含不同受眾間的共享和對話關系,他們之間的意識交流活動共同塑造了作為“他者”文本的社會文化文本。作為一種集體意識形態的構造物,社會文化文本能夠通過認知關系對受眾文本進行解釋和規范,在社會族群中發揮對話與規范的功能。實際上,百年黨史主題紀錄片的社會傳播建構了一種“命名關系”與“排除關系”。一方面,通過視覺框架對黨史記憶事件進行命名,確認其現實合法性與必要性;另一方面,黨史記憶的傳播還建構了一種“排除關系”,即通過對記憶符碼的“選擇性遺忘”形成“去認同”的傳播活動。通過對歷史敘事進行選擇性傳播和選擇性排除,讓黨史記憶更好地履行文化生產和傳播功能。
第三,社會文化文本促進了文化生產實踐。媒介話語是被建構的產物,同時,它也可以反向建構文化、政治與社會生活。黨史紀錄片的傳播與認知活動中,人們在社會文化中鋪設了關于黨史記憶的“話語場”和“意義場”,人們在面對新的文化問題時,一方面,可以通過“編碼—解碼”的實踐主動迎合主流黨史記憶形態,使得社會族群成員成為百年黨史文化的積極認同者和堅定踐行者;另一方面,黨史記憶的媒介敘事在社會層面形成了記憶資源的積累,促進了黨史記憶在不同存儲媒介間的轉化,例如從視聽語言到文字語言,文獻記錄到影像記錄,從視覺畫面到紀念器物等,這些轉化積極推動了社會記憶的再生產實踐,讓黨史記憶更加鮮活,更加生機勃勃。
三、紀錄影像中百年黨史記憶重現的視覺話語實踐
作為一種話語實踐,百年黨史題材紀錄片通過記憶重現的實踐,在當代社會文化生產中發揮了批判性的作用,或者說黨史記憶與當代中國現實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在黨史題材紀錄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現,以此形成在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活維度的反向建構力。在當下文化情境中,我們有必要深入體察紀錄影像在百年黨史記憶傳承中的話語、凝結與空間功能,以此錨定我們深化百年黨史記憶生產與修辭的方法路徑。
(一)以影像話語提升黨史記憶的可見性
記憶可見性意味著記憶被看見,被發現,意味著讓記憶敘事走出私人領域,走向公共生活。德國學者阿萊達·阿斯曼就指出:存在兩種用于存儲回憶的記憶存儲器——身體和語言。在記憶重現的過程中,身體之維指向了作為認知思維的記憶生產活動,體現了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間的互文關系,語言之維指向了社會溝通中形成的記憶框架和關系結構,二者共同決定了記憶重現的公共性特征。在記憶重現中提升百年黨史記憶的可見性,需要充分把握實現修辭的隱喻、互文、轉喻等修辭方法,實現對文化記憶的創造性生產。首先,以比喻關系展示時代精神。百年黨史記憶反映了當下中國的社會現實,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它的指向意義是在黨的領導下,社會成員通過努力奮斗實現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與必然性,通過記憶重現能夠在社會心理層面形成積極的心理建構,將人們幸福生活的獲取與黨的奮斗歷程“接合”起來,形成廣泛的心理認同和情感認同。其次,雖然黨史題材紀錄片展現的是宏大的歷史敘事,但其影像書寫往往要落腳于現實個體的生命書寫上。通過在宏大歷史與個體實踐間的互文書寫,黨史紀錄片將黨史記憶刻寫在社會族群的經驗世界中,將集體記憶、個體風格與私人記錄在記憶書寫中連接起來,讓記憶建構中的“整體”和“個體”,“官方”和“民間”都處在“可見”的狀態下,使得黨史記憶能夠在更廣泛的層面上發揮作用機制。
(二)以影像傳播開展黨史記憶的框架宣認
人是依賴框架存在的動物,在視覺文化時代,人們往往依靠視覺經驗來“框架世界”。在視覺敘事中,圖像可以證明真實,也可以書寫謊言,其體現在共時性的記憶書寫中時,就形成了對框架“命名權”與“釋義權”的爭奪。從這個角度來說,百年黨史的記憶重現中也蘊含著對記憶框架“爭議”和“宣認”的斗爭實踐。首先,紀錄片以視覺刺點激發情感反應,視覺修辭研究的先驅者羅蘭·巴特將“刺點”的概念引入視覺研究中,用來指代圖像中能夠吸引人們關注,引發人們情感的刺激物。利用黨史紀錄片進行記憶操演,就需要把握和運用視覺刺點,將人們的思維活動從簡單的畫面識別引向深層次的情感體驗,如畫面中的紅旗、黨徽,主體人物佩戴的黨徽等,這些視覺刺點的出場能夠迅速將記憶操演引導到百年黨史的記憶敘事框架中,從而實現對黨史文化意義的召喚。其次,以意識體驗開展社會動員。在黨史記憶的重現中,紀錄片能夠通過對觀看“場所”“語境”等的選擇實現對語義場的鋪設,也能夠通過程式化的重復操演將黨史記憶與人們的身體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在此過程中,“媒介扮演著象征黏合劑角色,使獨立的社會個體結合成為緊密的社會整體……媒介能夠在文化層面構建無形的社會組織象征模式”,可以說,黨史記憶的媒介傳播建構了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記憶敘事框架,在某種意義上實現了黨史記憶的神話操演,使其發揮出米歇爾·福柯所言的裝置作用,從而將記憶操演拉向生命政治之維,成為知識權利框架的表征。
(三)以空間傳播建立黨史記憶的凝聚結構
在百年黨史題材紀錄片的傳播過程中,人們所經歷的記憶世界,實際上是傳達了經由權利操演所定義的記憶路徑,形成了關于黨史文化的記憶空間。在黨史記憶空間中,我們運用符號回憶過去,定義現在,并面向未來形成意識想象的共同體,這就是百年黨史記憶的“凝聚性結構”。揚·阿斯曼認為“凝聚性結構”是維系記憶空間的基礎,他認為:“每種文化都會形成一種‘凝聚性結構’。凝聚性結構可以把人和他身邊的人連接到一起,其方式便是讓他們構造一個‘象征意義體系’——一個共同的經驗、期待和行為空間……”在黨史紀錄片的傳播過程中,紀錄片借助標簽符號的細描和共享式符號架構的闡釋體系,成為表述特定形象的載體,將抽象的記憶符碼轉化為現實的回憶行為。在體驗維度上,紀錄片通過對社會關系的編織,將人們的生活空間、紀念空間與黨史記憶連接起來,使得黨史記憶不僅表現為一種回憶行為,也體現為一種生活方式;在文化空間維度上,讓百年黨史記憶在社會生產和生活關系中“活化”起來,通過記憶傳承和記憶形態間的互文轉化,積極地介入社會文化再生產的實踐中,讓百年黨史記憶成為當代文化空間中的文化資本與思想寶藏。
概況來說,紀錄片作為“寫在膠片上的歷史”,是傳播和闡釋黨史記憶的重要載體。通過對百年黨史紀錄片視覺修辭模式與路徑的分析,我們能夠在影像世界、現實世界、記憶世界間建立貫通關系,發現并總結“記憶何以可能”的路徑與方式。在世界語圖時代的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在視覺生產與記憶生產間建立闡釋結構,回應視覺化時代開展記憶修辭的需要,從而為當代社會文化生產提供更多的精神資源和價值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