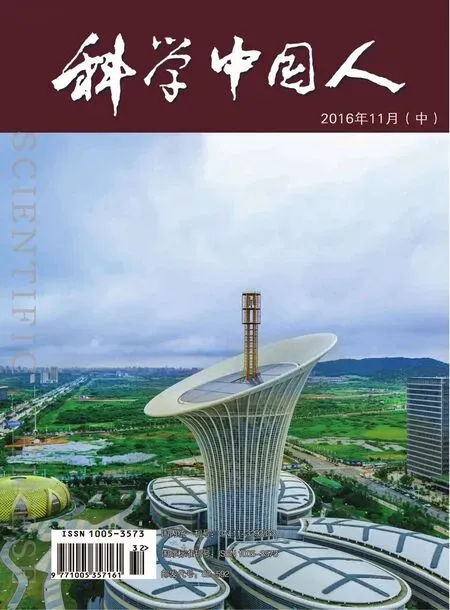冼世榮:一生只為“中國芯”
戶 萬
生于澳門,長于澳門,在數字時代與電子時代的斷裂處苦苦求索,讓他找到了芯片時代的模擬數字轉換器(ADC)。不斷追求卓越,自我導向和富有成效,是他的座右銘。
從沒有先輩、沒有設備、沒有經費,到現在建成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實驗室,再到成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十年磨一劍”,他成為澳門ADC芯片研發的先驅。
28年經驗,超過40款相關領域芯片,在分辨率、速度、功耗、面積等方面,近乎苛刻地追求更高、更快、更強,只為一顆“中國芯”。
他,叫冼世榮,澳門大學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微電子研究院副院長,電機及電子工程系副教授及副系主任。他同時也是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的副研究員。
“更高 更快 更強”——在“中國芯”書香中苦探索
模擬數字轉換器(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冼世榮將它稱作ADC,“它的功能是將模擬信號轉變為數字信號。也就是說,自然界,還有人類世界的信號,比如說我們看到的影像、看到的圖像、講話的聲音、手機通信和無線電波的信號等,都是模擬信號。這些信號,需要轉換,才能通過手機、電腦、平板等硬件與人類對話。那么,這個轉換器就是ADC”。

2011年獲國家科學與技術進步獎二等獎團隊合影(左一為冼世榮)
ADC是冼世榮在數字時代和電子時代的斷裂處找到的黃金礦藏。冼世榮讀大學的時代,是20世紀90年代。那時候,始于20世紀中期的信息革命,已經進入數字時代,“數碼港”“數碼世界”等是當時最流行的詞匯。但是,冼世榮選擇的是電機、電子工程。“數字的時代需要電子嗎?”這個問題,困擾了冼世榮很多年。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冼世榮的求學狀態。在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他不斷追問一個問題:數字時代,模擬電路的意義是什么?

2021年冼世榮在華人芯片設計技術研討會上發表演說
“信號轉換是不變的規則。人類需要更快的處理器,前提是要能快速地將模擬信號轉換,其關鍵前端結構仍然是更快的模數轉換器。所以,數字時代,信號轉換呼喚更高、更快、更強的模擬信號處理能力。這是繞不開的路,但這也是一個瓶頸,”找到關鍵因素的冼世榮高興得像個孩子,“因為這是一個關鍵部件,它不能自動迭代、升級,也不能自動匹配人類的需求。它需要工程師和科研人員的攻關、努力與經驗。沒有人能繞開它,進入數字區域。”再加上冼世榮本來就對模擬信號處理、晶體管、放大器等非常感興趣,選擇模擬信號處理就變得順理成章。冼世榮這樣形容當時的興奮:“就像探險者在荒漠看到綠洲,像勘探者在荒原上找到礦產。”冼世榮是在澳門出生,又在澳門長大的。從1997年畢業于澳門同善堂中學,到2008年獲得澳門大學電機及電子工程博士學位。十年磨一劍,冼世榮始終在這一領域深耕。他的博士學習和研究師承馬許愿教授,但當時的澳門還沒有專業軟硬配套設備。
“我求學的過程在老師身上得到很多啟發,”冼世榮說,“要勇于嘗試,不要怕失敗是最為深刻的感悟。”正是老師的鼓勵,讓他及后續團隊有了一直向前的動力,讓澳門大學乃至整個澳門,改變了沒有數據轉換器芯片研究活動和相關配套設施的歷史。一直以來,國內在數據轉換器相關領域的研究人才及工程師非常缺乏,數據轉換器芯片一直比較依賴國外進口,冼世榮算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博士期間論文研究的是“用于超高速時間交錯流水線ADC廣義低電壓電路設計”,后來成長為澳門首創研究模數轉換器芯片領域研究的科研學者。
如今,冼世榮和他的團隊已經在澳門大學建立了成熟的ADC研究平臺,包括設計方法論、仿真方法、分布式仿真引擎設置,以及自動評估ADC的頻譜和信噪比的ADC實時測量平臺。
十年磨一劍——在世界ADC領域嶄露頭角
因立志搞科研,同事給他起名“馬許愿”,他就是冼世榮的導師——Rui Martins。1992年,立志搞科研的馬許愿剛到澳門的時候,電子芯片領域還是一片荒原,既沒有科技成果,也沒有科研經費。櫛風沐雨,歷經艱辛,直到2004年,冼世榮開始在馬許愿帶領下攻讀博士研究生。
冼世榮也是在這個時期進入ADC領域的。在他看來,在不同種類的模擬芯片里面,ADC是比較具有挑戰性的課題。因為ADC包含了比較豐富的信號處理知識,還有數學、工程技術等問題,對驗證、設計、測量等也有很高的要求。一直以來,國內在數據轉換器ADC相關領域的研究人才都非常缺乏。那時候,數據轉換器芯片主要依賴進口。
2003年,澳門大學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實驗室創建。自此,澳門大學ADC走上了快速發展之路。2011年,冼世榮的一名博士生實現了高性能低功耗逐次逼近型ADC,這一論文在IEEE國際固態電路會議(ISSCC)上發表,獲得ISSCC絲綢之路獎。同時,這一研究成果在IEEE固態電路雜志(JSSC)上發表。
ISSCC是全世界微電子領域的奧林匹克,高峰會議每年都在美國舊金山舉行。如果能在ISSCC發表一篇論文,相當于在芯片的奧林匹克世界拿到一枚金牌。全世界學術機構、業界等每年在ISSCC共發表200多篇論文,每一篇論文都必須經過芯片的真實測量驗證才能被接受、發表。2011年的ISSCC,唯一一個拿到絲綢之路獎的就是冼世榮的這名博士研究生。
當年,全中國大陸一共發表兩篇ISSCC論文,香港有一篇,澳門有兩篇。也因此,2011年,澳門大學的芯片實驗室獲國家科技部授予“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至此,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落戶澳門大學。這是全國微電子芯片設計領域僅有的兩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之一,也是華南地區及粵港澳大灣區微電子領域唯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
2011年,對澳門大學ADC而言,實在是幸運的年份。這一年,他們還拿到了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這是澳門大學代表澳門,第一次拿到國家獎。
一步一步走來,澳門大學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已經成為澳門大學與國際、國內接軌的廣闊平臺。實驗室成立的國際學術委員會,囊括了全球微電子芯片領域頂尖的科學家。來自意大利帕維亞大學的Franco Maloberti教授,每年都會三訪澳門。每一次到澳門大學,他都會給同學們帶來全球最新的研究進展、最新的創新成果,也會與同學們互動,提出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的Boris Murmann教授,每年也會到澳門講學交流。他們很早就與清華大學合作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與澳門特區政府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聯合資助,為培養本土高端科技人才發力。
時間很快走到2019年,澳門大學微電子研究院團隊赴美國舊金山參與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舉辦的國際固態電路會議ISSCC。那一次,澳門大學有8篇論文被會議接納,成為論文發表數量最多的機構之一。他們與“聯發科技”及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同為全球第二名,僅次于全球第一的英特爾公司。而澳門大學在2018—2020年共發表了29篇固態電路雜志(JSSC),按機構排名位居全世界第九,全中國第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28年來,澳門大學在微電子ADC領域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輝煌。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在前行的路上,冼世榮和他的團隊成員一起更加堅定了努力的腳步。
大學與企業的產學研合作——把高效產能留給企業,把容錯創新留給大學
2009年6月,澳門大學在橫琴島上有了自己的新校區,這件事讓冼世榮開心了很久。作為芯片領域的科研人員,冼世榮看到了背靠橫琴山的大灣區校區的巨大意義,“珠三角地區,深圳是中國微電子芯片產業的重鎮,珠海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各種芯片產業和人才落戶,澳門擁有全國重點實驗室。就我們ADC領域而言,這里是天時地利人和,產學研轉化很好的舞臺”。

2019年冼世榮(中)參加ISSCC(美國國際固態電路會議,被譽為芯片“奧林匹克”)的合影
多年的科研經驗告訴他,大學科研成果轉化要有強有力的產業支撐,企業行穩致遠要有源源不斷的穩定人才,這樣,科學研究及其成果轉化才是順暢的,產學研才能形成良性循環。采訪中,冼世榮特意詳細闡釋了這個過程。他說:“大學是培養人才,生產和傳授知識、創新成果的平臺,科研的主力是老師和學生。大學的優勢在于,產生科研成果的過程中,允許犯錯。在我們看來,沒有不犯錯誤的學生。成長就是在一個又一個錯誤的累積和修正中進行的。錯誤是絕佳的學習機會,失敗是成功之母。因此,在學習和科研中,我們鼓勵學生自己思考,大膽創新,不怕失敗。一方面,這是學生學習和成長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大學沒有什么虧本的。但是,企業不同。他們需要參與市場競爭,時間是最大的成本。一旦失敗,不僅意味著投入歸零,關鍵是喪失窗口期,有可能被市場拋棄。因此,企業的容錯成本很高,或者說企業是不太能容錯的。正是在這一點上,大學為企業輸送成熟的科技人才,企業需要做的是提出問題,為科研提供生長的土壤,為人才提供成長的平臺。”
緊接著,冼世榮談到了關于“產學研合作”的第二個觀點。他認為,在產學研結合方面,大學也有軟肋。這個軟肋是由大學本身的特點決定的:“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他們在學校的時間是有限的。因此,從長遠來看,學校的科研人才的經驗一般是較短期的。但是,企業不一樣。企業的好多工程師,都是十年甚至幾十年在一個領域研究、實踐。他們擁有使研究快速產品化、產業化的能力。而且,企業緊盯的是市場,他們必須在市場的大風大浪中接受考驗。所以,市場的要求,使得企業一方面要求穩定的科研隊伍,另一方面是快速靈敏的市場反應能力。這一點上,大學和企業看似是矛盾的。但是,把眼光放到歷史的長河中,看未來5年、10年,甚至更久遠的時光,大學就有了用武之地。企業走在市場前沿,如果結合產品應用前景和客戶需求,有一個較為長遠的規劃,能確定長遠的創新性目標,就是與大學最好的合作點。因為大學的容錯空間比較高,大學的新生科研力量源源不斷,在創新驅動下,就可以勇敢一點去創新,失敗了也不會承受太大的損失。以這樣一條路徑來降低企業承受失敗的風險,相反,企業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研發短平快的項目,集中精力攻克短時間內可以迅速回收成本的項目,提高成功率。”
冼世榮的學生都拿到了行業很好的offer。這是他對產學研看法最好的證明。在這一點上,冼世榮希望的是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芯片產業中。冼世榮告訴記者,當年他在澳門大學讀書的時候,沒有人選擇ADC。28年過去了,ADC領域的拔尖人才還是很少,“現在,從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走出來的學生,都找到了非常好的工作。所以,最大的希望是ADC領域的人才越來越多”。
“一生摯愛ADC”——有多大壓力收獲多少快樂
在澳門,冼世榮是在ADC領域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發現研究ADC的理由很現實,數字的時代大家都去做數據了,可是當處理器需要更快的模擬數據的時候,卻出現了瓶頸。“為什么沒有人愿意去解決這個瓶頸?”冼世榮的回答很骨感,“太難!”然而,這個冷門的難題,是繞不過的坎!“既然繞不過,就讓我來做吧”,冼世榮認為自己找到了黃金富礦。
然而,難題就是難題。顯然,冼世榮一開始對困難的準備,還是稍顯不足。因為進入這個領域后,他才發現,“沒有前人經驗,沒有設備,前面沒有路”。不過,冼世榮還有一個撒手锏,他對模擬信號轉換很感興趣。他的解釋是,“前期,你遇到多大的困難,后面你解決困難之后,就會收獲多大的快樂。它們是成正比的”。
再之后,冼世榮把這個感悟講給學生聽。因此,他對學生的最基本要求是,“要有興趣”。“如果不感興趣,整個科研就會變得很無聊。一旦遇到難題,就很難承受其中的壓力,也沒有動力去探索和解決問題”。
在冼世榮的實驗室,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不管是師哥師姐,還是師弟師妹,進了實驗室就要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科研中。只要走進實驗室,他們就像換了一個人,個個精神抖擻。整個學習期間,他們要經歷完整的模擬電路芯片設計流程,包括從數學建模、電路設計及仿真、模擬版圖設計、芯片流片以至芯片實測。也因此,從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走出來的學生,很多都是早早地就拿到了企業、學術機構的工作合同,而且還是很有競爭力的待遇。多年以后,他們依舊沉浸在ADC,為澳門、大灣區、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相關企業及大學發光發熱。“要舍得投入時間和精力”,其實是冼世榮對同學們的第二個基本要求。

2019年冼世榮(右二)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參加ISSCC時和團隊合影
ADC是極具挑戰性的領域。在這個領域做模擬電路的生產和研發,是非常辛苦的探索。每次向前走一小步,都凝聚著無數工程師夜以繼日、一步一個腳印的艱辛。而且,ADC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領域。作為學生,加入這個領域,光看書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大量的實踐。實踐,就是扎進去,一步一步做,一個錯一個錯犯,一個錯一個錯修正。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來,才是研究ADC的日常。如果不能投入足夠的時間,沒有犯足夠多的錯誤,就很難成長,也很難創新。
“正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澳門大學的ADC研究才走在了全國前列。這里有28年的經驗累積。在28年時間里,澳門大學ADC團隊從無到有。無論是人才技術,還是儀器設備等,都是用28年的教訓和經驗累積出來的。”冼世榮說道。
篳路藍縷,披荊斬棘!28年后的今天,談起團隊ADC研究最大的優勢時,冼世榮說:“認清不足,才是我們最大的優勢。模擬電路,人才是非常缺乏的。大家明白微電子芯片的重要性,很多大學生未來愿意投身于微電子芯片行業。有這么多人愿意加入這個隊伍,就是最大的優勢。有這么多企業愿意投放資源,就是最大的優勢。”他深知,當澳門大學或澳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與全球其他頂尖大學、頂尖實驗室或研究團體進行比較或競爭時,總體團隊的規模體量大小至關重要。由于澳門大學及其團隊的規模較小, 所以冼世榮的團隊專注于數據轉換器和電源管理集成電路設計。他們的愿望是,為國家培養更多的科研人員,更多的研究型、應用型人才,實現在全球的ADC世界領先的地位。
回望來時路,碩果累累;邁步新征程,砥礪前行。只因他們都有一顆“中國芯”的夢想,希望祖國在未來的微電子領域擁有一片藍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