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形傳說:被“建構”的蘇美爾》
[英]保羅·柯林斯 著 曹磊 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鼓樓新悅 出品
2022.4/8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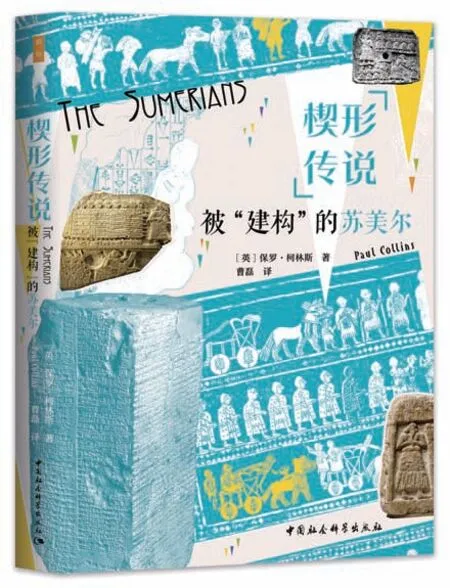
[英]保羅·柯林斯
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古代近東館館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和伊朗考古、藝術歷史。已出版著作《亞述王宮雕塑》《高山和低地:古代伊朗和美索不達米亞》。
曹磊
文學碩士,作家,翻譯。著作有《1945》《戰士之路》《從北京到曼德勒》等,其中《六千零一夜:關于古埃及的知識考古》入選第十五屆“文津圖書獎”推薦圖書。
本書為我們揭示了在過去150年當中,各國學者如何利用出土自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各類考古和文獻資料,構建出了一套以蘇美爾人為題的“知識”。作者以清晰而專業的文字講述了那片古老土地上曾發生過的戰爭,以及古代蘇美爾人創造出的文學、藝術、制度、建筑、文字等,讓那個“失落”過的古老文明重新煥發光彩,變得生動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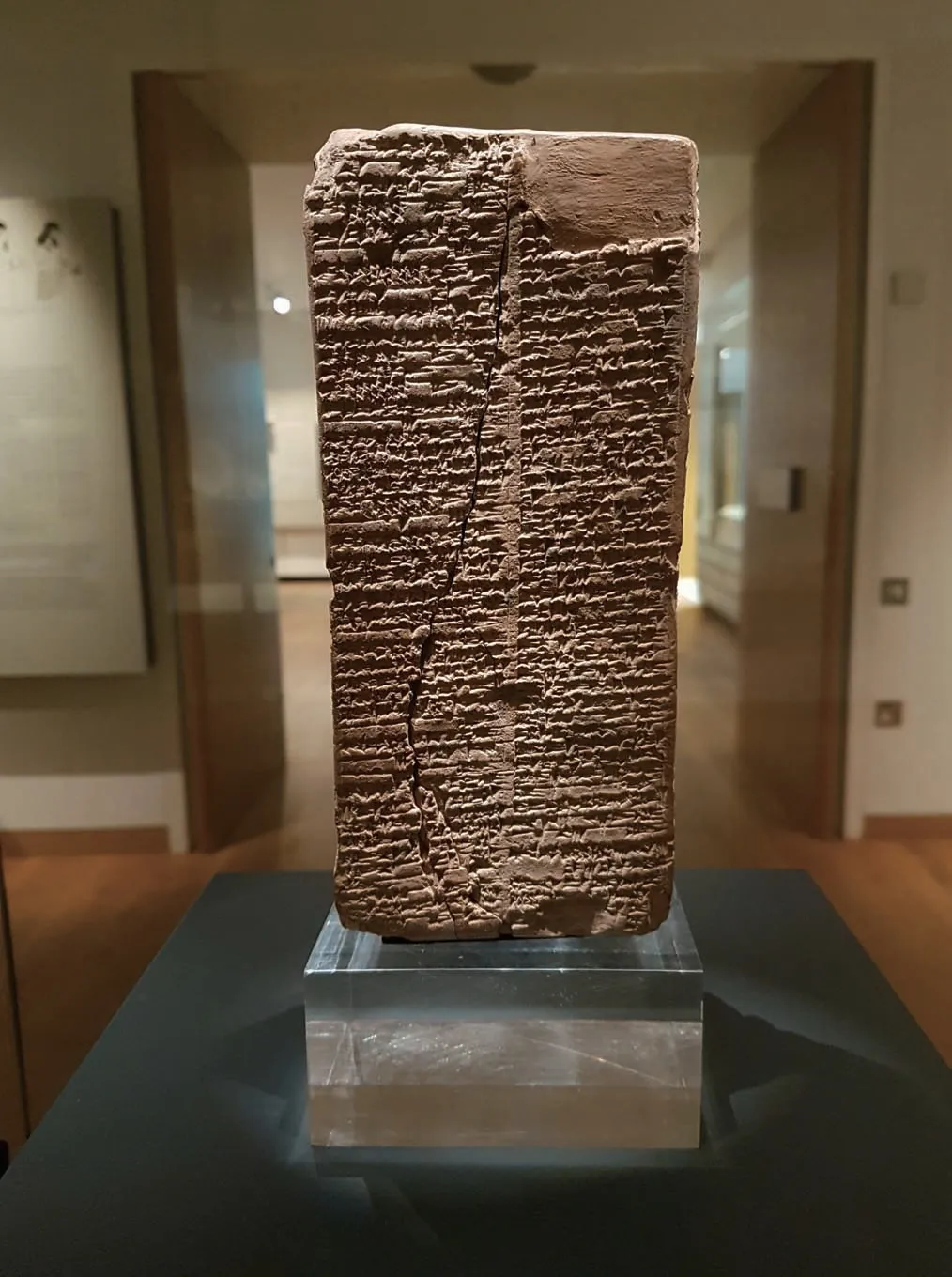
人們曾經認為,現在也經常認為,某個社會或地域是否“文明”主要取決于它所創造的社會文化和社會結構達到了怎樣的發展水平。對于社會發展水平的判斷則大多以西方世界為標尺,后者一般被視為最復雜的社會形態,也就是“最高級”的社會形態。
幸運的是,人類歷史上這種由“語義學”所引發的矛盾并非總能得到清醒的認知,進而妨礙同時期的歷史講述者建構他們的歷史。于是,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對于某些概念的“自以為是”將會對蘇美爾人理解和想象這個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
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再次告訴世人,很多時候追憶“過去”的目的往往是為“現在”服務。身在“西方”(即便如此簡單的一個定義,背后同樣存在著非常復雜的張力)的我們經常會將歷史上的其他文明和民族視為“他者”,然后通過“‘他者’如何影響和塑造了西方文明”的思維方式,將他們納入我們自己編織的那套歷史敘事和身份認同當中。
某些古代文明,例如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始終被認為在西方文明的演進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4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作為現代西方文明的起點,重新“發現”了這兩種古代文明,尤其是在美學和政治領域,它們被奉為完美和秩序的體現。
有別于這兩種從未失落過的古代文明,其他的所謂“失落文明”,比如古埃及文明,也可以通過西方探險家和考古學家的努力重見天日,進而在我們當今的社會生活中占據與上述兩者同等重要的地位。重新回歸歷史視野的古埃及文明憑借象形文字、金字塔、木乃伊之類的故事和傳說,以一種令人癡迷同時又八面玲瓏的東方“他者”形象呈現在世人面前,只不過這個“他者”形象的確立同樣基于西方人的文化想象。
美索不達米亞曾經存在過的那些古代文明雖然從未被賦予過如此重要的意義,卻依然在西方主流文化的構建過程中發揮著自身的獨特作用。就像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和古埃及人一樣,這個地區的某些古代族群,比如亞述人和巴比倫人,從來就沒有真正淡出過我們的視野。他們發出的聲音始終回蕩在《圣經》和其他古典世界文本的故事講述當中,隨后又借助古代西方、阿拉伯和波斯的相關文本得到間接閱讀和傳播。相比之下,由于語言的局限性,古代亞述人和巴比倫人留下的原始文本只能在較小的范圍內流傳。
按照歐洲人原先的文化想象,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的亞述人不過是《圣經》故事里欺壓猶太人的罪魁禍首。同時期的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則被描繪為猶太先知亞伯拉罕(Abraham)的故鄉,還是通天塔的所在地。
公元19世紀,位于尼姆魯德和尼尼微兩地的亞述王宮遺址被發現,當時的英國人認為,古代亞述文明取得的輝煌成就與維多利亞時代的工業和科技進步存在某種古今呼應的關系。置身于這樣的時代語境中,倫敦海德公園(Hyde Park)的阿爾伯特紀念碑才會以銘文的形式,將公元前700年前后營造王城尼尼微的亞述國王辛那赫里布(King Sennacherib)頌揚為現代工程學的先驅。
大概150年以前,包括西方人在內,世人其實對古代蘇美爾人一無所知,直到位于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古代遺跡、文獻得到發掘整理。話雖如此,但是單純憑借故事和傳說去想象古代蘇美爾人到底是什么樣,他們來自哪里,相貌如何,仍然是一項很難完成的任務。我們對蘇美爾文明的想象和闡釋也就無法達到古埃及文明那樣的高度,后者與西方思想之間畢竟存在著相對悠久的歷史淵源。更何況,蘇美爾人也沒有留下類似金字塔那樣可以穿越時空、為我們的想象提供參照的傳世建筑。
蘇美爾人的首次被“發現”是在 19 世紀下半葉。依靠歐洲列強的強大軍力,這個時期的西方探險家、外交家、商人和學者可以在美索不達米亞任意徜徉,記錄他們的所見所聞。出于自身愛好或者為博物館搜羅藏品的目的,他們還能夠隨心所欲地將當地文物帶回故鄉。
西方人從自身立場出發,認為當代中東地區的眾多東方民族在很大程度上與曾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那些古代族群風馬牛不相及,后者在《圣經》以及其他古典文獻中的形象反倒跟歐洲人存在很多相似性。于是,這些古代族群以及他們留下的那些建筑遺跡和藝術品,便被順理成章地劃入了西方文明的范疇。
憑借軍事和經濟實力的支持,歐洲列強可以在世界各地肆意搜羅文物,侵占古跡,還能讓那些綿延至今的古國淪為自己的殖民地。諸如此類的行為往往會以戰爭和宗主權作為遮羞布。歐洲人來到中東以后,最初的身份通常是商人和軍事顧問,再后來就變成了侵略軍。在殖民大軍的行列當中,經常還有考古學者混雜其間或尾隨其后。這些人的研究視角大多以當時剛剛成型的種族理論為立腳點。
隨著古代蘇美爾文物的不斷出土并得到研究,這種文明形式被越發深入地吸納進了有關西方文明起源的話語當中。
20世紀的多數時間里,各國列強以及各種理念相互沖突,給世界帶來了一場又一場難以想象的血腥戰爭。與此相反,古代蘇美爾人似乎是一個熱愛和平的民族,終日醉心于修建城市、書寫文字和發明車輪,除此之外再沒有留下別的東西。他們所采取的社會體制,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被視為民主政體的最早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