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傳》
錢志熙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2022.10/3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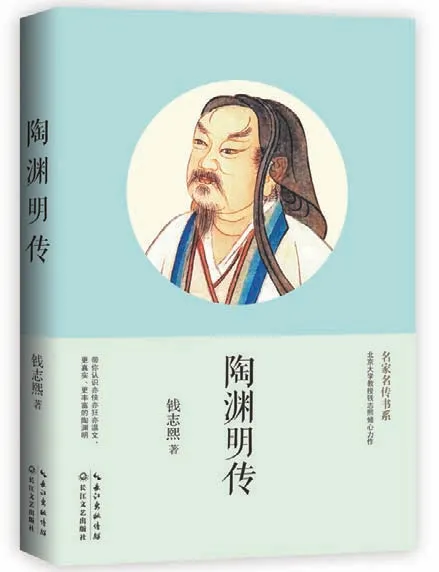
錢志熙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任中國李白研究會會長,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兼學術部主任,《國學研究》編委等。著有《中國詩歌通史:魏晉南北朝卷》《陶淵明傳》《唐詩近體源流》等。
本書沒有重塑傳統印象中隱逸詩人的肖像,而是真正走進陶淵明的內心世界,與他作生命的晤對。這場晤對,一是建立在對陶淵明生平經歷的追溯上,尤其在“士族”與“寒門”身份意識對陶淵明人生整體與生命觀的影響上,作者有著深刻而合情合理的見解;二是建立在對陶淵明所有作品,尤其是經典詩文作品的文本細讀上,這種文本細讀是探索陶淵明內心世界的一把金鑰匙。

追憶中的少年時光
進入中年以后的陶淵明常常沉浸在對青年和少年時光的追憶之中,他的不少詩篇都是以追憶為開端的。在追憶中,詩人為我們展現了自己青少年生活的色彩和情調。
從物質生活的層面來講,陶淵明小時候的家境可能還算富足,但到青年時代就近于清貧了。在陶氏家族中,陶淵明這一支并沒有繼承爵位,他的祖父雖做過太守,他父親卻是無官職無特權,再加上父親過早地去世,所以留給妻兒的田園財產應該是很有限的。魏晉間常常有父親官至守令,但因早逝而使兒女陷入孤貧之中的記載。如張華父曾為太守,但他幼年時曾為人牧羊;陶淵明曾祖父陶侃的父親曾為吳揚武將軍,但陶侃早年照樣受窮。所以像陶淵明這樣的家庭,淪于貧薄是完全有可能的。顏延之為陶淵明所寫的誄文中說,他早年“居無仆妾,井臼自任”。陶淵明作《自祭文》回顧自己的一生時,也很感慨地說,自己生來就與貧窮為伍:“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绤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既然沒有仆人,家務之事只能自理,一部分農業勞動也需要自己承擔:“春秋代謝,有務中原。載耘載耔,乃育乃繁。”陶淵明晚年罷官后,能夠從事農業勞動的能力是早年培養出來的,所以陶家雖然是一個官宦世家,但陶淵明的身份可以說是亦耕亦讀的寒儒,盡管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卻經歷過農民的生活。
因為貧困不得不務農時,陶淵明是帶著一種誠愿的心情去做的。之所以能夠這樣,除了他天性淳樸、勤勞之外,還因為他想起了歷史上那些自食其力的高士和貧窮儒生。當他含著歡悅走到谷底汲水灌園時,一定會想起莊子所說的那個因為害怕使用機械會產生機心而放棄桔槔不用、情愿抱甕汲水的漢陰老人;當他負薪道上時,也肯定會想起那位一邊挑著柴擔,一邊誦讀經書、唱著歌辭的朱買臣。所以亦耕亦讀的生活對于陶淵明來說,確實是貧困、勞苦的,但也是和諧的。后來當他奔波于仕途之上,更覺得早年的這種生活是很美好的,也是真正自由自在的:“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其二)所以在我們討論陶淵明后來歸隱田園的動機時,應該看到早年這種亦耕亦讀的生活體驗所起的作用。我們以后還會討論到,陶淵明關于農業勞動形成了一套社會理想和人格思想,他在某種角度上是先秦農家流派的傳人和發揚者。
既然是亦耕亦讀,在陶淵明的少年生活中,讀書仍然是最重要的一個主題。東晉時代,知識界讀書的風氣很淡薄,玄學家流不僅鄙視實干,同時也沒有力學之精神,他們只從事于《老》《莊》《周易》和少部分佛典,甚至有些人連老莊都沒有好好地讀就大談玄理。當時不少號稱“清談家”的人都不過是拾人牙慧而已,殷浩就說他的外甥韓康伯還沒有得到他的“牙后慧”(《世說新語箋疏》“文學第四”,第217頁)。所謂“名士”更是不需要什么才學,名士領袖王恭說過:“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說新語箋疏》“任誕第二十三”,第763頁)。殷仲文號稱一代文豪,可是“天才宏贍而讀書不甚廣”(《世說新語箋疏》“文學第四”,第275頁)。自漢代以來,文學家同時也是博學家,文學創作與博學多通的風氣是分不開的。東晉玄風扇熾而讀書風氣頓歇,無怪乎文風不振。南方士族比較崇尚實學,但經學家像范寧、范汪之輩所守的仍是漢代經生的門徑,也談不上博學多通。在這樣一個讀書風氣淡薄的時代,陶淵明卻是天性愛好讀書,自稱“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讀書一不為清言玄談,二不為窮經做注,所以陶淵明能夠超越時流,真正做到以讀書為樂: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與子儼等疏》)
這樣的讀書境界是令人羨慕的,也是常人難以達到的。這種讀書超越于功利之上,真正以讀書為人生最大的樂趣,而從書中領悟的也都是活生生的境界,打破了時空的界限,與古人作心靈的會晤。魏晉之際,能這樣讀書的人是不多的。陶淵明讀書的另一妙訣還在于在自然境界中讀書,將書本和自然放在一起賞玩,開卷有得,對景歡然,在讀書的同時也在閱讀自然。這種讀書方式更是那些經生們夢想不到的,而陶淵明從少至老都保持著這種讀書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