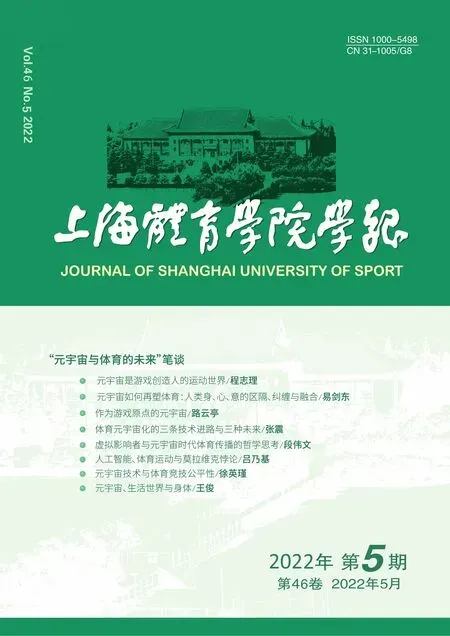中國“體育”概念詞匯的歷史源流考析
張 新,廖 雪,周 煜,李佳婕
(1. 成都體育學院 體育史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41;2. 成都體育學院 研究生院,四川 成都 610041)
現代漢語的許多重要概念詞匯都產生于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或者直接從西方語言中翻譯而來,或者借用“日本式漢語”的現成翻譯。不管以什么方式融入漢語體系,其都是東西方文化交匯碰撞的回音,是新概念、新思維在古老東方文化中的落地生根。中國“體育”概念群的形成和發展,表明中國人開始將這些語言概念作為思維的基本要素,深度思考人類特殊的身體運動現象。對于東西方“體育”概念的歷史源流,日本學者岸野雄三曾做過系統的梳理,中國學者周西寬、韓丹、羅時銘、楊樺、譚華、郝勤、任海、王廣虎、郭紅衛等也做過非常有學術價值的探討。筆者力圖從東西方體育概念的演變和對比出發,再次爬梳近代中國體育概念體系的來龍去脈及其表述維度,查考體育、體操、運動、競技等近代新詞的流行時間,以及“體育”與“教育”“衛生”等相關概念的交互影響,以此揭示“體育”概念的語義變遷。
1 西方“體育”(physical education)概念的產生
中國“體育”詞匯是譯介、借用西方“體育”概念的結果。按時間順序,從古代起西方“體育”概念主要名詞術語依次出現的是競技(athletics)、體操(gymnastics)、運動(sports)等,而“身體訓練”(physical training)、“身體教育”(physical education)是文藝復興之后相繼形成的詞語,是西方現代文明形成過程中學科發展和學校教育的產物,表明現代身體運動在生理學、心理學等學科的支撐下,發展成為具有現代實驗科學特征的規范性活動。中國、日本的“體育”一詞最初就對應譯自“physical education”和“physical training”,直接的詞匯來源是英國思想家斯賓塞的專著《教育論》(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因此,簡略了解西方體育術語體系的源流,理解對中國影響最大的英語體育詞匯的準確表意,是解釋中國“體育”概念語義發展的出發點。
“競技”(athletics)是古代希臘最早出現的體育詞語,據目前國外學者考證,公元前10—前9世紀產生的《荷馬史詩》中就有“競技”(athletics)一詞的原型,包含了獎品、較量等意思[1]。“體操”(gymnastics)則是在公元前5—前4世紀時出現的詞語,在希臘文版的《柏拉圖全集》中可以檢索到13處標準的“體操”用語,其中一個章節柏拉圖假借蘇格拉底與格勞孔的對話,闡述了用體操訓練身體的重要性[2]。相比而言,“競技”(athletics)比“體操”(gymnastics)出現得更早,說明作為游戲高級形式的競技運動很早就進入了人們的生活,在原始文明時期的荷馬時代就已經盛行。反之,作為滿足城邦時代公民普遍健身需求的一種社會建構,“體操”(gymnastics)是社會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研究古希臘、古羅馬體育的美爾庫里亞利斯在他的《體操術》一書中辨析了“體操”與“競技”的差別:“體操”是在一套理論指導下的身體養護方法,目的是使人身心達到良好狀態,促進身體的全面發展,練習者為此目的要采用多個項目進行綜合練習;“競技”運動員為了在競技賽會中折桂通常專攻一個項目,著重訓練單項運動的核心素質,其中體重是摔跤、搏擊等重競技項目決勝的關鍵因素,運動員要通過強制性的大量飲食來增加體重。美爾庫里亞利斯批評這種畸形發展的運動現象時說:“為了增加體重,不斷向胃里充填豬肉、野羊肉、牛肉······,使職業競技者陷入病態。”[3]實際上,希臘語“競技”一詞已經直接表明了競技活動的特性,其前綴詞根“Athlon”意為“獎品”[4],與中國古代“賽錦標”一詞中用“錦標”代表錦緞等獎品的構詞方式異曲同工,說明這類競賽活動參與者都有爭奪獎品的行為動機。由此可見,從古代希臘開始,就存在2種價值追求迥然不同的體育行為:“體操”講求身體的均衡發展;“競技”著眼于取勝而不是健康,著力訓練超強的單項運動素質。
“運動”(sports)是中世紀英國流行的詞語,從詞源上看,演化自13世紀出現的“disport”一詞,用否定前綴“dis”表示離開工作場所進入娛樂消遣狀態,其語義在中世紀意指多種娛樂消遣活動,到文藝復興以后才逐漸特指體育運動[5]。相比于擁有海洋屏障的英國,地處歐洲大陸的德國因為戰爭頻繁,特別注重國民的身體鍛煉。1811年楊氏沿用中世紀騎士比武中的一個德語專用術語“turnen”代替“gymnastics”,創立了“楊式體操”,主要由攀緣、懸垂、平衡等器械體操配以徒手體操、兵式體操等訓練方式組成,講求實用功效和紀律服從,落腳于身體機能、技能的培訓,發展成為風行近代世界的德國體操體系。
“身體訓練”(physical training)和“身體教育”(physical education)是西方進入現代社會之后流行的2個體育詞語。根據在線圖書電子資源檢索結果,英國學者馬爾卡斯特[6]1581年在《兒童教育論》的文句中開始用“training”一詞來表述符合兒童天性的身體訓練; 1733年法國學者杜博斯[7]在法文著作《詩畫論》中使用了“身體教育”(éducation physique)。在西方近代早期語境中,這2個詞語的語義相近,可以互用。有意思的是,斯賓塞1859年在《不列顛季刊》上以“physical training”為題發表了論文,1865年他將這篇論文收入《教育論》作為全書第4章再版時又改標題為“physical education”,說明此時“physical education”用來表述“體育”更加正式[8]。之后,這2個產生于兒童教育領域的相近詞語日趨分離,分別表達“ 身體教育” 和“ 身體訓練” 的意思。
體育活動的多元性使得體育術語紛繁復雜。郝勤[9]從“形態+價值”的定義出發,將體育活動的歷史源流分為2種社會行為:游戲與身體訓練。借用這一視角,筆者把眾多體育術語分化串聯為兩大類型。游戲類術語包括游戲(play)、運動(sports)、競技(athletics)。游戲源于人類游戲本能,與人類相伴而生,除了身體游戲外還包括拼字游戲、猜謎游戲等。運動(sports)則逐漸特指付出體力的身體運動,包括休閑和競賽類運動,后期因為競賽型運動的社會能見度日益顯著,運動(sports)又側重于表意競賽活動,與競技(athletics)語義相近。這一類活動的出發點都是游戲玩耍,游戲活動的目的是享受過程的愉悅,競技運動則在一般游戲基礎上發生了價值偏移,參與者通過體能、技能的較量爭取獎品、名譽等激勵,具有追求結果的功利性目的。身體訓練類術語包括“體操”(gymnastics)、 “身體訓練”(physical training)、“身體教育”(physical education)等,人們習慣性地把這類活動看作非對抗性的身體練習,在實施過程中講求做了幾組練習、達到了什么樣的身體鍛煉效果。
西方體育概念詞匯的發展從歷史的時間線上呈現了體育活動的形態變化:伴隨人類歷史的展開,體育活動廣泛存在于人類的社會生活之中,社會人群或投身于競賽游戲,或圍繞軍事、健身等需要進行身體訓練,是陪襯、補充生產勞動等例行生活的一種古老行為方式。因此,體育最初就是一種社會性存在,而作為教育組成部分的身體運動的普遍推行得益于現代文明的發展,尤其是中國、日本譯作“體育”的“physical education”一詞,屬于西方文藝復興之后產生的教育學專用概念,是社會傳承已久的“體操”與“運動”等固有運動方式被引入身體培訓場所的結果。
2 中國“體育”概念詞匯的譯介與普及
東西方文化的激蕩使上述體育新概念涌入東方大地。現代漢語的絕大多數新詞的出現都是為了表達近代西方的新概念和新事物,這些概念在漢語文化圈中都經歷了一個詞匯化(采用一個詞來指稱一個概念)的過程。那么,眾多的體育新名詞是如何出現、定型并普及的,最終編織了怎樣的意義網絡來解釋人類的體育現象,這是體育學術領域需要廓清的基礎性工作。
2.1 體操(gymnastics)實踐與概念的詞匯化
近代中國人最早接觸并能理解的西方體育運動就是體操。從19世紀中葉肇始,中國在軍隊和軍事學堂中就陸續開展了體操實踐。然而,直到19世紀90年代以前,體操的名稱在中國都沒有詞匯化。在洋務派軍隊中聘請西方職業軍人擔任教習,所用口令開始多為英語、德語音譯,士兵難以理解、記憶,后來為了啟用口令和術語的漢語譯名,一系列的軍事書籍被翻譯,其中涉及體操并且影響較大的書籍有《洋槍隊大操圖說》(1868年)、《陸操新議》(1884年)等。查考這些書籍的原文,均未形成“兵式體操”等后來的標準概念用語,而是用“步伐”“列隊之式”“走動操法”“泰西操演之法”等短語或者描述性語言配以圖示來說明具體的隊列操練方法。同樣,1890年譯自英文的普通體操教材《幼學操身》也未使用“體操”一詞,該書圖文并茂地將當時的徒手體操和器械體操介紹得非常清楚,繪圖講解了“木棍”和“兩頭鐵錘”(啞鈴)的器械練習,與1887—1889年訪問日本的清廷官員傅云龍所記“體操為學校通例······適見體操鈴、棍二法”[10]的見聞相印證,說明木棍和啞鈴是當時最流行的體操器械,只是在中國還未形成標準化的稱謂。
洋務運動之后,維新派人士開始關注體操訓練。康有為1891年創辦具有近代學校性質的新式書院長興學舍時,沒有“體操”一詞可以借用,在他同年撰寫的《長興學記》中用“槍”來代指體操,這是一門在校外“擇日學習”的課程。康有為將這門課程與先秦六藝教育中的“射”“御”進行類比,認為彼此性質相同而射、御“于今無用”,應該練習可以“經世通用”的新技能,目的是培養國家的“干城”[11]。康有為在學校中設置了“博文”“約禮”“干城”等學科的學長,協助教員實施管理。 1901年,梁啟超在評述長興學舍的文章中直接將“干城科學長”的職責注解為負責“督率體操”[12]64-66。可見,康有為在開辦新學無所憑借的年代,采用了“槍”“干城”2個既有字詞表意新式體操訓練。
1896年是“體操”這一詞語在中國普及的節點性時間。“體操”一詞借用自日本的翻譯,據岸野雄三考證,日本早在1873年就將“gymnastics”統一翻譯為“體操”[13]23。顯然,日本翻譯分解了這個西語單詞中表意“裸體”與“訓練”的2個語素,合成了“體操”這一漢語文化圈的新詞。中日之間漢字同根同源與表意相通,使彼此很容易交流互鑒,至1896年中國也開始普遍使用“體操”一詞。梁啟超在1896年發表的《變法通議》文章中多處提及“體操”,并對日本的幼兒體操課程進行較為詳細的解讀:“一下鐘復集,習體操,略依幼學操身之法。或一月或兩月盡一課,由師指授,操畢聽其玩耍不禁。”在梁啟超的同一篇文章中,“教育”還是一個沒有流行的生僻詞,以至于他在介紹日本課程設置的“教育”名目后面特別加按語解釋—“言教授及蒙養之法”[12]1-63,而“體操”已經無須注解,說明已經被國人普遍接受。
1898年變法失敗前的梁啟超并沒有去過日本,他是從何處接觸到“體操”一詞的呢?原來此前黃遵憲、傅云龍等人的日本游歷見聞中已經介紹了“體操”,尤其是黃遵憲1887年成書、1895年刊行的《日本國志》對維新派人士影響巨大,梁啟超曾經通讀該書并為之作后序,所以“體操”一詞通過這些記述日本風情的書籍傳遞到了中國。同樣是從1896年起,中國開始大量向日本官派留學生,這些留學生除了學習相關專業知識外都要學習體操。1899年,四川省官員丁鴻臣去日本考察時恰逢張之洞的子孫在此留學,他在記錄他們的學習狀況時說:“張薌帥文孫、剛孫在此中學校,于時亦負皮囊、習兵操初級也。”[14]張之洞在黃遵憲《日本國志》尚未刊行之前就讀過黃遵憲的手稿,1899年或許由于親屬留學日本,張之洞對于“體操”的了解更加深入,他同年上書朝廷對“體操”概念進行闡釋:“又體操一事,為習兵事者之初基,即與舊傳八段錦、易筋經諸法相類,所以強固身體,增長精神,必不可少。”[15]
無論以古代的“射”“御”還是八段錦、易筋經來類比認知現代西方體操,“體操”一詞1896年后已經固化流行,并逐步以“器械體操”“徒手體操”“兵式體操”等名詞構成了體操的門類。
2.2 體育(physical education)與“教育”概念的同時傳入
體育(physical education)是比“體操”稍晚流行的詞語。在日本,“體育”一詞的定型比“體操”一詞晚,到1876年才第一次將“physical education”譯作“體育”,至1886年逐漸成為通用詞語[13]24。在同時期的中國,“教育”“衛生”“體育”等概念的翻譯都還沒有固化,黃遵憲在1895年出版的《日本國志》一書中共有4處提及“體操”,卻無一處使用“體育”這一概念[16]。深受《日本國志》影響的梁啟超,在1898年流亡日本之前只使用過“體操”一詞,對于“體育”一詞似乎并不熟悉。
中日兩國對“體育”概念的深度理解都得益于英國思想家斯賓塞的《教育論》。斯賓塞不是“德、智、體”三育觀念的首創者,卻是對中日影響較大的代表性人物。1880年日本譯員尺振八就全文翻譯了斯賓塞的著作《教育論》,他將“三育”(Intellectual,Moral and Physical)翻譯為“心智教育、品行教育、體軀教育”[17]。至1886年,有賀長雄在其所著的《標注斯氏教育論》一書中正式將“三育”翻譯為“智育、德育、體育”[18]。1882年,中國留美學人顏永京以“肄業要覽”的書名翻譯了斯賓塞《教育論》的總論部分“什么是最有價值的知識”,翻譯內容尚未涉及斯賓塞著作第4章“論體育”。由于斯賓塞英文原著的總論部分沒有出現“physical education”一詞,文內只有一處使用了“physical training”,加之顏永京采用創作式翻譯,故難以查證譯著中的漢語對應譯詞。不過書中內容已經涉及體育,顏永京用“嬉戲”“養身衛身之計”等傳統術語來指稱身體運動[19]。1895年3月開始,嚴復通過發表《原強》等文,加上1897年在其所譯《天演論》中的按語備注,重點介紹了斯賓塞的教育學說。嚴復造詞講求音韻,文體接近駢文,盡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朗朗上口流行一時,但將“衛生”譯作“保身”,將“教育”譯作“明民”,并未作為標準概念用語流行。特別是嚴復將“三育”學說譯作“民智、民德、民力”,發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時代呼喚[20],影響了當時的一代中國人。但作為概念用語,嚴復的翻譯偏于“古雅”而難以普及,后來嚴復在他自己文章表述中也改用了“體育”一詞。
1897年,中國出現了“體育”一詞。康有為1897年完成編撰和刻印《日本書目志》,在第十卷“教育門”中列有一冊由毛利仙太郎、神保濤次郎合著的《體育學》書目[21]。康有為本人當時并不通曉日語,主要依靠其女兒康同微幫助翻譯。在此,已經采用了“教育”“體育”的標準譯詞。日本的快速崛起使中國人倍加關注,隨著游學日本的人員和相關譯介的增多,一時之間形成了“西學東來”的局面。1898年,姚錫光接受兩廣總督張之洞委派專程赴日本考察學制和學校選材授課之法,回國之后所著文章對中國近代教育產生了較大影響。姚錫光1898年6月在《時務報》發表文章《日本各學校規則》解釋說:“日本教育之法,大旨概分三類,曰體育,曰德育,曰智育。故雖極之盲啞,推及女子,亦有體操,重體育也······”[22]梁啟超在流亡日本期間,開始在多篇文章中使用“體育”一詞,1901年在《南海康先生傳》中通過文字和圖標明確表達了德育、智育、體育三育并重的思想[12]66。同年,朱樹人在《南洋公學蒙學課本二編編輯大意》中說:“泰西教育之學,其旨萬端,而以德育、智育、體育為三大綱。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體育者,衛生之事也。蒙養之道,于斯為備。”[23]在此,又將“體育”作為“衛生”的關聯概念進行定義解讀。 1902年項蘭生以“嵐僧”的筆名在《杭州白話報》分8期翻譯了日本作者西川政憲的《國民體育學》,體育的概念詞匯日益普及[24]。在洋務派重臣張之洞1904年撰寫的《學堂歌》中出現“教體育,第一樁,衛生先使民強壯”[25]的歌詞。可見,“體育”由此逐漸成為官方接受的流行用語。
2.3 競技運動(athletics sports)話語體系的建構
競技運動(athletic sports)是近代英美國家風行的體育活動方式,主要通過教會學校、基督教青年會傳入中國。相關的英語單詞在中國出現較早,《字林西報》1868年4月21日就有一則以“The Athletic Sports”為題的報道,介紹了旅華西方人一場比賽的跳遠、跳高等項目成績[26]。有中國人參與的運動會早期主要在學校開展。1879年美國圣公會創立的上海圣約翰大學是舉辦運動會最早的學校,自1890年起,學校就每年定期召開運動會,學校創辦的雙月刊雜志St. John's Echo持續報道了這些競賽活動,例如,1891年就以“SPORT RUN”(賽跑運動)、“HIGH JUMP”(跳高)等體育名詞術語記錄了優勝者的姓名和成績。遺憾的是St. John's Echo1905年才出中文版,因此,在這之前看不到相關報道對應的中文譯詞[27]。
劉正埮主編的《漢語外來詞詞典》將“運動”“競技”“運動會”等體育詞語都列為從日本引進的外來詞,從現有資料看,事實也的確如此。查閱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人物早年涉及體育活動的文獻,均未將“運”與“動”連用形成概念性詞語。1886年由李鴻章作序、英國傳教士艾約瑟翻譯的《西學啟蒙十六種》叢書中的《希臘志略》,將“Olympic Festival”和“Olympian Games”對譯成“俄倫比亞會”,沒有使用“運動”一詞[28]。日本使用相關詞匯的時間較早,至少1887年中國外交官員傅云龍游歷日本時就已經廣泛使用。在傅云龍后來撰寫的《游歷各國圖經》一書中就出現了“帝國大運動會”“勝者之金牌”等體育概念用語[10]。到1904年前后,“運動”“運動會”等已經是中國傳播度較廣的通行用語。上海的雜志《女子世界》1904年以“大運動會”為題,報道了“日本女子大學第四回秋季大運動會”的盛況[29]。這個時期眾多新式學校陸續開始定期舉辦運動會,1904年保定師范學堂、1905年京師大學堂都在其學校運動會的文告中使用了“運動會”這一標準用語。
日制漢語的新概念造詞偏愛從中國典籍中尋找詞源,如“運動”取自董仲舒《雨雹對》中的“運動抑揚,更相動薄”[30],由此很容易為中國人所理解接受。當然,中國古代已有一套游戲競賽類的體育詞匯,例如“玩”“賽”“游嬉”“賽錦標社”等,與西方“運動”系列詞匯的表意相近,可以互用。于是在中國運動比賽的報道中就出現了“錦標賽”“賽會”“奪標”“折桂”等本土習慣用語與“運動”“金牌”等日本借詞夾雜使用的狀況。特別是隨著中國近代運動競賽的發展,一些反映運動精神的詞匯也開始引起中國人的關注,并逐步完善了其翻譯。“Sportsmanship”被意譯成“運動君子精神”“運動家精神”,“fair play”被林語堂音譯為“廢厄潑賴”(公平競爭),說明中國近代形成了一套表述“運動”行為實踐與精神價值的話語體系。
3 中國“體育”概念的本義及意義嬗變
近代西方概念譯詞一旦融入中國的語言知識體系,就可能脫離原來對應的西語詞匯,衍生出新的語義。中國體育概念詞匯就經歷了這樣一個演變過程,在本源意義之外又附加新義,發生了意義的連續嬗變。人們不斷改變概念定義的目的是更好地從主觀上去命名和解釋外在體育現象的變遷。
3.1 “體育”的原初定義及其與“體操”“運動”之關系
中國“體育”概念始發于“physical education”,而斯賓塞所論“體育”主要針對初等教育體系中的兒童。中國近代自嚴復的翻譯肇始,就將“體育”范圍擴大到了全體國民,體現了近代中國人應對環境壓力的警醒與努力。所以,早期“教育”“體育”的定義背后都充滿了民族競爭的社會進化論思想。1915年中國出版的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國語辭典《辭源》就將“教育”定義為:“助人類之發達,以適于世界進化之作用也。”《辭源》將“體育”釋義為:“教育學名詞,所以輔助身體成長發達者。”[31]1915年蔡元培提出的“體育”定義為:“體育者,循生理上自然發達之趨勢,而以有規則之人工補助,使不致有所偏倚。”[32]歸納近代中國眾多“體育”定義的表述,均將體育看作是一種后天人為的活動事項,即按照先天自然的生理結構,有計劃地通過身體運動促進國民身心健全發展。這些“體育”概念的原初定義界定了體育活動的性質和范圍,“體育”是立足國民教育目標所開展的身體運動的總稱。
那么“體育”與“體操”“運動”之間又是何種關系呢?特別是1922年學制改革之前,中國學校體育課程均稱作“體操科”,很容易讓人誤解“體操”當時為“體育”的同義詞。事實上恰恰相反:一方面,自1901年起,“體育”與“體操”二詞在中國當時的語境中日益普及且并行不悖,梁啟超、陳獨秀、毛澤東等均在一篇文章中同時使用了這2個詞,二者表意不同可謂一目了然;另一方面,課堂上教習體操也不是中國的特例,在1918年“一戰”結束之前,無論日本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學校課程中進行體操教學幾乎是國際通例,甚至連上海圣約翰這樣以課外競賽運動出名的教會大學,1895年之后都要求學生按時參加早體操和軍事訓練課,進行兵操、啞鈴操以及持槍練習[27]。1915年,孫掞在《體操要義》一文中闡明“體操”“運動”的詞義實指具體的課程名稱與身體運動方法,他說:“視為正科者,即為體操科。體操科者,即學校體育中練習身體之一種方法。若以此體操科命之為身體練習之課業,其名稱也殊適當。”孫掞同時認為課外體育運動也不可或缺,體操課程教學與課外運動游戲相結合,可以實現學生身體“完全發達”的目的[33]。“一戰”后,德國衰敗一時,德國體操體系的弊端遭受非議,英美國家的國際影響力占據上風,盎格魯-撒克遜的運動體系由此成為世界主流體育項目,并以競賽為核心形成了覆蓋全球的賽事體系。受到世界體育潮流影響,1922年以后中國“體操科”更名為“體育科”,運動游戲項目進入了學校體育教學的正課。可見,“體育”是揭示身體運動屬性的“形而上學式”的抽象概念,“體操”與“運動”則是形而下的具體概念。簡單而言,人類的一些具體運動形式自被創造出來后,逐漸體系化和模式化,具有了歷史的傳承性,使人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按固有規范進行習練。“體操”和“運動”即被包納到近代中國“體育”概念的范疇,成為輔助“身體教育”的具體運動方式和練習手段的稱謂。
取自于漢語字庫的“體”與“育”二字,合成之后被賦予了現代語義,逐步在西方原初概念的基礎上加入了中國人自己的主觀理解。 “體育”一詞也逐漸脫離了“physical education”的原始對應譯詞,“athletics”和“sports”也時常被譯作“體育”。例如,1914年前后成立的相關體育組織“St. John's University Athletic Association”被漢譯為“圣約翰大學體育協會”,“East China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被漢譯為“華東六大學體育聯合會”[27]102-106,顯示了“體育”一詞在中國語言體系中的泛化使用。
3.2 “體育”概念與實踐的疏離及變化趨向
對比東西方“體育”概念生成的歷史進程,中國近代“體育”概念經歷了一個逆向生長的過程。由于在西方社會生活中歷史久遠的運動游戲傳統,加上古代軍隊、體操家、騎士貴族的身體訓練傳統,在學科發展和學校興盛的18世紀交匯形成了“身體教育”(physical education)的概念。近代中國則是基于“強國強種”的強烈愿望,高倍放大了“身體教育”(physical education)的觀察視角,成為近代中國人理解身體運動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中國近代的“體育”概念明顯帶有目的論色彩,把一切身體運動都納入了國民身心培養的總目標。這樣的主觀理解,為提倡體育運動形成了強大的理據和社會共鳴,表明近代中國人在教育、衛生、生理等新學科思維的引導下,對人類身心極強的教育可塑性有了清楚的認知,使體育運動超越其古代形態成為制度安排和公共事業。但體育單一功能屬性的強調與外在事物的對應關系產生了疏離,作為教育范式的“體育”無法囊括身體運動廣泛的社會性存在,“運動”的價值內涵就往往超越“體育”本義的框架邊界,產生概念使用的矛盾與沖突。1915年,蔡元培曾經評論學校體育運動員專攻某一項目的現象:“而專門演習,則生理上一部分偏于發展,而其他部分不能與之適應,失體育之本義矣。”[34]顯然,蔡元培是從身體平衡發展的標準出發去批評競技運動員的行為背離了體育本義。事實上,近代中國已有人意識到了定義與現實之間差距,鶴鎮在《運動競技之傳統》一文中就說:“并非所有現代化的競技組織,皆具有教育的目的,例如職業化的運動和競賽顯然是在達到商業的目的······”[35]近代中國人在體育實踐中已經感受到了“詞”與“物”不對應的困惑。
一個時代的“體育”概念反映了同時代人對體育現象的理解。體育活動客觀上是一種多元的社會性存在,在不同的社會場域有不同的目標追求和價值指向。中國近代“體育”概念始發于國民“身體教育”的驅動,在“人類體能性身體活動”的廣義概念中加上了“教育”的前綴限定。然而,“體育可以作為教育的一種形式與資源,而非先天便隸屬于教育,二者不存在包含與被包含關系”[36]。因此,中國近代“體育”概念的內涵變化是從狹義向廣義延展,因為人們總是試圖把合適的名詞賦予給被表象的事物,面對外在事物的不斷變遷和發展,“體育”的語義也隨之嬗變。1944年,袁敦禮在《談談體育一詞如何解釋的問題》一文中針對“體育是身體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這一觀點的局限,提出了“從身體活動中來教育”(educ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的概念[37],這一細微變化雖然沒有翻越教育學名詞的藩籬,但內涵更加寬泛,意圖加強職業化、商業化社會體育的教育價值。到1952年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成立時,采用了“體育運動”一詞,對外的英語名稱中突出了“sports”的位置。究其緣由:①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的成立,本身就是為了推動中國競技體育加入以奧運會為核心的世界運動競賽體系;②國際權威體育組織越來越多地使用“sports”作為身體運動的上位概念,“體育運動”表達了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意向,也擬通過這樣一個復合名詞涵蓋人類身體運動的多維價值指向。時至今日,人們只要在中國語境中用口語說“這個人喜歡體育”,聽者就會明白其意,并直觀地浮現出此人生龍活虎喜歡運動的形象,約定俗成且不會產生歧義,說明“體育”已超越教育領域被廣泛運用。
4 結束語
概念是思維的邏輯起點,人們在概念的基礎上建立起解釋外在事物的知識網絡。近代中國人從國民“教育”和“衛生”的本旨出發認識身體運動的價值內涵,進而抽象出“體育”這樣一個上位概念,把“體操”“運動”“競技”等一系列身體活動用語都集合到該詞語的名下,形成了表意身體教育活動的概念集群。但國民身心塑造的單一表述維度無法涵蓋身體運動事實上的多維價值取向,其中競技運動的價值追求就超越了狹義“體育”的邊界,運動競技除了間接衍生的身心鍛煉功能之外,更多展現了消遣、競賽和社交的功能,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公平競爭”“為國爭光”等價值意義。尤其是國際運動競賽與職業競賽表演的日益繁榮,改變了體育的實踐樣態,使中國的“體育”概念逐漸從原初狹義的教育學名詞向表述整體社會體育現象的廣義界定轉化。最終,人們不僅把促進身體均衡發展的身體練習活動看作是“體育”,也把有益心智健康、融洽社會交往的運動消遣或在各級競賽中奪標的體能活動均看作是“體育”。
作者貢獻聲明:
張 新:提出論文主題,設計論文框架,撰寫論文;
廖 雪:設計論文框架,修改論文,核實資料;
周煜、李佳婕:調研文獻,撰寫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