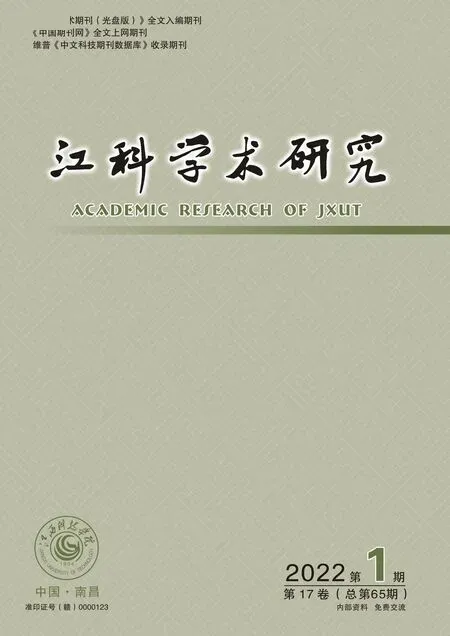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提高時政報道傳播力的策略
謝愛民
時政報道是報紙、廣播電臺、電視臺及網絡媒體等媒體對國家政治生活中新近或正在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其報道范圍主要表現為政黨、社會集團、社會勢力在處理國家生活和國際關系方面的方針、政策及活動。時政新聞作為傳播黨和政府聲音的一種主要報道形式,其與社會類、法制類及情感類等“自帶流量”的報道相比,由于肩負著宣傳黨的政策、傳播當的決策及密切聯系群眾的職責,而更難把握其報道內容,同時遭受新媒體時代所帶來的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及傳播發生的革新的影響也極大。鑒于此,反觀彭拜新聞客戶端、學習強國APP、壹深圳APP,以及《新聞啟示錄》《新聞深一度》等多樣化的時政新聞樣式,關注及探討時政新聞如何立足新媒體時代背景,將“影響”轉化為“動力”,在堅持其“權威性”“嚴肅性”原則的同時,以“內容為王”的理念指導下,破除以往“中規規矩”“艱澀難懂”的刻板印象,生產讓受眾喜聞樂見的報道內容及形式,進而提高其傳播力。
一、新媒體時代阻礙時政報道傳播力的因素
傳統紙媒創辦以來,傳播具有較強政治性、政策性等特點的時政新聞即是其主要工作,同時還自覺肩負著黨和政府的喉舌的重任,以此發揮構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功能。但是,伴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迭代式發展及廣泛應用,我國傳統媒體遭遇強烈的沖擊,進而愈加暴露出傳統時政報道方式單一,框架限制明顯等制約其傳播實效的問題。
(一)語言乏味冗長 報道缺乏吸引力
時政新聞不受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文字、語言生硬,缺乏生動性和形象感,且還陷入模式化的生產套路中,進而以千篇一律的報道八股傳至受眾,在一定程度上嚴重背離了新聞領域中的“三貼近”原則。此外,傳統的時政報道,不僅語言生硬乏味,而且篇幅還較長,與新媒體時代文章短平快的要求嚴重背離,致使報道缺乏吸引力。而且,當前時政新聞受新媒體時代的影響,其傳統單向傳播模式雖然已經革新為雙向互動的傳播模式,從而促使用戶不僅不再被動接受語言乏味的時政信息,而且還有權限將個人觀點融入語言表達和解讀中,對時政新聞進行再創作。但是由于用戶自身媒介素養參差不齊,而各新媒體平臺中把關角色的模糊,進而導致時政報道的質量良莠不齊,以及公信力的不足,并從整體上降低時政報道的傳播效率。
(二)程序性內容過重 用戶體驗感差
從新聞價值的五要素衡量時政報道,可知其是一種十分重要而具有較大信息量的新聞類別。也正是因此,使得記者在進行時政報道時,尤其重視其諸如名字、職務等程序內容的正確與否,甚至過于依賴對時政現場文件、講話等原件的摘抄,進而致使時政報道內容在挖掘和把握上較為膚淺。此外,新媒體時代下的“新”,其主要表現在信息內容的創作者與其消費者之間有著更強的互動性。鑒于此時代背景,用戶已經不再滿足于對時政信息單方面的獲取,并且更會對程序內容過重的時政信息產生慣習性的麻木,由此也會促使他們產生與時政報道頻繁互動的欲望。但時政報道程序化的束縛,又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用戶對時政報道參與的需求,其結局必然是用戶體驗性差。
(三)傳播形式單一 同質化嚴重
新媒體時代,諸如澎湃新聞、學習強國、今日頭條等媒體客戶端的層出不窮,促使新聞傳播形式多樣化的發展,進而滿足了現代人對信息獲取的差異化與個性化的需求。但是傳統時政報道由于形式單一,與新媒體技術的融合有待于提升,主要表現在應用層面,對新媒體的認識局限在其渠道功能,而未挖掘其對傳播形式的豐富。同時,還表現在融評、在線互動等傳播領域,因良好傳播環境的缺乏而致使新舊媒體在時政信息內容融合上未能與時俱進。此外,新媒體時代的時政報道記者缺乏融媒體運營理念,從而導致雖然當前多種移動信息終端共存,但是它們在傳播方式上卻表現出嚴重的同質化,比如在報道國家政策文件時,傳統電視節目、官方兩微一端,均采取諸如文字概述、文字+圖片等單一的表現形式,而沒有依據不同終端載體的特性,結合載體用戶使用習慣,對政策文件內容進行差異化轉播。
二、新媒體時代時政報道傳播力提高策略
新媒體時代融媒體運營理念的形成,促使時政報道傳播平臺呈多樣化的發展態勢,但時政報道中存在的諸如語言乏味,質量欠缺;程序性內容過重,用戶體驗感差;傳播形式單一,同質化嚴重等問題,卻明顯制約著其傳播力的發揮,對時政報道的傳播網建構造成較大影響。對于此,本文以用戶需求為導向,在遵循內容為王的報道原則下,結合時政報道具有的諸如權威性等優勢,在重塑的過程中,進一步提高時政報道的傳播力。
(一)創新表達方式提升時政報道的閱讀效率
新媒體時代,既是海量信息共存的時代,又是一個遵循“用戶至上”即由用戶選擇信息、快讀閱讀的經濟時代。于此說明,信息的多樣化,在拓寬著著用戶的選擇空間的同時,也使得曾經語言乏味且冗長的時政報道模式,喪失了時代需求,進而難以產生經濟效益。鑒于此,新媒體時代的時政報道應與當前用戶接收習慣與時俱進,進而創新表達方式,實現時政報道閱讀效率的提升。
具體而言,首先應在標題制作上契合現代傳播特點,將最新鮮、最重要及最有特點的實時和觀點,凝練于標題之中,如由昆明報業傳媒集團推出的掌上春城客戶端,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周年重大主題活動中,所推出的系列新媒體時政報道產品如《安全感!是“暖男”昆明給你的最好守護》《昆明的詩和遠方全在你的“腳下”》《回看昆明70年巨變,我更愛家鄉了》等,其標題在散發時代溫情的同時,也促使硬新聞實現了軟著陸。其次,新時代下的時政報道,應從宏大主題中深挖用戶的“趣點”,而后運用“清新”文風替代乏味冗長的八股語言給予采寫。如在2021年全國兩會電視端節目中,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新聞啟示錄》欄目,從公眾工作與生活中,尋找時政報道的切入點,在探討“數字化治理”主題時,將報道的重點聚焦在如何運用數字化管理破解上班族的考評機制問題。而且在探討“鄉村振興”話題時,以南平鄉村櫻花園中景色為導入,進而引出鄉村振興的意義與路徑。此外,在節目中還會適時地設置興趣點,進而激發受眾的好奇心,提升時政報道的閱讀效率。最后,智能手機的深入普及與廣泛應用,在加速淺閱讀時代的來臨的同時,也革新了用戶接收信息的慣習,即習慣閱讀短句式、短篇幅的文章,于此也亟需時政報道應摒棄傳統的長篇大論的寫作模式,并且在篇幅把控上,盡量做到短小精悍,意味悠長。
(二)堅守“內容為王”理念增強時政報道的服務性
新媒體時代下的網絡平臺,不僅是傳統時政新聞傳播的有益補充,而且更是時政報道的主戰場之一。從澎湃新聞客戶端的開通到學習強國APP的普及,均是立足于新媒體時代下時政報道傳播面拓寬的有益嘗試。但是對于傳統時政報道而言,雖然它已具有一定的傳播面,但是卻由于未能充分挖掘新媒體技術潛能而導致傳播面有限。鑒于此,筆者認為新媒體時代下的傳統時政報道的轉型應借鑒和學習深圳廣電集團精心推出的“壹深圳”客戶端,其緊扣“內容站臺,專業撐臺,主動融合”的理念,以多渠道融合的方式,開辟出一條獨具特色的涵蓋內容生產和發布的發展道路。比如,“壹深圳”融合深圳廣電集團旗下的10余個電視頻道和數套廣播頻率的內部內容資源,對接以CUTV等多家地方臺以及百余家品牌微信公眾號等外部平臺,在資源連通的基礎上,提供關乎切身利益的時政信息服務。
此外,傳統媒體的最大優勢在于其擁有專業性、權威性、公信力等特點,而其劣勢則是經營管理思維的僵化,此外互聯網產品運營的亮點又恰是其采用了快速迭代的互聯網思維。鑒于此,以壹深圳為代表的時政報道客戶端,應依托母體固有優勢,以新聞協作生產的,在豐富時政報道的內容同時,提升時政報道客戶端的粘性。換言之,則是時政新聞客戶端在依托母體專業性、權威性、公信力等優勢前提下,采用“UGC+PGC”協作模式,豐富新聞資訊的信源,進而在確保時政信息質量的同時,讓時政新聞不僅成為黨的政策、理論等的宣傳陣地,也從體量、規模、多元化、個性化等層面滿足廣大用戶需求,進而實現增強時政報道服務性的目的。
(三)豐富傳播形態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
時政報道因其傳播內容和方式的單一,而嚴重阻礙了其傳播力的發揮。鑒于此,新媒體時代下的時政報道應充分運用新技術和新載體的優勢,進而在豐富其傳播形式的同時,建構差異化的傳播策略。如壹深圳APP以交通整治、高峰論壇、公益等為主題采取交互直播的形式,進而增強相關主體的互動性。此外,壹深圳APP還直播企業年會、產品發布會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業直播服務,同時還以移動直播、專業直播的形式傳播具有專業價值的時政信息。同時,為了豐富平臺傳播形式,壹深圳APP還將各頻道、頻率的新聞報料集中放置其平臺窗口。又比如,針對政府工作的主要預期目標及過去五年經濟發展概況,新華網曾采用“三維立體書”的傳播形式,推出題為《躍然紙上看報告》的時政短視頻。此外,人民網在2019年兩會期間,借助喜馬拉雅FM、蜻蜓FM等軟件平臺,推出由著名評書表演藝術家劉蘭芳以評書形式主播有關兩會主題的新鮮事,即《劉蘭芳兩會評書》。而且,鳳凰視頻還以“融評”形式推出了一檔時政新聞類的脫口秀,即《又來了》。此欄目通過梳理時政新聞熱點,運用當前較為流行諸如諷刺、吐槽、反問、搞笑、抨擊等手法,借助視頻、圖片等表現形式,在進行麻辣點評的同時,提出新鮮、另類的言論。
以上諸如壹深圳、人民網、新華網等以“時政資訊”為主要內容,充分運用新媒體技術優勢,在挖掘其潛在性能的同時,促使時政報道以多樣化形式傳播,在一定程度上不僅滿足了當前用戶對于短視頻、在線互動等傳播形態的使用需求,而且也在踐行三貼近原則的同時,促使新媒體時代時政報道在報道定位、報道生產及其傳播過程中,實現了差異化傳播,從而有效的破除了時政報道同質化傾向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