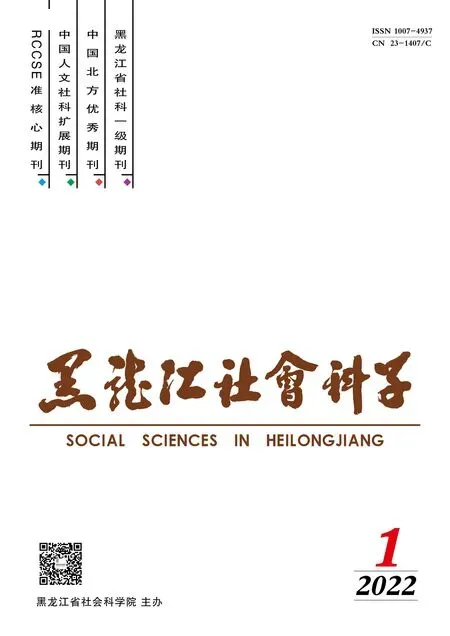“為藝術而藝術”合乎道而失之于義
李 建 棟
(中央財經大學 文化與傳媒學院,北京 100081)
一、問題的提出
“為藝術而藝術”這一主張源自19世紀的歐洲,自產生后經久不衰,至今仍有擁躉。本文討論一個有趣問題,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文化藝術豐富燦爛、源遠流長,為什么中國從沒有產生“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觀念呢?或者嚴謹地說,中國古代類似“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為什么沒有形成氣候?
在歷史上,中國也曾出現“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正如魯迅曾言:“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自覺的時代。”考究魏晉時代的名士風度,魏晉名士確實體現著“人的自覺”與“純文學”理念[1]。魏晉名士從事文藝活動,比如喝酒、彈琴、長嘯、隱居、雅集,都是非營利、非功利、非實用的行為,在這些活動中表現出來的是文人的放誕和率性。放誕是對自由的追求的極致,率性則是不顧世間評判徹底解放心性。具體到藝術作品上,在中國魏晉時代,主要是文章表現出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氣質。
但是,中國古代文學自產生起就自覺擔負著傳承道義的社會教化重任。即使在魏晉時代,文學也沒有離開過實用主義、現實主義或功能主義。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文本同而末異”,言志載道的傳統是“本”。曹丕對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評價與《左傳》所載的“三不朽”觀點一致。陸機的《文賦》最早系統地探討文學創作的問題,他將文學的根本目的歸結到載道教化一途。可以說,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明德、載道與經世致用是作文的首要目的。
除了文學,其他藝術種類例如音樂繪畫等,也皆奉“文以載道”為圭臬。例如,孔子對音樂舞蹈的要求是盡善盡美,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對于不合乎中庸的樂曲,評價為“鄭聲淫”。他把禮和樂放在一起討論,對于不合乎禮的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荀子·樂論》 將樂同個人修養、國家治亂聯系起來,從個人而言是歌以詠志,從治國而言則強調音樂的和同功效。中國繪畫分為工筆畫與寫意畫,但以寫意為主。即不著力于物象表面形態,而強調物象的內在的氣質和精神特征,比如鄭板橋的胸中之竹就講究神似。無論是寫物的借物抒情,寫景的自然和諧,還是寫事的情景相融,里面的情、意仍舊是統御在“道”之下的。
簡言之,中國文化歷史上沒有“為藝術而藝術”這樣明確的主張,也從未有過以“為藝術而藝術”為主導的時代。在魏晉時代,文章曾有過對辭藻、形式的熱烈追求,如曹丕所言“詩賦欲麗”,但隨后就由于過分的華麗和空洞招致批評,引發了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唐代古文運動。古文運動明確提出了指導思想——“文以明道”。(1)確切地講,這些 “文以明道”所明的其實是“義”,而不是“道”。參見萬光軍、丁乃順:《從道德仁義到仁義道德》,《貴州社會科學》2011年第12期。藝術的教化功能、實用功能一直是主流。
二、“為藝術而藝術”背后的康德哲學
“為藝術而藝術”這一口號一般認為是19世紀末由法國浪漫主義詩人戈蒂耶首次提出的[2]。戈蒂耶聲稱藝術本身就是目的,標榜文藝脫離社會,提倡純粹美,追求抽象的藝術效果。
“為藝術而藝術”產生的背景是波西米亞人(Bohemian,又稱吉卜賽人, Gypsy)的生活方式。波西米亞人原意指從波西米亞地區(現捷克地區)被驅逐流放出來聚集在法國巴黎地區的居民,后專指豪放、頹廢、窮困的文化人。這些人與蒸蒸日上的實用的資本主義主流精神無法相融,因此他們需要一個理論來為它們的生活、思想方式正名。“為藝術而藝術”最初正是這樣功用的一個口號與理念。
“為藝術而藝術”的來源是康德的哲學及其延伸出的康德美學。康德哲學以“三個批判”為代表。《純粹理性批判》中批判了純粹的理性。理性主義認為科學是高于一切的存在,想代替宗教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最高裁決。但科學本身是在變化的。今天的科學明日有可能成為謬說,又怎能成為依靠?純粹的理性因此必須輔以經驗(實踐),才能保證正確認識世界。康德指出人們的知識的對象包括“現象”和“物自體”,“現象”可以被認識,而“物自體”是不能被認識的。
《實踐理性批判》指出與其勞神費力地觀察這個世界,不如反轉過來,認真地認識自己。不管認知的結果是宗教還是科學,人本身才是認識世界的源泉,人也是生命追求的最高目標。康德認為人具備先天知識,知性可以為自然立法(類似孟子所謂的“不學而知”“不學而能”)。而獲得這些先天已有的知識的途徑就是追求自由。所以具體到藝術上,藝術的目的不能說是為了其他東西,諸如政治、教化之類,只能是為藝術本身,否則就不自由。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有一句話是康德對實踐的一個說明,也被后人刻在了他的墓碑上:“群星穹蒼在我上,道德法則存我心”。其中“道德法則存我心”表達的就是“自由”,是每個人的追求和精神依靠。因為它只存在于心中,而不能來自外界[3]。
而在《判斷力批判》中,“物自體”不可認識并不意味著我們不能觸及它,只是說明“認識”這種理性的工具有缺陷。觸及“物自體”的辦法就是體驗它,沉浸其中,也就是藝術審美。所謂的“美”就具備“物自體”的性質,只能感知,而不能言說。質言之,“美就是美”。康德認為美在于形式,排斥一切實際利益或目的。例如他說:“那規定鑒賞判斷的快感是沒有任何利害關系的。”[4]
以上,我們看出“為藝術而藝術”這一口號源于康德哲學,從康德哲學可以逐步推演出“為藝術而藝術”。從邏輯上說,首先我們要反對純粹的理性(科學),我們需要經驗來幫助我們認識世界。其次,這些經驗必須遵循自由主義的原則。最后,在所有經驗之中,只有藝術才有可能是自由的,能彌補認識的不足,通過感悟、體驗來與“頭頂之天上繁星”溝通。
1834年,蒂耶在小說《莫班小姐》的序言中寫道: “只有毫無用處的東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東西都是丑的,因為那是某種實際需要的表現,而人的實際需要,正如人的可憐的畸形的天性一樣,是卑污的、可厭的。”這篇序文被認為是“為藝術而藝術”的宣言。可以說“為藝術而藝術”完美地詮釋了康德哲學及美學,正是為了感悟“物自體”而采取的行動。“為藝術而藝術”一詞中第一個“藝術”是說明藝術本身不要追求額外的東西,而應該是追求藝術本身;第二個“藝術”說明藝術才是認識“物自體”的途徑。
康德哲學推出的“為藝術而藝術”有些類似從玄學推出魏晉的名士風度。玄學以《易經》《老子》《莊子》為根本,而以世間的儒家思想為批判對象,所謂“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 玄學興起的主要原因是連年的戰爭、瘟疫及政治變幻使人感到世事無常,世間萬般名利轉瞬即逝。魏晉名士之行為可以說是逃避現實的,但是換個角度看,有逃避的對象,自然就有追求的對象;魏晉名士的種種放浪形骸、縱酒疏狂的行為未嘗不是對“道”的主動追求,即以有限去把握無限,以眼前體驗永恒[5]。魏晉風度是玄學的外在表現形式,而玄學是魏晉風度的理論依據。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明確“道”的存在并了解“道”的真相的方法,只有悟道一途。悟道的方法,其一是出世,即徹底放下世間之事,其二就是塵世間的領會、體悟。這種體悟表現在自我意識的覺醒,開始關注個體生命自身的價值。康德哲學與老子的道是近似的。老子的“道”,被康德表達為“物自體”。在方法上,康德哲學也強調“對世界的認識要回到對自身的認識上來”。
綜上所述,康德通過對理性的批判、對實踐的批判、對判斷力的批判,最終得到了一個 “物自體”概念。“物自體”是不可以通過知識來得到認知的。由康德哲學可以推出“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美學概念。老子提出了“道”的思想,道也是不可通過“名、言”來表達的。由道家思想可以推出魏晉風度。這樣的類比為我們下面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角度,即以中國哲學的語言模式來分析“為藝術而藝術”。
三、中國的道德仁義
中國文化在“道”之后,又衍生出德、仁、義等概念。例如《道德經》講“大道廢,有仁義”,“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并不是每個人都有資質能夠理解“道”,相應的,也不是每人都有追求“道”的興趣。所以,德、仁、義就是在失道之后中國人追求“道”的道路。道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是自然(包括人類)運行的根本法則。其本義表示人所行之道,引申為整個宇宙所行之道。沒有與“道”相對的概念,因為“道”這里只有一,沒有二。但在人主觀意識產生之后,有了“我”的概念。也就產生了主體與客體的區別,偏離了道。
德者,得也。就是人有了“我” 和 “我所”。主體與客體發生了關系,產生“我得到”的概念。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道”。“道”本來就遍一切處,不存在得不得的問題。有“得”的概念反映的是有“我”的概念。因此“德”比“道”低一個層次,描述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 “德”字的甲骨文與金文的“道”字相似,表示所行的道路。但在道路中間不是一個人的符號,而是加了眼睛和心,表示主體的產生,表示得到了東西,也表示遵循正道。何謂正道呢?其實就是“無得”。例如,《道德經》中講“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仁者,二人也。由于人脫離了自然之本體,就開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伴隨著“我”的概念,有了“他人”的概念。人與人之間怎樣相處,才能回到“道”的層次呢?答案是仁。什么是仁?依據“德”的概念,遇到世間利益相爭的時候,仁者是要把它讓給他人,以求得“無得”。于是仁才有了“愛人”的意思。仁的例子就是母親總是想把好的東西留給子女,而不顧自己利害得失[6]。“仁”與“慈”多聯用,其他的“仁德”“仁政”“仁人”等皆從此義出。
子貢問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答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也就是說,“仁”的意義是先幫助別人,然后成就自己,是一種利他行為。但“仁”還有“己欲立”“己欲達”這樣的概念,因此比“德”又低一個層次。反過來講,遇到災害時,仁就是不讓對方承受傷害。例如,仲弓問仁,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義者,集體也。仁是處理人與人個體之間的關系。但有了國家、集體這樣的團體之后,仁就進化成了義。義所規范的是人與集體的關系,講的是如何以集體的角度來規范人的行為,以便符合“道”。如果人們能做到仁,義也不用講了。因為義本身代表的就是其他人的集合。正因為人們不能仁,變成了“經濟人”,熙熙攘攘皆為利往,所以又規定了義。義因此比仁又低了一個層次。義的本義表示用刀截割羊,表示祭祀時的場面,也表示大家一起分食。義是氏族部落聚集成一個團體的特征,沿襲仁的概念,義要求的是個人利益服從集體的利益。可以說“義”就是集體主義精神。
孟子說:“義,人之正路也。”這是孟子對人提出的要求。中國有句古話“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義”就是把個人利益放在了集體利益前面,把小集體利益放在了大集體利益前面。在政治相對穩定的時代,服從國王、君主也就是義。《易經》中講“禁民為非曰義”,董仲舒說“立義以定尊卑之序”,后來推而廣之,報答知遇之恩、忠于主人、忠于自己的理想等也歸為義。簡言之,“義”規范的是個人與集體,及大小不同集體之間的關系。
義再下之,就是禮。義分為大義、小義,大義就是更大的集體、更長期的利益。由于大義、小義的紛亂,就開始以禮進行約束。禮也是祭祀的意思。這是“禮”“義”相通的地方。所以孔子說“義以為質,禮以行之”,《禮記》講“禮義以為紀”。與禮相反,義是沒有外在約束的,是自己的內心要求。“禮”談的是有強制性的東西,換成現代語言,就是法律規章等保障秩序的東西。
仁義的等級低于道德,已經明確地有“我”的成分,但還有“無我”的趨向。這一“無我”趨向其實也就是“仁義”回歸“道”的憑借。比如《禮記》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然而到了“禮”這一層次,已經沒有“無我”的特征,形成了私有制社會。禮規定好每個人的利益,不斷強化了“我”的概念。“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所以僅僅遵循“禮”并不能“得道”。
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的關鍵是“克己”,而不是“復禮”。從周禮到現在的法律制度,“禮”隨著時間不斷改變。因此仁是孔子儒學的核心,周禮只是那個時代“仁”的表現。由此可知,禮也不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它只是“道德仁義”在不同環境下的表現形式。道德仁義才是中華文化的內核。
綜上所述,道德以下,“仁義禮智信”被當作五常。“仁”規范人與人之間的行為,“義”規范人與集體之間及不同集體間的行為,而“禮”只是義的外在表現形式。道德的追求是少數人的,而五常則是適合大眾的。自古以來,仁義之道,是中國倫理的核心,是立身處世、治國理政的要義,義利之辯是我們文化最基本的一部分。因為有“義”,中華文明才得以延續。中國社會是尊崇集體主義的社會。藝術創作,作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也服從道德仁義的規范。即藝術工作者要把工作做好,服務于人民,即可由仁義至道德。追尋“道德”并不必然要求脫離現實生活,這樣的邏輯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并無“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口號的產生。
四、西方文化中的道義
基督教國家沒有“道”的概念,但有“上帝”的概念,只是上帝是以人格化的形象出現的。文藝復興時期的笛卡爾就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概念,這近似于中國文化中的“德”的層次,指的是主客體的分離(人與自然的分離)。在笛卡爾之后,康德明白了“物自體”的道理,相當于中國文化中的“道”的層次。康德把“物自體”仍舊等同于上帝,所謂“神以載道”。所以西方文化中“道”“德”在時間順序上是錯位的,是以“德”產生“道”,而不似中國由“道”衍生“德”。
西方文化中亦有“義”。英語中righteousness 或 justice 即指合乎正義或公義的。然而其正義的根源卻是《圣經》。一方面,只有上帝和上帝之子耶穌才有義,其他的都稱不上義;另一方面,個人只有依附于上帝才有義,這里沒有個人任何發揮的空間。中國的義是指個人放棄個人利益,而服從集體、奉獻集體。然而,在《圣經》中,不信上帝的異教徒無論行為如何高尚,都稱不上義人。
這種人對上帝的依附就是所謂“因信稱義”。“因信稱義”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指的是信仰是得到救贖的必要條件。根據《圣經》,人們犯有原罪,所以無論如何做,都是“不義”。只有得到上帝的恩赦才成為“義”。狹義指的是基督教新教尤其是路德派關于如何得救的方法。《圣經·羅馬書》中說“心里相信就可以稱義”。
無論廣義還是狹義,西方的“義”都是個人與上帝(或上帝之子)的關系,是一種“個人主義”。也就是說,西方至今沒有發展出人與人之間的“仁”的關系,他人即地獄。 雖然《圣經·馬太福音》中提倡“你們愿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類似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謂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倫理,然而人們并不會因為奉行這樣的準則而獲得救贖。獲得救贖的唯一原因仍舊是奉侍上帝、相信上帝。這樣的“仁、義次序錯亂”導出了“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這樣的認知。以中華文化的角度看,西方由于依從于上帝,根本沒有人與人之間的“仁”,也沒有人與集體之間的“義”。所以西方人在現實生活中表現出來的是個人主義、重利輕義甚或見利忘義。
總之,雖然康德提出“物自體”后,“物自體”可以與老子的“道”相提并論。然而,西方卻沒有像中國那樣以“道”做為出發點發展出“德、仁、義”的概念。西方亦有“義”的概念,卻不是規定個人與集體的“義”,而是個人與上帝之間的關系。在這樣的道義概念之下,現實生活和“物自體”產生了對抗。藝術工作者如果推崇求道,只能提出“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口號。
五、結論
通過溯源“為藝術而藝術”,可以發現“為藝術而藝術”正是康德哲學美學的體現。康德“物自體”類似老子“道”,相應的,“為藝術而藝術”是“求道”的吶喊,是個人試圖追尋洞徹世界真理的行動。 借此本文從“道德仁義”的角度回答了兩個問題:其一,為什么西方會產生“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其二,為什么中國歷史上沒有提出“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口號?
西方之所以會產生“為藝術而藝術”“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純藝術”這樣的口號,并不時得到回應的原因,是由于西方始終沒有形成中國文化意義層面的“道德仁義”。當康德哲學提出“物自體”之后,如果以探尋“物自體”為目標,就必須批判現實社會、脫離現實。因為看到的世間都是骯臟的,只有純藝術才是凈土。“為藝術而藝術”是西方“求道”的直接體現。世俗文化中沒有“道”的容身之處,西方文化下的世間有用的東西都浸淫著個人主義、自私自利,遠遠背離了道德規范。“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依靠人之道,滿足一己之需去追求“物自體”,自是緣木求魚,不可能悟道、得道。 所以那些一心求道的人只能徹底否定社會的“實際需要”,從而提出了“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口號。藝術與生活在西方文化中是對立的,這是西方文化中二元思想的結果。
為什么中國歷史上沒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因為中國文化強調二元統一,追求和諧。中國文化很早就提出了“道”的概念,“道”又進化出“德、仁、義”等規范。中國整個文化系統都是以 “道德仁義”為主干的。“道、德、仁、義”之間雖有層次差別,但它們是相通的。通過求仁取義,中國人可以回到道、德,因此求道毋須與世間決裂。踐行“仁義”并不妨礙從事藝術工作的人返回到“道德”高度上。同樣,努力追求藝術之美,也不會影響妨礙世間之仁義之施。生活與藝術是對立且統一的。
從現實意義上講,“為藝術而藝術”是追尋“物自體”的一種途徑,其本質還是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當前正是中國文化復興之際,我們應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鼓勵藝術從業者“要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樹立高遠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國情懷,努力做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有貢獻的藝術家和學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