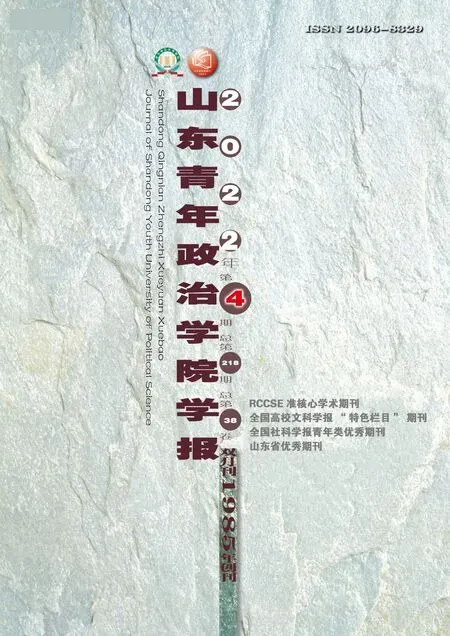因聲致誠:董仲舒“深察名號”新論
張曉周
(山東大學 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濟南 250100)
董仲舒在漢武帝時期,因建構了包含信仰、政治哲學、倫理等在內的經學體系,其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被漢廷采納等貢獻,而被史書尊為“群儒首”“儒者宗”。董仲舒實為春秋公羊學家,作為通經致用的經學家,他借助經學的詮釋與體系建立了儒學的系統。董仲舒在建構其理論時,使用了“深察名號”的“正名”方法,深入考察、探究名號的內涵與意義。他說“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1]董仲舒是從治理天下的角度來論述“深察名號”的:他認為治理天下的第一步就要審視、辨析事物的大綱,而辨析事物的大綱就在于“深察名號”。因為名號,是事物、大道理的總綱。董仲舒給出了“天子”“士”“民”“祭”“王”“君”“性”等名號的系統說法。需要追問的是,董仲舒為何提出“深察名號”?該方法在其經學、儒學體系中發揮了何種作用?這不僅是董仲舒的問題意識,亦是本文的問題所在。
一、因聲求義:“深察名號”信仰與理性的雙重維度
“深察名號”常被視作董仲舒對孔子“正名”思想的發展,并且被他運用在政治哲學、人性論等領域。侯外廬[2]、馮友蘭[3]等人雖持有唯心唯物二分的意識形態視角,但已經從邏輯、概念、分類的角度對董仲舒的“正名”思想進行研究。徐復觀從訓詁的角度認為該正名內容“有的可以成立……更多的是牽強附會”[4],不過他強調董仲舒的正名思想是納入到其天的哲學系統里去的。李澤厚盡管沒有具體研究“深察名號”,但其運用“理性與非理性”[5]的視角重新評價與褒獎董仲舒思想。該視角同樣適用于對“深察名號”的考察:“非理性”部分指向董仲舒的神秘主義,反映了董仲舒的信仰維度,而“理性”主要指“實用理性”。張祥龍主張“深察名號”是董仲舒的語言哲學,前者借用印度教的《奧義書》誦“名號”以通達“梵”“大我”的方法來佐證“深察名號”的哲學意涵,并引用萊布尼茨對漢字的理解,得出結論“董仲舒意義上的‘名號’,其真正‘大端’——其本原——就在陰陽五行的卦象名號和思想名號里頭”[6]。這種考察與結論同樣極富啟發性。
董仲舒在“深察名號”中大量運用聲訓方法。聲訓作為訓詁學的根本要義,到了清代段玉裁、王念孫等乾嘉學派訓詁專家又被重新地理解與說明。訓詁方法分為聲訓、形訓與義訓。根據王力的研究,從許慎時代到段玉裁、王念孫的時代,“重形不重音的觀點,控制著一千七百年的中國文字學”[7]。即從漢到清的一千七百年間,聲訓并沒有被重視。這種局面直到乾嘉學派時期才得到扭轉。段玉裁言:“治經莫重于得義,得義莫切于得音。”[8]對于經學的研究,最重要的莫過于求得其義理,而要獲得義理最關鍵迫切的就是要掌握住文字的發音。王念孫又云:“竊以訓詁之旨,本于聲音……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9]文字不僅有發音,還有字形。王念孫直接認為訓詁的根本宗旨起源于聲音,并主張通過古音來求得文字的含義:以聲音為線索,引而伸之,觸類旁通,不限制于或者要超越文字的字形。正如王引之所說:“訓詁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10]聲音便是指有聲語言,而文字則指字形。乾嘉學派的一個突出貢獻在于,區分了語言與文字,并認為“文字不是直接代表概念的,而是通過有聲語言來代表概念;有聲語言是文字的物質基礎”[11]。乾嘉學派主張必須通過“有聲語言”來喚起文字之義。“有聲語言”是文字的根本,而文字乃是“有聲語言”的標記符號,發聲相同或相近的字之義可以相通,這就是“因聲求義”的要旨。“深察名號”當中便有許多這樣“活生生”的例子,如“士者,事也”“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12]等。從“因聲求義”的角度來看,“事”與“士”音同,故義可相通;“王”與“皇、方、匡、黃、往”的發音相近或相同,后面五個字就可用于訓釋“王”。皇有大、盛大,古代“三皇”應當就已經蘊含著“王”的意思。“方”指王道的“正直而方”,可以升華為大中至正的境界。“匡”有“正”之意,依照董仲舒的觀點,王正而天下正,以王之正而正諸侯大夫、天下之治。黃作為一種顏色,得到古代經典的大力推崇,如《周易》就明確主張由“黃中通理”而上升到至美的境地。在中國傳統中,黃色是皇家貴族專用之色,皇帝的龍袍就是黃色。“往”指“王”能夠往來四方,而王道的實行亦能夠吸引四方民眾前往。董仲舒對“王”的五種解讀,使我們能夠更加全面立體地理解“王”了。
通過“因聲求義”的訓釋方法,我們就可以更好地考察“深察名號”之深意,即“名號”的根本到底是什么。董仲舒強調探求事物之根本,如在《奉本》篇說“禮者,繼天地,體陰陽”[13],視天地陰陽為禮之本。這種重視事物根本的思路貫徹于董仲舒的整個思想體系當中,“深察名號”也不例外。“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施命謂之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14]“謞”與“效”的發音相同,指大聲呼喊、吼叫。古時候的圣人,大聲呼喊而效法天地就叫作“號”,鳴叫而給萬物命名叫作“名”。名號的發聲雖然不同,但它們的根本都指向天意,所以圣人通過鳴號而通達、領會天意。名號——有聲語言——天意,構成了溯源求本的鏈條,而有聲語言成為接通名號與天意的橋梁。有聲語言是名號的根本,而天意又是有聲語言的根本。通過“謞”“鳴”出名號的聲音,就可以通達名號之義,該義再升華一步就是天意。董仲舒把名號之義溯源于天意透顯出了其對“天”的信仰。在董仲舒的體系中,“天”是“人心信仰的源出”[15]。信仰是一種情感、信念,信仰與理性不同,它屬于人類的非理性部分。信仰往往難以明晰地表達與論證。理性對應著知識,而信仰與知識是不同的地盤。正如康德所言:“我不得不懸置知識,以便給信仰騰出位置。”[16]康德明確了如何處理理性與信仰的關系:懸置、限制理性與知識,以避免它們對信仰的干擾。不能用理性檢驗乃至批判信仰,也不能用信仰檢驗乃至批判理性。兩者互補而共同組成人類的構成要素。信仰在董仲舒體系中表現為天意、感應、祭祀等范疇或活動。
“深察名號”中除了有信仰維度的意涵,還有對“名號”理性詮釋的部分。先來看對“士”的訓釋:“士者,事也”。在《尚書·康誥》中“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此指周公謀劃營建東都洛邑之時,侯、甸、男、采、衛邦國的諸侯、百官和臣民等都來朝見周公,服事于周王室,這里的“士”即為“服事”,譯注者明確地認為“士,與事通用”。[17]由此可見,“士者,事也”訓釋具有經典依據。
再來看對“王”的訓釋,它同樣能夠找到古代文本的支撐。在《詩經·周頌·桓》“于昭于天,皇以間之”,其意為:周武王的功德大業輝煌光耀于天,他代替殷紂成為新王。此處的“皇”指周武王,便釋作“君王”或“王”之意。質言之,“王”與“皇”可以互訓。《詩經·豳風·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此處“皇,通‘匡’,即匡正,治理”。[18]因此,“皇”與“匡”可以互訓;又因為“皇”與“王”可以相通,所以“王”與“匡”亦可相通。《詩經·小雅·楚茨》:“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皇”被釋為“往”。[19]如上一般,“王”亦可訓為“往”。而對于“王者,黃也”,張世亮等人認為,黃色在五行之中為土之顏色,土居中央方位,象征君王地位;根據五行生克關系,漢克秦,秦屬水,則漢為土德:由此可知,黃為貴色。[20]此種觀點符合董仲舒陰陽五行理論,當為正論。蘇輿認為這與《周易·文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有關[21],而比照董仲舒對“黃”的詮釋“德不能匡運周遍,則美不能黃”[22]來看,蘇輿所論言之有理。而對于“王者,方也”,董仲舒解為“道不能正直而方”[23],本文推測此亦是從《周易·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來。通過以上的考察,董仲舒對于“士”“王”的詮釋都有其經學來源、經典依據。
董仲舒對“士”“王”等名號的詮釋,已不再是信仰的部分了,而是一種理性化的表現。“名號”反映了事物的真實情況,“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圣人所以真物也。名之為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則黮黮者還昭昭耳。”[24]“真”指事物的真實樣貌或意義。“名號”即產生于并用來言說事物之“真”。如果不“真”的話,那就不能用“名號”來命名。所以凡是幽暗模糊的事物,只要還原到它的“真”,那么幽暗模糊的也會變得清晰明白起來。“名號”反映事物之“真”就是其理性的部分,它經得起分析與論辯,盡管這種理性往往被稱作實用理性。
實用理性還表現在對于“字”的訓詁與“正名”的關系處理上。鄭玄在對《論語·子路篇》的注釋中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為之字。”[25]按鄭玄說法,“正名”也就是“正字”。江沅接續鄭玄的思路主張:“孔子曰‘必也正名’,蓋必形、聲、義三者正,而后可言可行也。亦必本義明,而后形、聲、義三者可正也。”[26]“正名”就是正“字”的“形、聲、義”,而且必須明確字的本義,而后才能正字的“形、聲、義”。董仲舒在“深察名號”中,主要從“聲”的方面對“名號”之本義進行追溯與正定,與鄭玄、江沅的思路非常相似。因此,董仲舒通過“因聲求義”的方法,從“正字”轉而達成“正名”,是經得起理性論辯的。
二、至誠之道:理順天人關系,確立禮樂秩序
董仲舒“深察名號”的方法旨在理順天人關系,確立禮樂秩序,其論述皆不離開“天人之際”框架以及禮樂制度的設計。如他對“天子”“士”“民”“祭”“獵禽獸”等名號的考察,無不是想在天人關系與禮樂秩序中給予它們以恰當的意涵與規定。即便是對“性”的探討,也是這樣:“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于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與天道一也。”[27]他對“性”“心”“身”的正名亦是放在了天人關系之中,并最終落實為禮樂教化對人性的改善。他在《深察名號》中對天人關系直接表述為:“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28]在董仲舒看來,各種事物的名號是圣人按照天意而取的。表面上看,在事與天之間是由名號而貫通的,但是名號經由圣人而取,因此,事與天之間本質上是由圣人來溝通、接通、貫通的。由事到名、由名到圣人、由圣人到天,依次貫通,從而形成圣人所取名號來自天意,而天意又是通過圣人而彰顯,使得天與人合二為一。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的重要命題,這在董仲舒的經學天人之學中得到了大量論證與發展。通過新舊“天人合一”的發展脈絡來呈現董仲舒所處的歷史語境,可以更加明晰他的運思理路。
新舊“天人合一”的提法出自余英時的《論天人之際》一書。余英時認為“軸心突破”時期的諸子學派思想家、哲學家通過建構了一個以“道”為核心的新“天”,取代了傳統禮樂傳統中巫文化主導的舊“天”;前者被稱作以“內向超越”為特色的“新天人合一”模式,而后者則名為“舊天人合一”模式。余英時強調,“軸心突破”之后,新舊“天人合一”的兩種模式處于并存、交互狀態,如漢武帝的“巫蠱事件”。①余英時的觀察對于審視董仲舒的“深察名號”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視角:董仲舒去世十多年后,發生了“巫蠱事件”,那么董仲舒處在新舊“天人合一”并存的時代,其思想方法與思維模式具有新舊的雙重烙印與維度。
在禮樂傳統中,“舊天人合一”是通過巫覡和巫術完成的。巫覡是唯一能夠溝通天與神的特殊群體,他們成為帝王最信賴的助手,而帝王實際上便是“巫覡之首”[29]或者就是巫覡本身。巫覡成為“天人”之間的通道,天與人之間的“合一”也就集中在了巫覡身上。巫覡通過一整套祭祀儀式溝通天人,“舊天人合一”也就體現在該儀式上。這就是董仲舒為何在討論“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蒸”[30]之后,提出了上面提到的“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結論。祭祀是禮樂傳統中的核心要素,既然“舊天人合一”是通過祭祀完成的,那么這些祭祀“名號”的本義就指向祭祀本身,而祭祀則進一步體現、導向“天人合一”的關系,這是其一。其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對祭祀活動有大量詳細的描述,比如“求雨”“止雨”等儀式。顯然,他對于這些祭祀儀式都是了然于胸的。儀式包含巫師的歌舞,這種歌常以“號”的形式被巫覡表現出來。根據陳夢家的考證,“巫之所事乃舞號以降神求雨……名其求雨以祭祀行為曰雩”[31]。巫覡在名為“雩”的求雨儀式中,是通過歌舞、鳴號來達到降神求雨的目的的。巫師之“號”或許是董仲舒“謞而效天地謂之號”的重要來源,只不過董仲舒之“號”的發出者已不是巫覡,而是圣人。即使“深察名號”的“號”外在形式類似于或者根本就是巫覡之“號”,但其發動者已然是圣人了。圣人與巫覡的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巫覡在“舊天人合一”傳統中具有核心地位,而圣人通過哲學體悟或修行方法在“新天人合一”中取代了、至少極大地削弱了巫覡的地位。由此可見,必須從這“天人合一”新舊模式兩個角度來考察董仲舒的“深察名號”,才能得其要旨。
余英時強調“軸心突破”之所以形成了“新天人合一”的歷史范式,在于以孔孟、老莊為代表的諸子百家通過哲學思辨或個人修養的方法達成了“內在超越”,這與巫師的外向祈求迥異。比如“孟子強調‘萬物皆備于我’,是為了實現‘誠’‘恕’‘仁’,即儒家的中心價值。”②而董仲舒有著同樣的轉向與關注,比如《祭義篇》中強調“君子之祭也,躬親之,致其中心之誠”[32]。通過祭祀來激發君子心中之“誠”,甚至可以說以“誠”來解釋祭祀禮樂傳統,這已經蘊含“內在超越”的轉向了。董仲舒對“誠”“仁”“義”等儒家價值的追求,不僅表現在祭祀的層面,而且還有精神修養、思辨論證的向度。在《天道施篇》中,董仲舒云“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而不與俗推,眾強弗能入。蜩蛻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圣人之心也。”[33]他把“至誠”視為圣人內在修行的心靈境界,以此來拒絕外在濁穢、世俗事物的侵襲與干擾。
祥瑞作為董仲舒“天人感應”的重要環節,其運作也需要“誠”。在其第一次給漢武帝的對策中,董仲舒強調“天人感應”的核心是“誠”:“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34]三代受命,天降祥瑞,而君王之“誠”是天瑞出現的核心要素。天人之間的溝通,已然不是借助巫覡,而是通過人心之“誠”。“誠”的效用不僅如此,其對于治國理政的重要性亦是不可或缺。當漢武帝在第二次策問時,詢問為何他付出了諸如親自耕種,勸勉孝悌等一系列努力,但治理成效甚微,未讓老百姓獲得益處。董仲舒在對策中直言其中緣由:“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愿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35]董仲舒批評漢武帝的誠心不足,導致老百姓沒有得到實惠,武帝亦無政治之功績,因此建議漢武帝要“設誠”于心中,再去治國理政,如此才能向三王看齊。董仲舒把“誠”作為一種精神修養的追求目標,不僅圣人有“至誠”之心,君王也要“設誠”于心。
如果說孟子對“誠”的追求,還未把“誠”在天人關系、天人感應中的重要地位凸顯出來,那么《文子》中的論述則可以幫助我們來考察該問題:“圣人象之……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于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36]。《文子》的這段引文尤其重要,因為從這句話的角度來審視董仲舒的“名號”與“天人感應”思想的話,會完全排出掉巫覡、巫術的因素。這段論述足見其以“精誠”來溝通“天人”,形成了其“新天人合一”模式。董仲舒主張“天瑞應誠而至”,而他對“誠”的功能與重要性的認識和文子如出一轍。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董仲舒在《王道篇》的論述:“《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并見。”[37]此處的“景星見,黃龍下”與《文子》的引文完全一致,足見董仲舒與《文子》思想的借鑒關系。董仲舒主張只有“王正”了,才能出現“景星見,黃龍下”這般的吉祥局面。王如何“正”呢?就是要君王“設誠”于心。這就是董仲舒“深察名號”的任務之一,就是對“王”的正名。而且《文子》關于語言、聲音的觀點——“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亦與董仲舒“名號異聲而同本,鳴號而達天意者也”相互發明。那么是否就能得出結論——董仲舒的“誠”與“災祥”的思想就是來源于《文子》,這值得進一步研究,畢竟孔子、孟子、《中庸》等都對“誠”有大量論述。但至少可以看出,在董仲舒之前的時代,儒道兩家均非常重視“誠”。
“深察名號”也反映了禮樂傳統中“聲音”對董仲舒的深刻影響。比如在禮樂文明發達的商朝非常重視聲音,有“殷人尚聲”的說法:“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后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禮記·郊特牲》)《史記·樂書》對“音”與天地之間的關系表達得更為明晰:“凡音由于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38]前者只是表達了聲音與天地之間的模糊關系,而后者則把聲音當作天與人相接通的媒介。此兩處雖還不像董仲舒所言“鳴號而達天意”,但聲音與天地之間的關系在禮樂傳統中有其重要的地位則是毫無疑問的。當然,如果非要追溯其思想根源,則要尋到《周易》:如《中孚》九二爻“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中孚·彖》“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文言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孚”乃信之意,信又為誠,故在《周易》中已經大量出現“天人感應”“同聲相應”的思想,其內在邏輯也蘊含著“誠”的要素。這或許就是董仲舒“同而通理,動而相益”[39]的思想來源。
三、感通與立象盡意:“深察名號”的運思方式
據王力的研究,聲訓在漢代之前,就已經被廣泛使用,如《周易·說卦傳》:“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離,麗也。兌,說也。”[40]乾、坤、坎、離與兌為卦名或卦象,它們象征的物象依次為天、地、水、火與澤。即天有健之義,地有順之義,水有陷之義,火有麗之義,澤有說之義。《周易》與其他文本的一個重大不同就是通過“立象盡意”,即立卦象、物象來闡述圣人之意。《周易·系辭傳》云:“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普通的書籍并不能窮盡所欲表達之言,而言又不能窮盡所要表達之意,因為該種文本只有文字、字形。《周易》與此不同,圣人是通過卦象、物象來窮盡其意的,與卦爻象對應并蘊含著物象的卦爻辭亦能夠窮盡所要論述之言。卦爻象與純粹的文字不同,它打破了文字表意的局限,能夠符示、象征多種意涵。如,乾卦既能符示健,又能象征馬、首、天、圜、君、父、玉、金、寒、冰等物象。(《說卦傳》)這是《周易》之象的強大表意功能,也彰顯了《周易》的思維方式。
王樹人為了給中國傳統思維“正名”并與西方“概念思維”相區別而提出“象思維”。他認為,“象思維”奠基于《周易》,主要集中表現在“觀物取象”和“立象盡意”:“‘觀物取象’的思維與西方概念思維根本不同之點在于,‘象’不是不動的實體,不是用定義可以規定的概念,相反,‘象’是‘非實體’的、‘非概念’的,也就是具有非對象性和非現成性的特點,因此‘象’是借助概念用理性和邏輯所無法把握的。”[41]“象思維”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于“象的流動與轉化”,這種“流動與轉化”表現在不同象之間的“異相擬,類相合,似相通”。比如《周易·乾·大象傳》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行健”與“君子自強”,既是“相異之象”,又是“相類之象”,也是“相似之象”。[42]《周易》把這種“觀物取象”的方式與“名”聯系起來:“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系辭下傳》)卦爻象之名雖然微小,但所引申喻指的物象卻廣大,而這其實就是“象的流動與轉化”。這是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維模式,這也正是董仲舒思維特色。董仲舒在《天道施篇》云:“萬物載名而生,圣人因其象而命之。”[43]萬物生來就承載著名號,圣人通過觀其象,而命其名。他在《陰陽義篇》又說:“以類合之,天人一也。”[44]從“取象”分類的角度來看,天與人是合一的。董仲舒認同圣人“觀物取象”的方法,由此而為萬物進行命名。對于“天”與“人”,又從“象的轉化與流動”的角度,推斷兩者合一的關系。由此可知,董仲舒運用了《周易》象、類、名的“象思維”方法。
在王樹人看來,聲象為感知之象的種類之一。董仲舒在詮釋“王”之內涵時,“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就是依據“聲象”的“流動與轉化”,在感知、聞見的領域呈現“王”的意涵。“聲象”繼續“流動與轉化”,繼而外在的感知之象被消解,而轉化為整體的意象或氣象。[45]董仲舒所謂的“名號異聲而同本,鳴號而達天意者也”,此一過程便經歷了這一轉化與升華:圣人由“名號”之“聲象”升華到蘊含“天意”的氣象或意象,如此就完成了“立聲象以盡意”的“象思維”過程③。
“深察名號”與《周易》“象思維”關系緊密的一個有力的佐證是上文引述張祥龍的說法:“董仲舒意義上的‘名號’,其真正‘大端’——其本原——就在陰陽五行的卦象名號和思想名號里頭。”張祥龍是根據萊布尼茨對漢字的認識,從而得出的這個結論,與此處借助“象思維”的思路,可謂“殊途同歸”。
“象思維”是以《周易》為代表的中國哲學感通精神的呈現。“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系辭傳》)無思無為是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人的思慮、行為對領會、體悟世界的影響。蔡祥元根據現象學的視角,認為《周易》的感通是圣人克服了人的主觀任意性,而把握道之象;感通是“介于感性與理性之間的認知方式”。[46]圣人通過感通,能夠從道的視角來觀照萬事萬象,并在感通的基礎上進行詮釋。如果前者處在非理性的、信仰的階段,而后者則是理性的闡釋。這同樣適用于董仲舒的“深察名號”。董仲舒所論述的天人關系,天人感應以及把名號之義追溯到“天意”,都是其對天的信仰的表現。他從聲訓、立聲象以盡意的角度去探究名號的“語源學”之“真”,則顯示出理性探求的向度。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確切的結論:董仲舒的“深察名號”具有堅實的聲訓依據,體現了董仲舒的信仰與理性雙重維度。他的目的在于理順天人關系,確立禮樂秩序,為新帝國的政治實踐提供理論指導。董仲舒具有中國哲學感通精神氣質,其發展運用了《周易》“象思維”、立象盡意的闡釋方法。至于說“深察名號”到底有何學術意義,我想它應當提醒我們重新認識漢字、漢語及其訓釋方法,有聲語言比文字、字形更為根本與重要。在這個意義上,漢字、漢語與西方所謂的“語音中心主義”字母文字、語言的對話與比較,或許能夠開啟更豐富的討論空間。④
注釋:
①②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M].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62,148+187.本文從該角度探討“深察名號”問題,受到薛學財《名號的神圣性及其在天人之間的中介作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第三十五>箋釋》一文的啟發,但本文與其論述的落腳點差異頗大。
③此一過程被《莊子》更明確地表達出來了:“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人間世》)從這個上升通道考察的話,起初為“名號”之“聲象”,聲象首先被耳朵聽到,而再轉化為心之意象,最終升華為氣象。
④關于該比較議題,已超出本文的范圍。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顧明棟.漢字的性質新論[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04):33-41;尚杰.一種新文字的可能性——關于漢字哲學的一個文學維度[J].世界哲學,2018(01):104-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