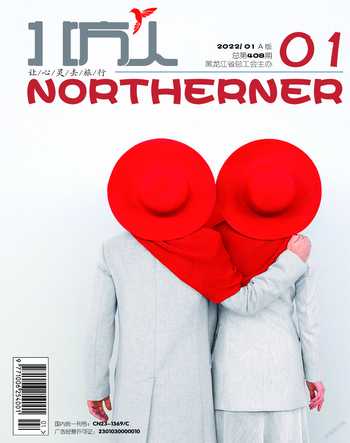三毛:吃苦,其實(shí)都是很好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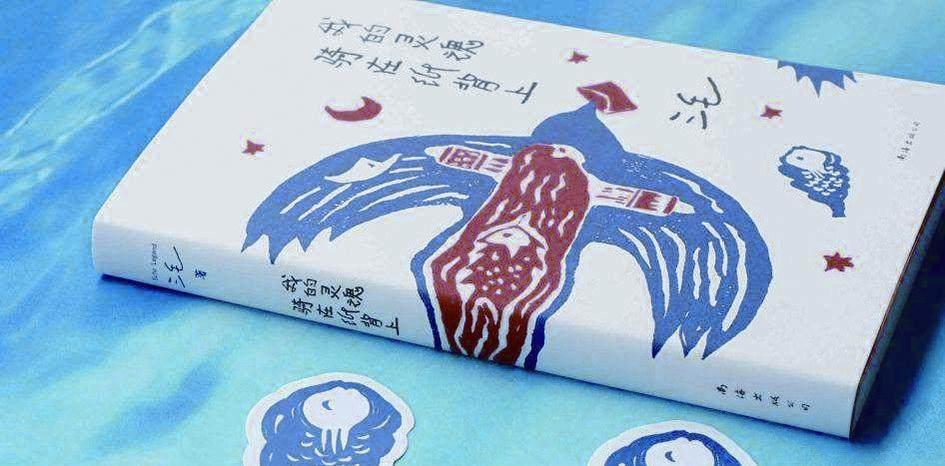
“爹爹,姆媽,我是中國(guó)歷史上有記錄以來(lái),第一個(gè)女性踏上撒哈拉沙漠的土地,很有意思。”
“這才是人生,如果說(shuō)來(lái)世界上走一遭,只這幾個(gè)月的生活,已值回票價(jià)。”
1974年4月18日,三毛在家書(shū)中講述初到撒哈拉的心情。
這是一段佳話的序章,也是她的文字風(fēng)靡華語(yǔ)世界的開(kāi)始。
這段文字,收錄在三毛的新書(shū)《我的靈魂騎在紙背上》里。書(shū)中跨越4大洲23年光陰,收錄了三毛83封私人書(shū)信(含首度出版的48封),包含23張珍貴照片、手跡。
它們是三毛寫(xiě)給家人的最真實(shí)的生活與情感記錄;是三毛寫(xiě)給友人的心靈與心靈的碰撞與共鳴;它們也是三毛留給我們最溫暖的陪伴。
俗話說(shuō)“見(jiàn)字如面”,在《我的靈魂騎在紙背上》中,三毛仿佛破空而來(lái),又從空中落到地上,向我們呈現(xiàn)出一個(gè)更真實(shí)、更鮮活可愛(ài)的“小姐姐”。
吃苦,其實(shí)都是很好玩的
在撒哈拉沙漠,三毛面臨的是物質(zhì)、精神上的雙重困境:結(jié)婚一年,連一把椅子都沒(méi)有;洗衣、洗澡全是臭水,吃睡都在地上;孤獨(dú),時(shí)常一天沒(méi)人說(shuō)一句話;病痛,吃藥全吐,要喝一點(diǎn)兒熱水都沒(méi)有人煮。
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粗糲,三毛沒(méi)有故作堅(jiān)強(qiáng),但叫苦與吐槽中,都透出健康的底色。
她筆下有沖勁兒和活潑潑的生命力:“怎么有女人不會(huì)吃苦,其實(shí)都是很好玩的。”
有腳踏實(shí)地的生活:細(xì)致計(jì)算家用,讓姐姐“替我禱告給我中獎(jiǎng)券”;
有幽默感:“屋頂又飛走了”“我那么丑,卻無(wú)往不利”;
有面對(duì)惡意的坦然:因?yàn)榕c荷西在一起,船員罵她婊子,她不以為意。
她的一生,遠(yuǎn)不只是“文藝?yán)寺彼芨爬āO喾矗畹谜鎸?shí)、坦蕩——她自己做決定,并能承擔(dān)其中的重量;她有追求,即使要為此付上代價(jià)也不退縮。
有荷西,我可以撐下來(lái)
在歌曲《今生》中,三毛有一段深情的告白:“為什么看到沙漠里有這么多蔚藍(lán)的海水,有這樣的花,因?yàn)榫褪怯兴谖疑磉叀!?/p>
“他”,就是大胡子荷西。
小時(shí)候讀《撒哈拉的故事》,印象深的是深夜在沙海駕車(chē)找化石、婚禮上在帽子上別一把香菜的浪漫。在《我的靈魂騎在紙背上》里,這段已成傳奇的愛(ài)情,更多卻是每對(duì)平凡夫妻的模樣——為瑣事吵架,怕見(jiàn)婆婆,拼命省錢(qián)攢錢(qián),上班累到回家倒頭就睡……
而荷西,也不是所謂的“完美丈夫”。他不懂文學(xué),不喜歡女人哭,是三毛“男朋友中唯一沒(méi)車(chē)的一個(gè)”。然而,從三毛平實(shí)親切的碎碎念中,仍可以切實(shí)感受到他的誠(chéng)懇與擔(dān)當(dāng)。
他遇事不含糊,苦活兒、臟活兒、累活兒,一力承擔(dān);性格闊朗不自苦,兩人的感情“是荷西在努力增加”。
荷西的性格里有孩子般的純真。他把三毛父母寄來(lái)的豬肉干搶去給同事吃,三毛“真氣他”,直嘆荷西“被姆媽寵壞了”;他叫三毛的外甥和外甥女“親愛(ài)的小蚱蜢”,寫(xiě)道“當(dāng)你們收到這個(gè)小紙包裹時(shí),趕快給紙上的魚(yú)吃點(diǎn)東西,它們一路由非洲到臺(tái)灣都沒(méi)有東西吃”。
相濡以沫、點(diǎn)點(diǎn)滴滴的日常,漸漸匯成一片深情。
三毛說(shuō):“我一生在物質(zhì)上沒(méi)有如此苦過(guò),但是有荷西,我可以撐下來(lái)。有時(shí)我會(huì)抱怨,但那是假的,心里沒(méi)有太多的苦,我仍是很幸福的女人。”
他們也是患難之交、生死之交。三毛與荷西居住的沙漠小城阿雍局勢(shì)動(dòng)蕩,一片“人擠人,人吃人”的地獄景象。三毛急得十天無(wú)食無(wú)睡,荷西在海邊露宿兩天,有船卡住,荷西用潛水幫忙換來(lái)上船的機(jī)會(huì)。他奇跡般地出現(xiàn)在三毛面前,兩人相抱痛哭。
三毛寫(xiě)給父母的信中,自豪之情躍然紙上:“爹爹,姆媽,你們的女婿是世界上最最了不起的青年。他不但人來(lái)了,車(chē)來(lái)了,連我的鳥(niǎo)、花、筷子、書(shū)、你們的信……連駱駝?lì)^骨、肉松、冬菇……全部運(yùn)出來(lái),我連一條床單都沒(méi)有損失。”
這一生有太多愛(ài),太多活著的方式
愛(ài)情,只是三毛生命的一部分;而愛(ài),則是貫穿三毛一生的主題。
在父母面前,三毛毫無(wú)保留,“我跟爹爹姆媽無(wú)所不談”;她對(duì)父母,不僅有依戀,更有由衷的敬愛(ài),盛贊“爹爹樣樣都行”“我的父母這世上找不出另外一對(duì)”;收到家里寄來(lái)的包裹,她興奮不已,直呼“我領(lǐng)的最大”。
如三毛自己所說(shuō),她對(duì)父母,更多不是“孝”,而是“親”。
回到臺(tái)灣后,三毛的文字中最多的是“忙”和“累”,貧病交加,母親癌癥,每天需要應(yīng)對(duì)無(wú)數(shù)伸來(lái)的手、要擔(dān)的責(zé)。
然而,在收到患有脆骨癥的少年郭星宏的信時(shí),三毛仍毫不猶豫地認(rèn)下了這個(gè)弟弟。通信經(jīng)年,她殫精竭慮,事事為星宏想得極細(xì)極深。
信中字里行間滿是疼愛(ài):“如果有人敢歧視你,姐姐先把那個(gè)人打死”“姐只要活一天,就顧你一天”;她鼓勵(lì)星宏寫(xiě)作、自立,說(shuō)“你要有用,不可自暴自棄”;她極盡坦誠(chéng),甚至將心中傷痛剖出來(lái),只為將心比心;她寄錢(qián)寄物,每筆錢(qián)如何花、如何存,都替弟弟打算得細(xì)致周全。
三毛懷念荷西時(shí)寫(xiě)道:“荷西的迷人,在于他實(shí)在是個(gè)愛(ài)生命、愛(ài)人類、愛(ài)家庭又極慷慨的人。”
三毛何嘗不是如此?她清醒,最明白“大都好物不堅(jiān)牢”,但每次仍全情投入、傾盡所有——
“愛(ài)到底是什么東西,為什么那么辛酸那么苦痛,但只要還能握住它,到死還是不肯放棄,到死也是甘心。”
這世上有兩種永恒的距離,一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這意味著孤獨(dú);一是現(xiàn)實(shí)與理想間的距離,這意味著苦痛。然而,總有人懷著一顆赤子之心,要摘星。
(摘自微信公眾號(hào)“1天1本書(sh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