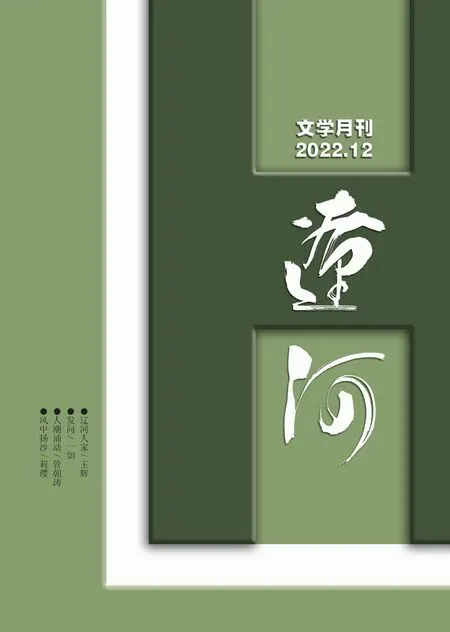人潮涌動
管朝濤
半個月前,離我三百公里的老家縣城通了鐵路,朋友回去參加首發儀式后,繞道回了浙、閩間的深山中探望親戚。回來時,他帶了一個紙箱給我,外面用記號筆工工整整地寫著“內有雞蛋,小心輕放”一行字,這是父親的筆跡。
父親今年七十歲,與大多步入老年的人一樣,對離他遠的后輩時時牽掛。因為我常年在外跑推銷,大女兒三歲前由父親和母親在鄉下撫養,大女兒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和我一起去了城里,父母便成了鄉村留守老人。父親常常挑著擔子換乘班車輾轉,或托返鄉的同村人,把他認為最好的東西捎給我們:春季有香菇木耳;夏季有各種脫水的菜干,山林里的牛肝菌;秋季是栗子、玉米、芋艿等;冬季則是收拾好的雞……他甚至把每一個雞蛋按照日期做好編號,再放上紙條告知我們按照數字的先后給孩子烹食。他做這一切,在得心應手中,又小心翼翼。每次給孩子做飯,我總想起父親,這讓我的內心總充滿溫馨,同時,又有一些愧疚。
我的老家與福建毗鄰,是離省會杭州最遠的山村。十一年前,妻子在家鄉縣城的醫院待產,我從工作地金華返回老家與母親在醫院里守候,父親則守在家中。大女兒降生的那一刻,我迅速給他打電話,父親在電話的那頭聲音沙啞著、高興地應答。我知道,他為了等待孩子出生已經幾夜沒睡好了。得知母女平安,他開始做一些供品,在老家,孩子出生的第三天有做“洗三旦”儀式,需要準備粳米做的黃粿、豆腐、豇豆干、筍干、萵苣干等。他鄭重地把它們擺在院子里的桌上,并焚香三炷,向上天和先輩告知家中添了新人。那時,還沒有手機和微信,當時的場景我沒有看到。今年年初,小女兒在這座遠離家鄉的海濱城市出生時,父親又如法炮制這個他認為非常重要的儀式。我從去賀喜的村里人拍的視頻中,看到父親虔誠地向天地、先祖致禮的情景,父親佝僂著身軀令我動容。
那年,大女兒滿月后,我又返回金華上班,便把妻女放在老家中讓父母幫忙照顧。父親更勤于勞作,努力緩解我經濟上的困頓。那段時間,老家很多人種植高山蔬菜,也就是利用高海拔山區的低溫,種一些反季蔬菜,再由收購商集中拉到浙江溫州、福建福鼎一帶售賣。有一天,父親想把自己種的菜集中后,再收購一些鄰居種的菜,直接雇車拉到溫州去賣。
父親不知道,城市里的銷售方式已經改變,再不是古老的集市交易。他只是道聽途說溫州生意好做,完全不知新興市場都有著自己的銷售渠道,或者有自己固定的攤位、或者有固定的酒店采購。父親全然不知道這些,他雇了一輛廂式貨車,裝好自己種植的以及收購來的花菜便匆忙出發。
那時,連接浙西和閩東間的山區高速公路還沒開通,前往海邊,需要繞行景寧畬族自治縣,轉道云和、麗水至青田后再上高速到溫州,全程近三百公里。那一天,沿江高速沈海線因故封道,車輛全部從G330國道上行進,一路上輾轉到達目的地已是上午十一點——這比原計劃晚了十二個小時。菜市每天凌晨三點開始到早上九點結束,父親錯過了批發的黃金時段。
初秋的熱浪里,父親在市場外守著那車花菜,憂心忡忡。下午三點,他焦急地給我打來電話,問我溫州有沒有熟人,有沒有辦法在晚上開市的時候爭取一個車攤進行交易,要不然這一車的菜就要虧了。
我當時剛進入一家通訊公司就職,接到父親電話時,剛購買好從湖州德清返回金華的車票。上車后我迅速補票,從湖州趕到浙南,列車在浙北平原的軌道上緩緩行駛,車外初秋的風景我無心欣賞,只是一路祈禱列車不要晚點,早一點兒站在父親的身邊,替他吆喝兩聲。列車到達金華站已經是晚上八點,車過浙中平原后在深山中穿梭,有了參照物后感覺快了一些,但到終點還是需要九個小時。
列車駛出金華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一點,座椅上的人已鼾聲四起,我則毫無睡意。過了幾個小站后,隨著長長的剎車聲,火車停在麗水站,我看到一個女人拎著一個大包帶著兩個孩子下了車,睡意未消的孩子踉蹌著跟在她身后。白色的燈光下,深夜的站臺顯得有些孤寂。這個場景讓我想起當年父親把披紅掛花的我送到縣城,我在人群中與他揮手作別,再踏上列車前往金華轉道西北去服兵役。父親后來寫信告訴我,他本想來甘肅探望我,只是他還沒有坐過火車,加上路途遙遠,只好作罷。
時光飛逝,如今我已為人父,看到站臺上燈光下蹣跚而行的孩子,心中生出十分的憐愛。列車關門啟動時,我看到了一個帶著安全頭盔的男人匆匆從出口臺階處跑上來,他應當是這兩個孩子的父親。只見他蹲在站臺遠處,張開手臂,那兩個孩子搖搖晃晃地沖向父親的懷抱,隨后,銀鈴般的笑聲便在站臺間蕩漾……我正凝視間,列車猛地抖動了一下,火車再次啟程了。車外的路燈在加速中化作了一道朦朧的橘色光影,流光忽明忽暗地掠過每一個人的臉,每個人的夢里,都有著同樣的目的地和希望吧?
金溫鐵路過了麗水后就變成了沿著甌江向東南的單軌,白天,車輛逢站必停等候交會,過了凌晨以后,始發站為溫州北向的列車全部已經駛過麗水,往東南走的列車若無貨運專列,一般也是暢通無阻的。我們很幸運,火車提前了一小時,到達也就是凌晨四點就到了終點站。
出租車司機拉著我去婁橋菜市集散地,一路上,我無暇攀談,只是希望早一點兒看到父親,與他一起賣菜。
婁橋菜市場燈火通明,嘈雜聲轟然:大卡車一排排尾部朝外,匯集著全國各地運來的蔬菜、海鮮、干貨、水果;摩托車、三輪車在大卡車中穿梭,面包車和小四輪車喇叭聲不斷,急急地催促著川流不息的人們。我快步前行,用目光掃視著每一個角落,尋找父親的身影,他的手機已經沒電,想要找到他真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時間很快過去,東方漸漸露出魚肚白,大宗采購的人們已經逐漸離場,喧囂漸息。剩下騎著三輪車和摩托車的小飯店老板、工廠食堂的采購商與販賣剩菜的攤主正在激烈地討價還價。
找了一圈后,我終于在東北角找到了父親。這是塊市場外的空地,有幾輛三輪車與他那輛小貨車臨時并排在一起在賣水果和蔬菜。他們大抵是與我父親一樣,被市場拒絕后誤打誤撞湊到這里擺路邊攤。
父親站在塑料籮筐上,在晨霧中揮舞著手臂,用沙啞的聲音吆喝著叫賣:“花菜,大削價五毛一斤,最后二百斤!”父親沒有看見我。
霧氣散去,天色開始大亮了,父親坐在空地上一個被人丟棄的空木箱子上,一五一十地數著手里的鈔票,他不知道我已經悄悄地走到了他身邊。他抬起頭的一瞬間,除了眼里的血絲外,皆是欣喜。然后,他在小筆記本上快速地寫著什么,把筆記本遞給了我,原來上面是收支小計:
1、收購,1800斤×0.8元=1440元——付清。2、自產,1000斤——不計價。3、裝運費,1200元——付清。4、與開車師傅路上快餐40元。共計成本2680元,另(零)售收入2750元。
父親說,這兩千八百斤菜原來按照溫州市場一塊八的預估批發價,本來可以多賺兩千八百塊。但是因為晚到了,又在車廂悶了半天,菜都蔫了,只好折價售賣,相當于自己的菜白種了……
“明年再來就是了!”父親說。我攥著筆記本站在那里久久說不出話來。父親說完這句話又開始念叨他分別了一天的小孫女。我遞給他一瓶水,帶著他走到大路上等第一班前往城里的公交車。
清早,路燈還未熄滅,橘黃色的燈光下,我與父親一前一后地走著。路上呼嘯而過的卡車揚起一陣塵煙。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城市結伴而行。上了公交車后,父親總是不自覺地把頭伸出車窗,每次都被我制止,飛速變化的城市對于他永遠是陌生的。
我在窗口買好了火車票,然后給貨車司機發了信息,帶著父親在火車站對面的街邊小店吃早飯。我們叫了兩屜小籠包、一碗糯米飯、一碗咸豆漿,這其中大部分是父親愛吃的,鄉間通常把早飯當正餐,父親這種超大的食量很正常。
吃飯的時間很寬裕,但父親卻狼吞虎咽,像是怕火車馬上要開走一般,他總是這樣。記得在我年幼時他出遠門攬活兒,頭一天晚上總是輾轉反側,生怕誤了班車。
我們坐在站前廣場等待檢票,這是他第一次坐火車,也是我特意安排的。到麗水的快客是一個半小時,而火車通常需要兩個小時以上,一般的綠皮火車甚至超過四個小時。我買了兩張金溫短途城際列車票,父親在麗水下車再坐長途客車回慶元,我直接返回金華繼續上班。
候車的時候,父親依然不停地向我講述他的小孫女。他說,越越現在長牙了,會爬到他身邊撒嬌……說著說著,父親居然拿著紙巾擦拭了下已經濕潤的眼睛,像是和一位遠方來的朋友說著他的孩子。
火車站熙熙攘攘,我生怕父親走丟,便緊緊拽住他那生硬的、長滿老繭的手,我們在人群中穿梭——就像二十多年前他帶我去外祖母家,在長途客車站時,他也是這樣緊緊攥著我的小手。
兩段喧囂的時光中,一大一小兩個身影在人潮中向前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