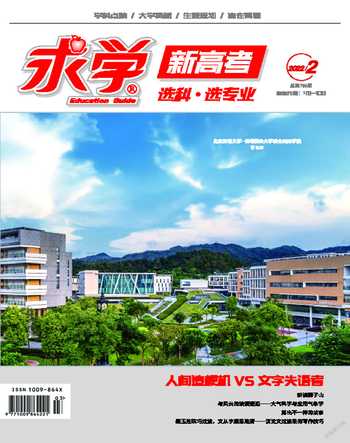古代詩歌常見意象(三)
典故類
借指為正義事業所流的血,如顧炎武《酬朱監紀四輔》:“愁看京口三軍潰,痛說揚州七日圍。碧血未消今戰壘,白頭相見舊征衣。”語出《莊子·外物》:“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后來也用“碧血”“萇弘化碧”比喻蒙冤而死或忠心不泯,如《竇娥冤》:“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等無頭愿,委實的冤情不淺……這就是咱萇弘化碧,望帝啼鵑。”
泛指寶刀、利劍。出自漢趙曄《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吳作鉤者甚眾。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釁金,遂成二鉤獻于闔閭,詣宮門而求賞……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不平凡的來歷鑄就的這一柄寶劍,成了渴求建功立業者的利器。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通過看吳鉤,拍欄桿,表達了自己意欲報效祖國、建功立業,但又無人領會的失意情懷。
指立志報效國家,收復失地。出自《晉書·祖逖傳》:“(逖)仍將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又有宋人趙善括《滿江紅·海岳儲祥》:“穎脫難藏沖斗劍,誓清行擊中流楫。”
又稱“中流誓”,如陳亮《念奴嬌·登多景樓》:“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
指軍營。唐武元衡《送張六諫議歸朝》:“笛怨柳營煙漠漠,云愁江館雨蕭蕭。”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記載,漢文帝時,漢軍分扎霸上、棘門、細柳以備匈奴,細柳營主將為周亞夫。周亞夫的細柳軍營紀律嚴明、軍容整齊,連文帝及隨從都得經周亞夫許可,方可入營。文帝極為贊賞周亞夫的治軍有方。后將細柳營代稱紀律嚴明的軍營,如唐人鮑溶《贈李黯將軍》:“細柳連營石塹牢,平安狼火赤星高。”
指囚犯。《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通“脫”)之。……公曰:‘能樂乎?對曰:‘先人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楚人鐘儀被囚于晉,仍然戴南冠,彈奏南國音樂,范文子稱贊這是君子之行。后來文人以此指代自己懷有節操的囚徒生活,如駱賓王《在獄詠蟬》:“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
比喻杰出的人才。語出李斯《諫逐客書》:“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指隨侯珠與和氏璧)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吳國名劍)之劍,乘纖離(駿馬名)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tuó,揚子鱷之類的動物,皮可制鼓)之鼓……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
后來便以“昆山玉”比喻優秀的人才,如劉禹錫《送李中丞赴楚州》:“憶君初得昆山玉,同向揚州攜手行。”
南浦是水邊的送別之所。屈原《九歌·河伯》:“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之如何!”范成大《橫塘》:“南浦春來綠一川,石橋朱塔倆依然。”南宋韓元吉《瑞鶴仙·送王季夷》:“西風吹暮雨。正碧樹涼生,送君南浦。”古來水邊送別并非只在南浦,但因長期的文化浸染,南浦已成為水邊送別之地的一個專名了。
羌笛是古代出自西部的一種樂器,它發出的聲音凄切哀婉,唐代邊塞詩中經常提到,如王之渙《涼州詞》:“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范仲淹《漁家傲》:“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羌管發出的凄切之音,常讓征夫愴然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