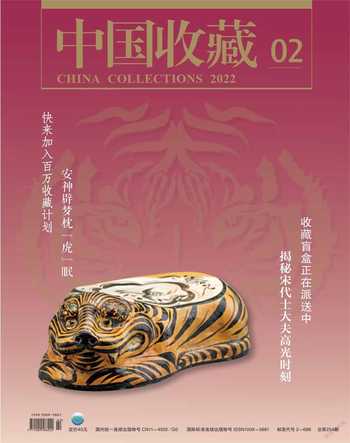收藏也是志向
葉辛

我的同時代人吳少華,在今天的上海灘,是一個大名人。說他是大名人,是因為他的名字,和上海的收藏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我在一次文化活動中認識他時,他是上海市收藏協會的會長。一同參會的人告訴我,他不僅僅是會長,管理協會業務,組織協會展覽,而且推出一個一個“大王”,鐘表收藏“大王”、折扇收藏“大王”、紫砂壺收藏“ 大王”、紅木收藏“大王”、火花收藏“大王”、算盤收藏“大王”、錢幣收藏“大王”……這“大王”兩字,既不是職稱,也不是職務,但是在收藏界,受人尊敬,令人感興趣,愿意和他交談、交流。你說一個“筷子大王”,有多少工資?價值多少?是不好評判的,但是走進去參觀一下,就會開拓眼界,得到許許多多有關你天天在使用的筷子的知識。
我不搞收藏,但我對收藏感興趣。為什么呢,是覺得每一件珍貴的藏品里面都有故事。
對了,真是故事,令我這個小說家感到濃郁的興趣。比如說和筷子近似的扇子,一把扇子能值多少錢呢?再名貴的扇子,用金錢去衡量,也是能算出它價值來的。名人題了字,在扇面上繪了畫,簽下了他的名字,就讓人覺得珍貴了。如果這把扇子還有故事,這故事又同歷史人物,同某一歷史事件有關系,那么這把扇子就成了藏品。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藏家,一輩子有幾件這樣的藏品,那意義就非同一般了,就能引出非同尋常的故事來了。
吳少華推出的這本書,《大言齋收藏筆記》收錄的文章,都是一些這樣的故事。
這是我籠而統之的說法,講詳細一點。疫情襲來,吳少華宅在家中,回想40多年的收藏經歷,從事收藏協會工作,和各界藏家廣交朋友,往事歷歷,一一浮上心頭,他以筆記形式,寫下了一個又一個和收藏有關的故事。
饒有興趣地讀完了他以樸實的文字寫出的一篇篇筆記,我得到了一個強烈的印象——收藏也是志向。
自古以來,社會上流傳著一種說法,玩物喪志。我們小時候,也經常被家長、老師教導,不要沉浸和迷醉于某一樣物品。比如很多男孩子喜歡過的蟋蟀盆,進康樂球房打球,收藏火花、郵票、香煙牌子,從早到晚和人對弈下棋……這一類行為往往被斥為“玩物喪志”。為此,學習成績下降了,考試不及格了。一位同學的父親,甚至把孩子收藏在天井里的蟋蟀盆砸了個稀巴爛,因為他的成績單上開了“紅燈”,害得這位同學哭了半天。
殊不知收藏不僅是一種喜好,一種興趣,一種獨特的眼光。收藏還是一種情趣,一種品格,一種精神的追求,一種志向。
吳少華文章中寫到的折扇收藏家黃國棟,曾經是海上聞人杜月笙的賬房先生,想他一生經手過多少錢財與金銀財寶,見過多多少少各界名人雅士,經受過多少跌宕和波折?但他視財富如流水,把一切視作過眼云煙。唯獨陪他的,是他一輩子收藏的264把扇子。這一把把看來普普通通的扇子上,留下了無數達官貴人、文人雅士、各族各界人士的題簽和大家廖廖數筆的繪畫。恐怕在“文革”中抄家的時候,誰都不會對扇子感多大的興趣。可能也正是因為眾人的這種心理,這批扇子得以保留下來,如今展開一把把扇面觀看,人們會不由自主地贊嘆:這是一批無價之寶。
對黃國棟藏家來講,收藏扇子,不僅僅是一種愛好和風度,更是他的情趣,他的精神寄托,他的志向。有了這一志向,他的精神有了寄托,心靈得以慰籍。故而風雨人生,云去霧來,他都能坦然應對。這對于一個人,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
且不論收藏協會在這看似熱熱鬧鬧,國家這里那里總有些類似的地震、洪澇災害、扶貧救助弱勢群體的事兒時,協會經常做些將拍賣所得,捐獻捐助一類善舉,那就更有意義了。
近期聽說收藏協會換屆了,比吳少華年輕的張堅接替了他的會長職務,吳少華整理已經在大小報刊發表的文章,又新寫了一些和藏品、藏家、藏界有關的趣聞軼事,要出一本書,拿來請我寫個序。
我津津有味地暢讀之后,欣然寫下了這篇小文。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