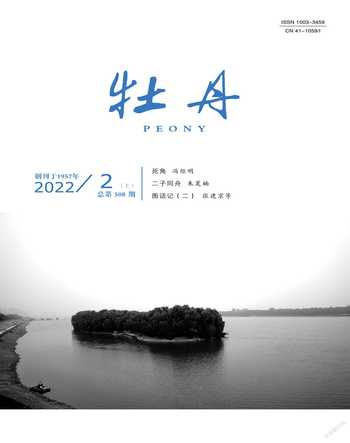天門
王剛,80后,魯迅文學院少數民族25期學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014年開始小說創作,作品見《民族文學》《長城》《四川文學》《朔方》《廣州文藝》《文學港》《南方文學》《野草》等刊。
這個村莊有個奇怪的名字——天門。
從崖上俯瞰,村莊呈三角形。具體點兒說,村后是高大巍峨的吳王山,構成三角形的底邊;百盤江從左邊峽谷奔涌而出,毛從河從右邊峽谷咆哮而來,兩江于村前匯合,構成三角形的另外兩邊。就這樣,山水狼狽為奸,將村莊圍困其中。什么叫絕地,這就叫絕地;什么叫絕境,這就叫絕境。站在崖頂俯瞰,天門就像一座孤島,如浮萍飄搖,那么小,那么孤單,那么無望。
遙望天門,頭腦里不禁跳出彈丸之地窮山惡水之類的詞語。不得不感嘆,這樣的地方,怎么會有人煙?最初來到這里的人,怎么會停下跋涉的腳步?他們有沒有想到,因為他們輕率的決定,讓兒孫一輩又一輩固守于孤島之上,無法走出山山水水的重重屏障。這里的每一個人,從出生那天起,不得不面對一個宿命:形同囚徒。身陷銅墻鐵壁之中。哪怕望穿秋水,也盼不來一只鴻雁。哪怕腳板磨破,也踏不出一條大道。哪怕癡望百年,也無法飛越大山川大河。在這塊巴掌大的土地上,他們一代代出生,一代代死去,像一茬茬生生死死的莊稼。
要出村,須翻越高聳入云的吳王山。多少年來,天門人不知用什么辦法,在絕壁上開鑿了一條蜿蜒曲折的石梯。這是通往村外的唯一途徑,陡峭難行,稍有不慎,就會墜落懸崖,粉身碎骨。途中要經過一道狹窄的石門,石門兩邊是刀砍斧削的絕壁,抬頭仰望,只能看見一線天空。據說,天門的名稱就是從這里來的。提起這道石門,天門人唏噓不已,說老天沒有瞎眼,給他們留了一道門。有了這道門,天門就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有了血液,活上一千年一萬年也沒問題。也許正是如此,他們對石門充滿虔誠,不許任何人損壞這里的一草一木。從石門經過的時候,他們小心翼翼,悄無聲息,似乎稍有動靜,就會把石門弄垮了。沒了石門,天門無門,無門的村莊,終會寂然死去,連草木也沒辦法茍活。
第一次踏進天門,是在二十年前。那時候,我剛從學校畢業,成了鄉中學的一名教師。班上有一個來自天門的學生,叫盧小朋。盧小朋矮個,黑臉,穿一件肥大的外衣,走起路來晃晃悠悠。同學們說他是掃地僧,意思是只要他走過的地方,根本不需要打掃。盧小朋沉默寡言,常坐在角落發呆,像一塊不吭不哈的石頭。我找他談過幾次話,他總是埋著頭,啥也不說。逼急了,哼哼哈哈說上幾句,卻帶著濃重的鼻音,讓人聽不清楚。這不奇怪,天門的孩子打從娘胎里掉下來,聽的說的全是布依族語言,怎么會說漢話呢?當他們漸漸長大,當他們終于有機會走出天門,當他們戰戰兢兢張開嘴巴,卻招來陣陣刺耳的笑聲。或許正是這個原因,盧小朋待了幾個月,忽然不聲不響地消失了。恰在此時,學校接到鄉政府的通知,要求全體老師進村入戶,完成文化戶口普查。我和一個被稱為大程的老師因為比較年輕,被派往天門。大程不樂意,一張苦瓜臉拉得老長,眉頭擰成了川字。我雖忐忑不安,但心想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去盧小朋家看看。
站在崖頂,俯瞰縹渺的天門。風真大,呼啦啦從崖下沖上來,吹得草木唰唰發抖。樹木又矮又小,扭曲變形,裸露著枯黑的枝干。靠近崖邊,陡覺有一股巨大的磁力,要把人吸下去。我只看了一眼,趕緊往后退,擔心被風抓住,拽下萬丈懸崖。靠著一棵樹站定,眼光一路滑翔墜落,經過長途跋涉,終于落到天門的土地上。那塊三角形的小洲,夾在兩條江水之間,顯得那么小,那么孤獨。
沿著山勢稍緩處的一個豁口,踏上了那條石梯。說是石梯,其實不過是一些或橫或豎的石頭槽子。行走的時候,要把腳掌踩到石頭槽上,手抓枯黃的草木,小心翼翼往下挪。風聲響亮,讓人頭皮發麻,腳桿發軟,心頭打戰。稍微探一下頭,就能看見垂直險峻的懸崖,深不見底。頭上的石壁犬牙交錯,掛著一些枯樹斷藤。我們蹲下身子,手抓草木,腳踩石梯,形同壁虎,緊貼石壁,一步一步往前移。就這樣,大概走了幾十分鐘,終于來到了那道傳說中的石門。
說是石門,其實就是一條裂縫。縫隙狹長,甩手的幅度稍大一點兒,就會碰上石壁。仰起頭,目光艱難地爬上高高的巖壁,方能看見一線巴掌寬的天空。盯著那線天空看上一會,陡然產生一種跌落井底的感覺。這道石頭裂縫,是天門的眼,讓天門不再黑暗;是天門的嘴,讓天門有了呼吸。多少年來,盡管天門身陷重圍,但仍然沒有死去。它是一只困獸,千百年來伏在吳王山腳。兩條江鐵鏈般鎖住它的四肢,囚禁著它的脈搏。不過,它還活著,像一塊沉默的石頭。
過了石門,一路下坡。路旁亂石遍地,雜草叢生,時有鳥兒鳴叫。回頭仰望,吳王山直插云天,越發顯得卓然險峻。幾只老鷹張開翅膀,盤旋在高高的山頂,看上去像幾片樹葉。太陽掛在高遠的蒼穹,像一張圓形的單薄的白紙。
小路彎彎扭扭,蛇一般爬進村子。房子很有特點,清一色木樓,一律二層,青瓦房蓋。這種樓房稱作吊腳樓,第一層用作圈舍,第二層住人。這種房子省地,干凈、涼快、通風好,采光好。其壞處也顯然易見:牲畜和人之間,僅隔一層木板,可以聽見豬牛馬羊的哼哼聲,吵鬧聲,打鼾聲,大小便的聲音。如果天氣干燥,風會把牲畜的臭味送到樓上,讓人無處可躲。時見布依族姑娘坐在二樓,靠著窗子飛針走線。據說,布依族有一條規矩,姑娘們要親手為自己做一件嫁衣。嫁衣極為考究,須一針一線縫制。要做成一套,往往需耗時多年。
邊走邊問,邊問邊走。轉過一片竹林,看見一棵亭亭如蓋的大楓樹,樹下站著一幢青瓦吊腳樓。一條漢子赤裸肩膀,坐在篾片之中,彎腰編織籮筐。修長的篾片翩翩起舞,富有極強的節奏感。這漢子就是村主任陸勇。他丟下籮筐,從篾片中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土,招呼我們上樓。我們跟著他,沿之字形石頭臺階,爬上二樓。屁股還沒坐穩,他變魔術般端來兩碗米酒,遞給我和大程。天門有個規矩,進門要喝一碗酒,絕不能拒絕。如果不喝,主人家會不高興。看著飄香的米酒,我們還能說什么呢?只有端起碗,一飲而盡。
陸勇帶著我們,一戶一戶往下走。那些掩映于林木間的吊腳樓,乍看是一道美麗的風景,可當你走近,會看見破損的瓦片,密密麻麻的蟲眼,斑斑駁駁的痕跡,沾滿蟲子的蛛網,半人多高的荒草……走進一扇扇門,滿眼是漆黑的灶臺,破爛的籬笆,殘缺的鐵鍋,低矮的凳子,斑駁的桌子,空洞洞的竹簍。從路上走過,會遇上泥猴似的頑童,踽踽獨行的老人,面色灰黑的男人,眉頭緊鎖的婦女。多少年來,他們像雜草匍匐在這片土地上,那種卑微讓人心痛。
走訪中,我們發現百分之八九十的村民是半文盲,或者文盲;少部分讀過小學,上過初中的少之又少;上過高中、中師、中專的,一個也沒有。村里設有小學,但只有一二三年級。學校只有兩個民辦教師:一個姓潘,讀過初一;一個姓岑,讀過初二。兩位老師名為老師,實為農民。遇上農忙季節,他們一頭扎進土地,對學生實行放羊式教學。這不怪他們,試想一下吧,每個月只有幾十元工資,如果不種地,怎么養活老婆孩子?家長們也巴望學校不上課,可以理直氣壯地把孩子叫回來,讓他們下地干活。就這樣,學生們渾渾噩噩混日子,稀里糊涂走到三年級。少數家庭條件稍好的,把孩子送到山外的小學繼續學習。大多學生選擇輟學,回家種田種地,娶媳婦嫁男人,生孩子,重復祖輩的生活。
眼前是一片廣袤的梯田,層層疊疊,綠波蕩漾。迎面走來幾個孩子,背著書包,蹦蹦跳跳,打打鬧鬧。轉個彎,看見一株茂盛的火繩樹,樹下站著一幢石頭瓦房。幾只麻雀站在枝頭,瞪著圓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打量我們。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站在屋檐下,望著天上的云朵發呆。陸勇叫了聲潘老師,他這才驚醒過來,趕緊用衣袖擦了擦手,迎上來和我們握手。潘老師個子矮小,戴了副眼鏡,額頭有不少扎眼的白發。潘老師領著我們,參觀了他們的學校:三間教室,分別掛著一二三年級的班牌;樓前有一塊長滿野草的平地,這就是操場。走進教室,呈現在眼前的是粗糙的石頭墻體,凸凹的地板,瘸腿的桌子,斷腳的椅子,斑駁的黑板,粘著蟲子的蛛絲網。抬起頭來,可見椽子的顏色深淺不一,有被雨水侵蝕過的痕跡。看看腳下的地板,果然有明顯的水漬。窗邊放著一張書桌,上面放著兩盒粉筆,一瓶紅墨水,一支鋼筆,幾本教參書。不用說,這是潘老師辦公的地方。潘老師很不自在,紅著臉說,唉,見笑了,見笑了。
出了學校,穿過一片樹林,走過一座木橋,繞過一座小山,一棵枝干遒勁的柿子樹躍入眼簾。柿子樹比周圍的樹要高一頭,掛滿了樹葉和青色的柿子。樹下站著一幢腳樓,歪歪斜斜的。陸勇指著吊腳樓說,那就是盧小朋家。
我們扶著顫悠悠的木梯,小心翼翼爬上二樓。一個滿臉菜色的姑娘從屋里探出頭,懷里抱著一個瘦小的嬰兒。陸勇問盧小朋在不在家。姑娘滿臉狐疑,一聲不吭。陸勇換了布依族語言,打著手勢,繼續跟她交談。姑娘終于說話了,但聲音微弱,如同耳語。陸勇問了幾句,對我們說,盧小朋去了很遠的地方,今天不回來了。姑娘堵住門口,似乎也沒有讓我們進去的意思。
翻開戶口本,盧小朋婚姻情況那一欄,赫然填著已婚。看了看他的年齡,不過十七歲。翻開下一頁,是盧小朋妻子的信息:潘小云,十六歲。這么小的年紀就結婚了?會不會登記錯了?陸勇說沒錯,盧小朋確實已經結婚了。陸勇解釋說,沒什么奇怪的,不少家長都希望兒子早點娶妻,早點抱上孫子。我悄聲問,這是潘小云嗎?陸勇點點頭,看著嬰兒說,對,這就是盧小朋的女兒。
完成文化戶口普查之后,我們離開了天門。當我們鉆出石門,攀上石梯,耳邊傳來了嗚嗚咽咽的嗩吶聲。登上崖頂,回頭俯瞰縹渺的天門,心想這輩子不會再來了。這是一塊孤獨的土地,是一塊封閉的土地,是一塊絕望的土地。多少年來,人們匍匐在吳王山下,以山為神,寂寞生長,寂寞老去。多少年來,人們徘徊于百盤江畔,毛從河邊,望水興嘆,孤獨地生活。
幾年后,我離開鄉中學,調入了縣城。時間長了,天門已成為遙遠的回憶,逐漸變成一個模糊的影子。偶有人提起,也只是嘆息一聲。那地方實在太苦了,太讓人絕望了。那條掛在懸崖上的小路,如同繩索飄蕩,讓人不寒而栗。我從來沒有想過,這輩子還會再次踏進天門。誰料世事變幻,冥冥之中老天自有安排。二十年之后,命運之神讓我再次回到了天門。
事情是這樣的。縣里組織一批文化工作者前往天門采風,我也在邀請之列。接電話時,我的腦海里倏然閃出那條掛在懸崖上的小路。可工作人員說,這一次走水路。直到這時,我才知道天門的水路已經開通了,可以乘船前往。據工作人員介紹,天門已被納入旅游規劃,這一次活動是為了給下一步的工作做鋪墊。比如說,記錄沿途風光,撰寫解說詞;測試船速、水速、用時;采集天門的風景點,為旅游規劃提供依據;要在天門選定修建碼頭的位置等。我有點發蒙,萬萬沒想到,天門竟以這種方式再次闖進了我的生活。
出發那天,我們乘坐大巴,抵達猴場碼頭。百盤江與毛從河于天門匯合之后,穿越崇山峻嶺,來到了這里。該河段地勢平緩,旅游局在這里修了碼頭,稱作猴場碼頭。我們穿上救生衣,登上“六盤水號”,迎著習習清風,奔向連綿群山。站在船頭,森森峭壁撲面而來,遮天蔽日。懸崖刀砍斧削,垂直插入碧水之中。時見遒勁的古樹懸于崖上,裸露的樹根抓住堅硬的巖石,仿佛稍一松勁,就會墜落江心。藤蔓從崖上垂下來,長長的,毛茸茸的,飄來蕩去。兩岸的懸崖陡然靠近,形成彎曲漫長的峽谷。最窄的一處,兩邊山崖幾乎靠在一起。從遠處望去,江水突然消失,只剩下莽莽蒼蒼的大山。行至山腳,頓覺光線昏暗,陰氣森森。聽說,這地方稱為一線天,是江上最險要的關口。
山重水復,水復山重,柳暗花明,花明柳暗。這個明媚的秋日,大船沿蜿蜒江流,一路趕往天門。船行似風,穿過一道道峽谷,繞過一座座山峰,一個小小的村莊從水里冒出來。有人大喊,快看,天門到了。遠遠望去,似曾相識,又覺得格外陌生。不過,我很快認出了村子后卓爾不群的吳王山。
大船靠岸,一群人擁了上來。打頭的是個身材高挑的女孩,牛仔褲,白T恤,頭發馬尾般晃來晃去。她的身后跟著一群男女,抱著酒壇,端著酒碗。女孩笑瞇瞇地說,各位領導各位朋友,到哪山唱哪山的歌,到天門得喝天門的酒。女孩操著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字正腔圓,鏗鏘悅耳。有人告訴我,姑娘名叫盧鳳秀,是個大學生村官。姑娘說完,穿紅著綠的姑娘們一擁而上,把一碗碗酒遞到我們手里。我端著碗,細細品味米酒的芬芳,思緒卻飄過了二十年。
一個干瘦的漢子擠到面前,盯著我看了看說,你是王老師吧?我看著他,腦海里嘎噔一下:這不是村主任陸勇嗎?
陸勇告訴我,他退下來了。他指了指一個身材敦實的小伙子,說他是村里的主任。小伙子正在和旅游局的領導說話,落落大方,有一股潑辣勁。陸勇說,小伙子叫王似令,是個中專生,腦子活,點子多,能說能寫,是把干事的好手。五六年前,陸勇從村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把擔子交給了年輕人。
午飯安排在村里的農家樂。飯菜非常豐盛,竹筒米飯,麻婆豆腐,青菜豆花,干煸洋芋絲,青椒拌茄子,清燉烏骨雞,紅燒野生魚……米飯尤其特別,粒粒豐滿,呈醬紅色,有一股清香。據盧鳳秀介紹,這是村里栽種的紅米。近年來,村里進行產業調整,因地制宜種植紅米。紅米的收購價20元一公斤,遠超普通大米的價格,卻供不應求。除了種植紅米,村里還大力拓寬致富之路:辦養殖場,養鴨養雞;在江里養魚;種植甘蔗等。喝著美酒,聽著盧鳳秀唱歌一般的聲音,想起第一次到天門的情景,不禁思緒翻涌,感慨萬千。
吃過飯,盧鳳秀、王似令及鄉工作人員陪同縣里的領導去江邊勘察,選擇修建碼頭的地址。其他人自由活動,四處走,到處看,用自己的方式去領略天門的韻味。我和陸勇一道,打算沿著二十年前的足跡,重新走上一次。
吊腳樓還是二十年前的吊腳樓。穿紅著綠的布依姑娘倚窗而坐,飛針走線,不時發出陣陣笑聲。站在樓下,靜靜看上幾分鐘,竟覺得那是一幅畫,一首詩。仔細打量,發現吊腳樓也不再是當初的吊腳樓。破碎的瓦片沒了,拾掇得干干凈凈。破爛的板壁沒了,換上了結實的木板。晃悠悠的木梯沒了,換成了穩固安全的石頭臺階。裂縫到處可見的樓板也變了樣子,該補的補,該換的換。看著那些錯落有致的吊腳樓,浮躁的心竟慢慢回歸寧靜。也許,不管時代如果發展,有些東西應該留下來,不管我們走遍千山萬水,還能夠找到鄉愁的源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村里修建了布依族文化陳列館。走進古色古香的陳列館,可以看見百年前的銅鼓,花式多樣的服飾,大美無言的刺繡,用來表達布依人生死悲歡愛恨情仇的嗩吶………看著這些,不由讓人想起一個村落的滄桑歲月,一個民族沉甸甸的歷史。為了辦好陳列館,工作人員不知耗費了多少心血。他們為每一幢吊腳樓建立了檔案,形成一戶一檔臺賬式管理,有圖片,有文字,有數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應該說,這些吊腳樓是幸運的,它們有了自己的身份證和戶口本。想一想吧,隨著時代的飛速發展,許多農村地區已經看不見一幢木樓。再過幾十年,上百年,當人們走出鋼筋水泥的城市,走進全是吊腳樓的村莊,會不會感謝今天這些人做的努力?那時候,當我們面對沉默的銅鼓,泛黃的刺繡,無聲的長笛,緘默的嗩吶,又會涌起多少感傷?引發多少感慨?
走過金黃的彩云般的紅米梯田,轉了一個彎,赫然看見那株枝繁葉茂的火繩樹,樹下站在一幢二層平房。陸勇說,那是新建的學校。教學樓前面,是一片寬闊的水泥場,有籃球架,有兵乓球臺。正值課間,穿著校服的學生們或做游戲,或打籃球,或打乒乓球,不時響起陣陣歡笑聲。
我們爬上二樓,走進教師辦公室。幾個老師坐在座位上,各忙各的事。陸勇沖一個伏在桌上改作業的老師喊道,盧老師,看看誰來了?那位老師抬起頭,慌忙站起來,抓住我的手說,王老師,是你啊。我有點兒發愣,看著他瘦削黧黑的臉,多少往事涌上心頭。剎那間,記憶穿越塵封的歲月,我又看見了那個矮矮的、穿著肥大衣服的、沉默寡言的盧小朋。我鼻子發酸,握緊他的手說,小朋,真是你啊。盧小朋眼眶泛紅,哽咽說,是我,王老師,是我,我是小朋。
盧小朋告訴我,退學的第二年,他頂了岑老師的位置(岑老師辭職了)。再后來,他參加考試,轉為了公辦教師。我問,潘老師呢?他現在在哪里?盧小朋說,他退休了,前年退的。我一驚,潘老師已經退休了啊,時間過得真快。猶記得二十年前那個站在屋檐下發呆的漢子,戴著眼鏡,白發絲絲飄動。
出了校門,陸勇忽然問我,你知道盧鳳秀是誰的女兒嗎?不等我回答,他又補充說,盧小朋。我愣住了,盧鳳秀竟然是盧小朋的女兒,這是真的嗎?
陸勇說,你忘記了嗎?二十年前,你見過她!
我記起來了,二十年前,我沒遇上盧小朋,卻遇上了他的妻子女兒。時間真是最神奇的魔術師,它上演了讓人目瞪口呆的奇跡。那個只會哭泣的瘦瘦的襁褓中的孩子,歷經二十個春秋的涅槃,已經變成一只金鳳凰。
據陸勇還說,天門旅游項目的落地,盧鳳秀功不可沒。幾年前,就讀大學的盧鳳秀假期回村,舉著相機拍吊腳樓、吳王山、石梯路、龍竹、火繩樹、梯田、嗩吶、銅鼓、刺繡……回校后,她把圖片進行整理,編輯排版,配上說明文字,發到QQ和微信上。這些圖片引起了關注,不少人不顧路途遙遠,沿著石梯進入天門。這些人中,有喜歡冒險的驢友,標新立異的畫家,披著長發的詩人,舉著相機的攝影愛好者。誰也沒想到,正是那些照片,給天門打開了另一扇門。
出了村,看見一條正在修建的公路,如彎曲的繩子掛在吳王山上。陸勇告訴我,公路是去年動工的,目前已經打通了毛路。這條路修得格外艱難,是用炸藥一點兒一點兒炸開的。幾乎每推進一尺,都要付出血的代價。下一步,將對公路進行硬化。等到明年這個季節,就可以把車開進天門了。我望著巍然聳立的吳王山,感到不可思議。二十年前,誰會想到能夠從絕壁上掘出一條通天大道?
踩著嗩吶聲聲,我們拾級而上。走公路真快啊,不過二十分鐘,我們爬上了崖頂。壯麗的夕陽染紅西天云彩,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佇立崖上,俯瞰五彩斑斕的天門,竟覺得她是一只展翅躍飛的鳳凰。
風很大,呼啦啦從崖下沖上來,吹得草木唰唰作響。我們迎風舉起手臂,忽有一種變成蒼鷹飛向天空的快感。恰在此時,傳來幾聲響亮的鷹嘯。揚起臉,看見一只蒼鷹展開翅膀,翱翔于云彩之上。
責任編輯?? 楊?? 櫪